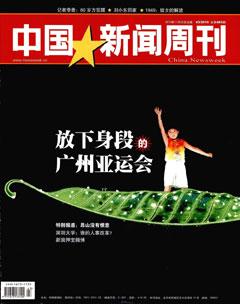记者李普: 60岁方觉醒
徐庆全

11月8日,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走完了92年生命历程。
在八宝山向他安详的遗容告别时,曾经的一个场景一直萦绕在脑海。那是2001年的一次聚会上,老少数十口人,老有耄耋之年如李普,少有风华者如卢跃刚。主持人介绍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云云,李普站起来朗声说:“记者李普!”主持人愕然,与会者也愕然,随即满堂掌声。
文章千古事,官衔堪几年?李普,1937年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共,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后来官至新华社副社长高位,但在1949年至今的六十多年来,部长数以千计,有几个名字被记住?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他是“记者李普”,又是“思想者李普”。
作品成为新闻史上一个个路标
1938年,李普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虽然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写作才华已经显露。那一年10月长沙大火,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的李普给中共湖南省委半公开的机关报《观察日报》写了一篇《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这是他的第一篇新闻文字。1939年初,他受命为《观察日报》的特派记者。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
《观察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李普到贵阳,他给主张全民抗战的成都全民通讯社写了几篇通讯。后来他辗转来到重庆,成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社的记者,那是1940年,他22岁。
李普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入学以后,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李普在《新华日报》只做了一年多记者,从1942年开始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不能亲临第一线,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作为专栏作者,他写下了诸多有影响的文章。
1945年2月,李普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系统介绍解放区的专栏。他用解放区的实践,阐述抗日与民主两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强调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生长的共产党,也是在民主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民主,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文章陆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来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底出版。东北三省最早解放,解放区的东北书店曾经大量翻印这本书,它又随着东北解放军进关而流入关内。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
有位当年国统区的读者后来写信给李普:“感谢你写的《光荣归于民主》,使我们这些当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知道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我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为着共同的幸福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感谢这本书和另外几本书的指引,我在1946年4月参加了党组织。”这位读者至今还记得那本书封面的样子,又写道:“我更记得这本书当时唤起的革命激情,给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展现了一片光明。我总是怀着亲切的感情想起《光荣归于民主》。”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李普重新开始当记者。敏锐、勤奋的个性,使他成为解放区著名的“记者李普”。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李普作为随军记者采写《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准确地揭示了战局的发展,指出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新华社很快播发后,毛泽东看到后说,“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意在批评这条消息发早了。此文后来被选入小学课本,成为如笔者这样年龄的人对刘邓挺进大别山之于解放战争意义的最早概念——当然,后来党史、军史上也是这么写的。有一位当年在东北当县委书记的老人,多年以后对李普的军事报道,还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他说当时在下面当县委书记,看不到上面的文件,他对整个形势的了解,主要就靠李普这些报道。
“记者李普”再一次为人们所记住并被写入历史,是他1949年对开国大典的报道。那时,他就在站在毛泽东身后。李普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一文回顾了当年他报道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形:“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深怀念,神往不已。”文章里,他讲了两条“独家新闻”。一条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宣读这个公告的时候我站在他后排,他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原来铅印的这份《公告》稿并没有这个委员的名单,是临时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增补上去的。另一条“独家新闻”是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周恩来向会议作了关于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大会所有的报告和讲演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惟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我们记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看他手里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我感到今天的任务不轻松,必须详细做笔记。等他讲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李普就是根据周恩来写在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的八条提纲写出一篇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并据以收入后来的《周恩来选集》。
“记者李普”也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脑中的印记。开国大典结束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就给李普在他的办公室里摆一张办公桌。李普成为经委员会新闻秘书,列席财经委员会一切大小会议。1950年李普采写的《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洋洋万余言,综论全国经济形势,着重分析了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贯彻新民主主义财政经济政策,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及其稳定金融物价的巨大成就。这篇文章,至今为新闻界和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重视。
“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
记者生涯,使李普能够从近处看历史的演进,或者参与这种历史的演进。而当他晚年退下来后,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又深入地回顾与反思历史演进的过程,并写下了大量文章。因此,李普又有了“思想者李普”的名号。
《悼胡绳》一文是李普前几年的作品。他追忆在重庆新华日报与胡绳共事的往事,结尾对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吧。”这与胡绳的自评是一致的。胡绳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
李普对胡绳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心有戚戚然”,对他自己也适用。李普总结自己说:“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李普把第三阶段喻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他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成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他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李普晚年多次说自己在“补课”,补思考之缺憾。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家李普”在学术思想界也叫开了。李普说,他不是思想家,顶多是个“思想者”:“思想家只能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还要大声疾呼大家都思想。拿我自己来说,学养不足,年已八十又二,这辈子是做不成思想家的了。但是,不论年老年少,人人应当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个人而言,要脑袋何用;就社会而言,要知识何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脑袋,理应走在社会前列,首先自己要想,要独立思考。”
“有幸遇到了她”
李普长着一张娃娃脸,始终是笑眯眯的形象。他充满睿智幽默的谈吐,让人感觉到这老头一生是快乐的。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好伴侣沈容。
李普与沈容结成伉俪,是在重庆《新华日报》期间。那时,李普是编辑兼专栏作者,沈容做翻译,向读者译介国外的信息。两人都是周恩来的部下,周恩来直接关注两人的婚礼。他对沈容说:女儿出嫁是件大事,要办得正规一点儿。第一要通知家庭,家里同意不同意不去管他,但必须先通知;第二要在报上登个“结婚启事”;第三还要请一位有名望如沈钧儒那样的大律师证婚。
婚后,李普和沈容携手相伴,不管是在历次政治运动,还是在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十年,互相牵挂。到晚年,生活上是“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在思想上也相得益彰:李普在“补课”,在反思;沈容也在回顾,在反思。李普写下了《洋女婿土老帽》等反思作品,沈容则出版了《红色记忆》一书。此书是沈容回顾性散文的集成,记录了她从投身革命到晚年的经历,又以红岩村、西柏坡、钓鱼台三地的记忆为主,记叙了从革命到和平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幻,展现了高层领导人的活动片断。有记录,有反思,更有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因而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
2004年12月15日,沈容去世。追悼会上,李普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的心里。我相信,她还会活在万千个读者的心里。”
《红色记忆》在沈容去世后才面世,李普在送给笔者的书中夹了一张字条,内中写道:“奉上《红色记忆》一本,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是怎样走的。”“虽然她比我小四岁,最后让我来承担这苦痛,应当说的确比较合适,也可见她比我有福气。”“我多么希望真正有阴间,有前生、有来世。我有幸遇到了她,相伴六十年,这福气也是前世修的吧。”李普并赋诗一首:“相伴六十六载,辞别何其匆匆;应恨不曾教我,如何度此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