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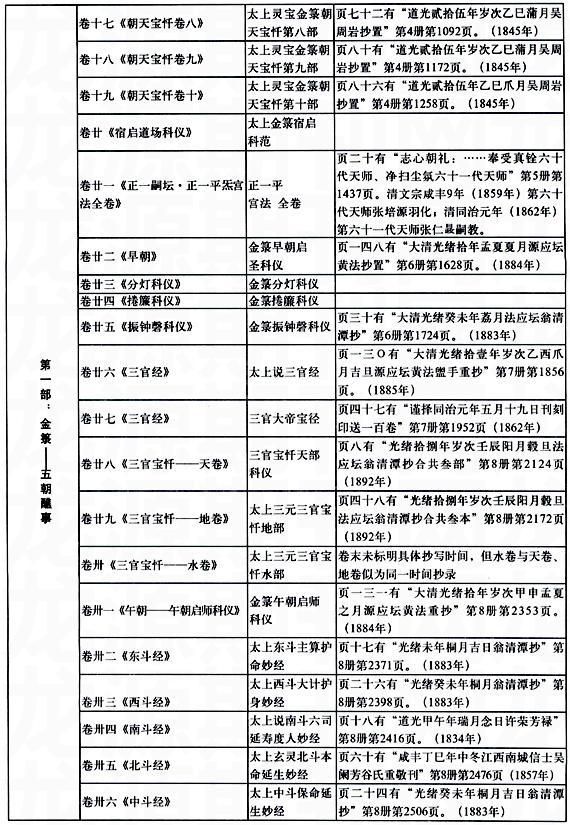

明未清初,王岱舆出于“不使天下公理废而不传”的目的,在阐释伊斯兰宗教思想时,有意识地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进行比较,辨析它们的同异,揭示二者之间某些范畴学说的相近性并加以融合,从而开启了“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的先河,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了中阿和回汉文化交流,对当代宗教对话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伊斯兰教儒家道教佛教
作者:杨兆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
当今由于技术、通讯的巨大改善,人类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出现了空前的交流和共融,而且在精神层面上的接触也日趋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不仅仅是交流与理解的手段,而是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与其它对话样式相比,宗教对话深及参与者的心灵或精神,触动他们各自的根本信念或终极关切,是一种“深层的或根本的对话”,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宗教思想家们的关注,但由于不同宗教的信仰观或真理观是多元化或多样性的,甚至是相冲突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对话方式。而明末清初(17世纪中期),“四教博通,诸家毕览”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发前人之所末发,言前人之所不敢占”,在以伊斯兰教为本位的基础上,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进行比较、借用并加以有机整合,对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做了最早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对当前的文明交往和宗教对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一、矢志以汉书的“真回老人”
王代舆(约1580-1660年),号“真回老人”,“是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第一位系统地研究伊斯兰哲理并刊行其汉文译著的宗教学者。”他“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末,帝心欣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徭役,与国始终。三百年来,虽于此习熟之久,然而溯本推原,不敢有忘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岱舆自幼就开始接受伊斯兰教教育,及长师从金陵著名学者马忠信,熟读伊斯兰教经籍,成为一名饱学经文之士。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自称:“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渐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并在“稍通大义”后,“觉其议乘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宵壤。不自揣度,谬欲立言明厥至理。”宗教“只知其一者,则一无的知”,而王岱舆对四教的深入研究,就为其“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在穆斯林心目中,真主“降示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以便他们敬畏,或使他们记忆”,他们相信真主最终是用阿拉伯语以无比力量和直率说话,阿拉伯文是纯正的宗教语言,因而担心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会影响教义教理的纯正。一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问,仍有人认为“凡以一句‘哈他(译日差错)文字,杂于清真,真主之慈即止,而罚且随之。若以‘哈他文字,注释正教之经旨”,就与伊斯兰教义的宗旨大相违背,因此“言教道不如口口,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但“道不大著,教恐中湮”,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岱舆以特有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论证了用汉文翻译伊斯兰经典的合理性,认为“文字比如土木,可以建礼拜寺,可以造供佛堂,正道异端互相取用,其功过不在材料,唯论人之所用何如耳。……由是言之,明命圣谕,何尝拘于一方,无非便于世人,本为阐扬正教,岂区区执于文字也哉”,王岱舆在“言清真之道”时,还“授引诸家,彼此辩论”,阐述得恺切诚恳、精确得当,有利于“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
二、历史与文化背景
明未清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教众中黄童白叟不知所钦遵,黑汉村愚亦不思所恪守,就连教内阿訇也因不精通“天房文字”,而不能对教义有深刻理解,某些达官贵人和豪族大姓甚至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面临“生存危机”。这种衰危局面,是王岱舆将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动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的支持与否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虽有明太祖“洪武元年敕建礼拜寺于金陵,御书百字赞,褒美清真,以示优异”;明世宗“敕名净觉寺,行令礼部给与札付,冠带荣身,仍准免差摇,令供职焚修”等一些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政策,但明朝历代皇帝为了“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生),对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实行强制性同化政策。例如洪武元年(1368年)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大明律》还明确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若“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类日滋也”,其同化用心不仅大大冲淡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而且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第二,伊斯兰教从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后,“仅恃习俗渲染,口头上之授受,血统止之遗传,阿拉伯文之讲解,以为传授之工具,故宋、元之时,犹无人以中国文字解说回教教义与礼节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结果使许多回回穆斯林对于教门只是“沿其性,不得其真迹”,不能对伊斯兰教教义有深的理解,呈现出“兰台石室之藏,浩足充栋,但俱国音中幅之人,无一晓者”的局面,限制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的传播方式,不仅使教外人士无法理解伊斯兰教教义及其文化,一些统治者的猜忌和疑虑,这使回汉之间的文化隔阂日益突出。因此,伊斯兰教信仰在中国要得以世代相承,就必须面以地和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寻觅宗教文化的民族载体,是外来宗教文化得以在异地生根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社会性载体在每个历史时期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唐宋时期,落籍中国的阿拉伯、波斯等国的穆斯林分地聚居,“被称为‘住唐,后来,这些‘住唐娶中国妇女为妻,繁衍子孙,逐渐演变为‘土生蕃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元代,随着蒙古大军西征而来的大批阿拉伯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作为商人、士兵、手工业者、宗教职业者及上层人士,散居全国各地,形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从“土生蕃客”到“回回”,虽然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性行为,但实质没有变化,即: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社会性行为,而是一种个体行为,其载体是单个的穆斯林。到“明代三百年中,回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一旦形成便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和防止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的机制与能力,这就使回族不仅成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新社会载体,而且逐步演变成为在中国维护和发展伊斯兰教的中坚力量。但由于中国回族穆斯林“大分散,小集中”,处于汉文化

汪洋大海氛围中,不掌握汉语就不能进行社会经济与文化活动,就无法顺利生活下去,久而久之,对外接触面愈广泛,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愈强烈。
因此,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寻求一条既能保持自身固有的伊斯兰宗教方式传统,自立图存,又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结合,让教外人尤其是封建统治阶级明了、理解、接纳伊斯兰教的有效途径,是很有必要,也是极为迫切的。
三、“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独特的宗教对话方式
“不同民族群体所具有的多样性、特殊性的文化内容往往是用普遍性的框架组织起来的,不同文化在终极价值和一般性伦理约定等方面是非常相似的。”故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虽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但二者存在共同关注的话题与焦点,在理论思想上有着某些共同点和相通之处。例如,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都重视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说和讲究道德修养,《古兰经》、《圣训》中对夫妇、父子、邻里关系的处理有详尽的规定,“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人训责自己的父母,是大罪。”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等伦理道德观,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二者都发挥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有机体存在的功能,这为其交流对话提供了潜在的基础。因此,王岱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并没有排斥,而是认同和尊重:“宇宙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理尽义极,无复漏遗,至正大中,绝去偏颇,非此则人道不全,法治不备,此儒者之道之所以不易也。”王岱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为其进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革新提供了前提条件。
“思想开始于语言”,不同宗教,使用不同语言。宗教对话不需要译成通用的中性语言,但“可以对每一种语言作具体的诠释,这种诠释的目的是让人可以以知性方式相互接近。”因此,王岱舆在著作中常常借用、移植儒、释、道的一些术语、概念、命题来看待、解释、宣传伊斯兰教思想。例如,他在阐述“真一”这一命题时说:“数之一,非独一也,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数之一也;曰‘一本万殊,‘万法归一,亦数之一也”,并认为“真一”并没有脱离人的自身,假若脱离人的自身而谈论空泛的道理,属于荒诞无稽之词,因为“人之本性,乃无极之样式;此身之本质,即太极之证明。首圆象天,所以轻清者上升,属阳也;足方象地,所以重浊者下降,属阴也。五脏按五行,通身类万物。其行止知觉,虽由无极之性灵,孽生百骸,固出太极之本质,然其生死穷通安危得失,概不由本性本体所能自传。即此便知,无极虽受真主之命代理乾坤万物,其生死贵贱之权,必不由无极太极所能自主也。”这里,太极、两仪、四象、无极、阴阳、清浊、五行、乾坤等术语、概念不是伊斯兰教固有的,而是源自中国儒家思想。这种借用儒家语言行别是宋朝理学来阐述伊斯兰教思想的情况,在王岱舆的著作中俯拾即是。另外,王岱舆还大量借用道家、道教和佛教术语,如“人极玄枢,包罗万象,有无造化之希微,尽载此身之古册。”这里的“希微”在《老子》中指“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河上公注:“无声日希。言一无音声,不可得听而闻之。无形日微。言一无形体,不可博持而得之”。王岱舆在阐述性情时,分为真性和禀性,“禀性者出于身体,本干四大,”“四大”是佛教用语,指土、水、火、风四大元素。当心性返还到宇宙万物初现时的太极境界,即心意回归正道时,“真如已见,太极已圆,众妙之门已开,有无之道至矣。”“真如”,佛教词语,指真实如此之本来面目,恒常如此,不变不来,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即无为法,亦即一切众生的自性清净心。此处指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其心性所达到的清规戒律静境界。
王岱舆在阐述伊斯兰宗教思想时,不仅大量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语言,还采用它们的模式,甚至借鉴亦或吸收了部分儒、释、道的思想,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王岱舆在本体论中,将伊斯兰教“真主独一”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太极说”相结合,把伊斯兰教的认主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了新的发挥和概括,提出了一套自己的宇宙论学说。首先,用“真一”这个概念来强调真主安拉作为世界本原的突出地位:“真主止一,无有比似,乃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真一本然非从所生,亦无从生,无似相、无往来、无始终、无处所、无时光、无抑扬、无开合、无倚赖、无气质、不囿物、不同特”,即“真一”就是真主安拉,并强调指出: “须知真一乃单另之一”,“真乃独一耳,因道契于真,故能不更不易,始终一理。不得真一,则根不深;根不深,则道不定;道不定,则信不笃,不一不深不笃,其道岂能久乎?所以正教惟尊兹真一也”。接着展开论述,“盖辨一有三:曰‘单另之一、曰‘数本之一、曰‘体认之一。单另之一,乃天地万物之主也;数本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寥寥数语概括了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是“万物之主”、“万物之种”、“万物之果”,并隐喻真主创造宇宙的程序是:真一(真主)——数一(太极、无极)——人类和万物,与宋明理学的宇宙发生论:太极(亦称无极)——阴阳——人类和万物大体一致。这既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同时又吸收了儒家思想,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宇宙创世论。在伦理观方面,王岱舆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伊斯兰教的“敬主爱人”理念融合更为贴切,推出了一套既有别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伦理规范,又不同于中国伦理准则的伊中合璧的伦理体系。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忠于独一无二的真主,是不容改变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故王岱舆强调:“吾教自生民以来,不拜像,来诸邪,方谓之清静;尊独一无二主,方谓之真忠。”“经云:‘尔等拜主,尔等孝亲。是故事主以下莫大乎事亲。孝也者,其为人之本钦。道德所以事主,仁义所以事亲。真忠者必孝,行孝者必忠,忠孝两全,方为正教。”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王权高于神权,伊斯兰教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就需要具有忠君思想。因此,五岱舆明确指出: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他更进一步引申为:“人但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而不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者,则前事亦不足为功;如徒忠君、赞圣、孝亲、济人,而不能顺主、赞主、拜主、感主之恩,则前事仍为左道。”这里把宗教伦理的“敬主”说、社会伦理的“忠君”说、宗法伦理的“孝亲”说三者统一,鲜明地反映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特点,确定了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中重要的地位。
四、捍卫伊斯兰教正统性——宗教对话的基本原则
“宗教对话并非在简单意味着:对其他的宗教传统或别人的宗教信仰抱什么态度;而是从根本上关系到:怎么解释现存的诸多相冲突或相矛盾的宗教真理观。由此来看,关于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