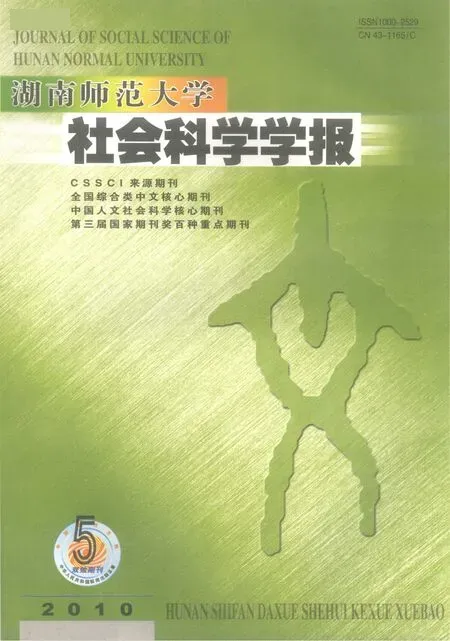无言之美
——论康拉德小说的“空白”叙事艺术
邓颖玲,简剑芬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4)
无言之美
——论康拉德小说的“空白”叙事艺术
邓颖玲1,简剑芬2
(1.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4)
艺术空白是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现象。康拉德在小说创作中善于运用“空白”叙事手法增加作品的信息量、召唤力和艺术感染力,使读者获得更多的审美自由和审美愉悦。空白艺术的引入不仅使康拉德可以多层次、多角度、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复杂的现代经验和多变的社会现实,而且大大提高了他作品的丰厚性、含蓄性和作品题旨的多义性。
康拉德;小说;空白艺术;审美愉悦
一、引 言
“空白”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不仅是作家寻意索境的载体,也是作家托物寄情的手段。关于“空白”,中外理论家和作家有诸多相似的论点,如老子的“大象无形”,梅尧臣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波德莱尔的“象征”,新批评的“含混”,英伽登的“不定点”。上述观点虽然存在着文化背景和理论背景的差异,但都明确地表明,真正成功的文学作品,其文本意义不应该是确定和完结的,而应当是含蓄、含混,布满“空白”。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明确指出,“任何一部作品,不论它多么严密,对接受理论来说实际上都是由一些空隙构成的作品,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一些看来靠读者去解释的成分”[1](P80)。
“空白”的含义极其广泛,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既指视觉形象、艺术结构的形式空白,又有寓寄的、情感的内容空白;它既指文本设计,又包括读者反应。就文本设计而言,“空白”是指语义单位之间的空缺及意义的隐含表达;是文本中未实写出来或明确写出来的部分;是“用来表示存在于文本自始至终的系统之中的一种空位”[2](P249)。就读者反应而言,“空白”意味着读者因文本的不确定而产生的视界上的模糊性和判断的多义性。它是以模糊的、不确定的表达来激发和诱导读者的想象和联想,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作品中提供的内容进行再创造。因此,“空白”既包括语言文字的形式空白,也包括审美意象的空白;它属于有意省略、空缺的部分,蕴藏着审美潜能和艺术张力。
新小说派领袖罗伯·格里耶说,“空白”是造就文学生命运动和生命活力的源泉。[3](P204-205)康拉德创作小说的年代,适逢西方多元化审美批评和美学思想风起云涌的开始。他从自己的审美体认出发,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摒弃了19世纪后期人们所喜爱的繁缛辞藻,而且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实验。他的小说中不仅渗透了散文、诗歌等相邻艺术的特点,而且还借鉴了音乐、绘画中的艺术手法,其中“空白”手法的巧妙运用使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含蓄与凝练,达到了虚实相生、“味外之味”的艺术效果。
二、省略或含混造成的语言空白
20世纪语言学转向后,作家们认识到语言自身的表现潜质和意义建构功能,更多地使用沉默、中断、叙事要素的缺失等方式来构造小说,以超越语言自身表达的有限性。康拉德也像其他现代派作家一样,具有很强的语言意识。他擅长通过语言的省略和表达的含混来表达隽永含蓄的意味和言外之意。著名批评家罗伯特·潘·沃伦在谈到《黑暗深处》时就说,“在其中寻找确切释义,就如同企图在莫扎特的交响乐中找出确切释义一样徒劳无功”[4](P21)。康拉德在作品中经常用“也不知”,“未见真切”、“不敢纂创”等词语对一些情节或材料作空白处理,甚至类似“我看到”与“我没看到”等一些前后矛盾的表达也可出现在同一语境中。马洛在讲述他的非洲之行时,就这样描述道:
此外,按我判断,我还认为两岸的密林显然无法穿过——可是里面却有许多双眼睛,它们能看见我们。河岸边的丛林无疑非常浓密,可它后面的乱草丛看来是可以穿过的。无论如何,在浓雾暂时消失的那一刻,在整个河道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独木舟——至少肯定没有一条和我们的船在平行的位置上。但是,真正使我感到不能设想他们会进行攻击的,是那声音——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阵喊叫声的性质。[5](P578-579)
这种前后不一、模棱两可的表述,表面上造成了文本意义的模糊、晦涩和不确定,实际上是马洛意识迂回及感觉变幻的体现。作者刻意追求的这种相互矛盾的主观性判断,使整个非洲之行和对马洛的认识过程成了一个捉摸不定的谜。康拉德藉马洛之口表达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东西。此外,作品中库尔兹在临终前喊出的“可怕啊!可怕!”两个孤零零的词组,其意义也扑朔迷离,含混不清。到底什么可怕?是库尔兹为自己原有的理想与后来的所作所为之间产生的强烈偏差感到可怕?还是对欧洲这个所谓的“美好世界”感到可怕?作者并没有究其原因,文本本身也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康拉德有意识地造成这两个词语语义表达上的含混、模糊,给读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
在《吉姆爷》中,康拉德对吉姆这个中心人物也进行了模糊处理。他极力避免直接描绘吉姆,尽可能采取迂回的途径,间接地描述他。在第一章第一行,康拉德这样描述道:“他差一两英寸不到六英尺,体格健壮,他直冲你走来……令你想到一头正冲过来的公牛。”[5](P6)从身高看,吉姆并不高大,缺乏英雄人物那高大的身躯和俊美的面孔。可是,在第十四章的最后一段,马罗在描述吉姆时说道:“我什么也没说。我迅速地想象着吉姆站在一块豪无遮拦的岩石上,站在没膝的鸟粪中的情景,满耳是海鸟的叫声,头顶上是灼人的太阳火球;空荡荡的天,空荡荡的海都在颤动,在目力所及的地方一起因炎热而沸腾着。”[5](P142)这分明是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这两个大相径庭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对吉姆作出评价时的矛盾心理,表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模糊和晦涩。此外,文本始终没有出现过吉姆的真实姓名。吉姆没有说过,马洛也没有提及。作者让小说里的每个人物都从自身独特的视角来定义他。在马洛眼里吉姆始终是“内心深不可测”[5](P361);他仿佛身在迷雾中,只是偶尔让马洛窥见一星半点内心的秘密。即使对最爱他的妻子珠儿来说,吉姆“也一直是一个残酷而不可解的谜”[5](P341)。海盗布朗临死前也不理解吉姆:“我看不出他是谁。他是谁呢?”[5](P334)除了马洛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如法国少尉、英国船长布莱尔利、西澳大利亚人彻斯特、北欧人埃格斯特朗以及罗宾逊和斯坦因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吉姆进行叙述。每个人在多重交错的视角下,吉姆这一中心人物显得模糊、难以捉摸,似乎总是隐藏在宫殿中,神秘而飘渺,可望而不可及。吉姆离弃帕特那沉船的事件也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他弃船而走是我们预料得到的,但是这个关键性的事件作者只是用“我跳下去了……”“大概是跳下去了罢”等模棱两可的话进行描述,而对整个事件的某些细节和具体环节却进行省略、虚化和模糊处理。这种跳跃式的叙述构成了情节空白。它在启示读者,现实由于空白的存在离我们很远;语言已无力重现这个对吉姆极为残酷的现实。
三、间接叙事与语言的不确定性
读者在阅读康拉德的小说时,常常会读到一些表达不连贯的文字或多重叙事声音。他的几部小说的主体部分几乎囊括在无数的双引号与单引号之内,以层层间隔的叙事模式拉开语言与现实的距离,造成时空的间隔和文本的不确定性。
在《黑暗深处》中,马洛和“我”两位叙述者各司其职,交替叙述。马洛以第一人称对“我”讲述他的经历;“我”再对读者直接转述他的故事。层层叙述,层层转述,有时让读者摸不清头脑,理不清究竟是谁在讲故事。而恰恰是各种不同的叙述声音,不断变化的视角,让读者远离了事件本身,使现实、马洛、我、读者层层间隔开来。此外,马洛与主人公库尔兹之间也存在着间隔的关系。虽然马洛是直接叙述者,但他与库尔兹除了在结尾部分,并没有多少正面接触。他对库尔兹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零散的文件或报告,缺乏完整性和可信度。正如在黑暗中追寻库尔兹的马洛所感觉的那样,“我跟你们一样,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你们见过他吗?你们见过故事里的事情吗?你们见过任何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我是在给你们讲一个梦——完全是白费力气,因为对梦的叙述是永远也不可能传达出梦的感觉”[5](P554)。因此,读者面对的语言文本是经过两位叙述者转述,带有强烈主观色彩。这种叙述的叙述,客观上造成了语言与现实的背离,再加上叙述者材料的不确切,使文本充满了不确定点和空白。
在《吉姆爷》中,马洛的叙述依然占据了主要位置。但与《黑暗深处》不同的是,马洛与另一位叙述者之间并不是转述的关系,而是由另一位叙述者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描述开头,再由马洛以第一人称叙述他对吉姆的印象。小说中马洛的许多叙述内容都是他从吉姆处听到的。吉姆对他的海上经历做出解释;他的解释被马洛重新解释;马洛的解释又继而被他的听众解释。因此,读《吉姆爷》就像是进行一次没有休止的诠释过程。马洛对自己的叙述这样评价道:“你们没有见过他,听他的讲话也是间接的,所以我无法对你们解释我的感觉的复杂性。”[5](P79)因此,他只能“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好把它的存在,它的现实传给你们——这是在那片刻的幻觉中揭示的真理”[5](P279)。这些话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所接受的是间接信息,所听到的语言与所描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异,需要仔细揣摩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此外,这部小说中同时融合了其他几种叙述方式。从小说的整体布局来看,前四章为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作者躲在马洛的背后,以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身份,将影响吉姆命运的关键事件全盘托出。第五章至第三十五章由马洛以第一人称叙述,他以讲故事的方式,回忆了吉姆命运多舛的一生。最后十章主要为第一人称书信体叙述,转述了吉姆一生最后的生活经历,包括马洛的“说明信”、吉姆的信——“一张散开的淡灰色的方纸”,还有从马洛信里掉出来的别的信——吉姆父亲写给吉姆的信。信中有信,叙述中有叙述,层层间隔的叙述模式无形中否认了语言表达的最终准确性[6],使通过“互为对照的语言风格展示出来的不同眼光处于经常相互冲突和挑战的状态之中,赋予作品一种争辩性质的动态结构”[7](P190)。这种间接叙事使小说充满一种“对话的泛音”[8](P178),进一步扩大了小说解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和小说的可读性。
康拉德故意通过间接叙事和叙事角度的转换拉大时空的距离,时时提醒读者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已有变化的;他所讲述的一切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这种间接叙事造成了文本表达的含混,形成了叙述上的不完整和空白。它促使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观察文本,面对语言与现实的距离,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凭借自己的经验,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揣度,去填补,去参与小说的创造,以完成小说的未竟之义。
四、叙述的断裂与不连贯造成的情节空白
德国著名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在他的《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学本文应具有结构上的“空白”,以留给读者再创造与想象。他强调,“‘空白’存在于文学本文的各层结构中,最明显的是存在于情节结构层上”[2](P266)。康拉德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之一。在他看来,传统小说的完整结构完全出自作家的虚构,是不真实的。现实不是按照人们的逻辑安排的,它远远超出人们的感知和认识能力之外。因此,他在创作小说时不按时间顺序安排情节,不向读者提供主客观世界的完整图景,而是有意割裂事件的完整性,隐藏事件发生的逻辑性,人为留下叙事空白,以表现多层次的想象空间和丰富含义。
《间谍》一开始便将读者带入云雾缭绕的谜团之中。小说没有一个连贯的叙事线索,充斥其中的只是一些看似孤立、扑朔迷离的事件。作者在讲述这些似乎没有关联的事的同时,不断进行时空切换,对大量的事实及其真相进行省略和空白处理。小说以“维尔洛克先生一大早就出门去了,名义上是把商店交给他妻弟照管”开头[9](P1),但随着他一出门,他的行踪立刻从读者视野中消失,叙述随即转向了他半是商店半是住房的家。在第二章里,维尔洛克先生又出现了,但在他这次出门见到了改变他懒散生活厄运的始作蛹者后,叙述又转向维尔洛克先生那个永远是黄昏或傍晚的家。第四章作者运用了时序倒错,故事时间直接跳到一个月后。这一个月的故事省略成了叙事时间上的“空洞”,暗含了中心事件的缺场。读者无从知道格林威治爆炸案的细节,不知道斯迪威被杀的详情。第八章过渡到第九章是个十天的中断叙述,“维尔洛克先生在欧洲大陆逗留了十天就回来了”[9](P161)。十天的空缺带给读者中顿感,使读者猜想他欧洲之行的目的和转变。第十二章向第十三章过渡时,又是一个十多天的中断叙述。[10]这些重要的场景省略就成了一个“谜”,成为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故事的发展、高潮和结局均被这个揭谜过程所牵制。莱昂·埃德尔在评论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时说:“大师在玩火,却没有烧到自己的手指。他创作了一部小说,里面所有‘重大’的场景——所有读者‘期待’的场景都省略了”。[11](P452)这句话用来评价《间谍》一点也不为过。这种割裂再重组的创作手法正是康拉德叙事艺术的非凡革新,使作品表现的残破、碎片的主题意义得到充分体现。
《诺斯托罗莫》是康拉德的一部长篇社会小说。它具有史诗般社会长篇小说的全部特征——贪婪的权力之争、恢弘的战争场面、无处不在的贪欲和众多复杂的人物。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小说。康拉德并未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故事,而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将故事“肢解”,将在时间和空间上相距甚远的事件、场景、意象并置起来。通观《诺斯托罗莫》的整个构架,读者会发现小说中除了许多零散的画面外似乎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整部小说由三部分组成,共二十九章。第一部分叙述的是高尔德开发桑·托梅银矿,其中穿插许许多多没有时间关联的片段:里比厄拉政府溃败、国家中央铁路的破土典礼、蒙特罗兄弟叛乱等。第二部分讲述的是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驾船将银子埋藏到大伊莎贝尔群岛的经历。其中,作者以空间剪辑的方式将古斯曼·本托的暴政、里比厄拉政府的建立和土匪赫尔南迪兹的故事并置其中。第三部分围绕萨拉科的分治以及诺斯托罗莫的沉沦而展开。小说从故事的中间部分开始叙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大半部在时间上是倒置的,直到德考得在暴乱当天写信记叙正在发生的枪战,主要事件才开始。康拉德在《诺斯托罗莫》中有意打破小说情节发展的自然时间流程,在小说的章与章之间,甚至在同一章之间前后大幅度来回跳跃,进行时间错位,将故事的主要情节和线索加以模糊化,有他自己的用意:避免线性地看待和描述事件的发展,要求读者主要关注的并非事件本身,而是小说人物的精神活动与内心世界。这种结构上的空白为多角度表现人类历史和现实本身提供了便利,可以避免读者线性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它要求读者关注于事件本身,在一系列流动变换的事件中去发现、体验和感悟小说中所揭示的超越时空的历史观。[12]正如虞建华教授所说,“叙述上的跳跃和断裂同时也迫使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共同感受历史的突兀与残破”[13](P52)。
五、结 语
中西美学家都将“空白”视为一个涉及艺术创作内在规律的美学概念,对“空白”的美学价值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苏轼的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道出了“空白”的无限蕴涵。司空图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14](P102),严羽的“凡得文妙处全在于空”[15](P102),都道出了空白艺术的精髓。作为爱德华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康拉德不仅继承了由亨利·詹姆斯开创的英国小说实验与改革的传统,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他在小说创作中,大量引入“空白”艺术形式和技巧,在无字处巧心经营,从容地表达出复杂的现代经验和多变的社会现实。这种语言和情节上的空白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作品的信息量,而且还增加了小说的召唤力和艺术感染力,使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含蓄与凝练,难怪利维斯称他为“堂堂正正的职业艺术家”[16](P219),“位于英语—或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16](P257)。
[1]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 杰,傅德根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霍桂桓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3]陈 侗等主编.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第3卷)[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
[4]R.P.Warren.“The Great Mirage:Conrad and Nostromo.”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Joseph Conrad’s Nostromo[M].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 House,1986.
[5]康拉德.吉姆爷 黑暗深处 水仙花号上的黑水手(熊蕾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吕洪灵.“康拉德的语言危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3):86-89.
[7]申 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8]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译)[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9]康拉德.间谍(张 健译)[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10]邓颖玲.《间谍》的时间意义探讨[J].外国文学研究,2006,(2):93-98.
[11]Leon Edel.The Life of Henry James[M].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
[12]邓颖玲.《诺斯托罗莫》的空间解读[J].外国文学评论.2005,(1):32-38.
[13]虞建华.解读《诺斯托罗莫》——康拉德表现历史观、英雄观的表现手法[J].外国文学评论.2001,(3):50-56.
[14]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孙昌熙等校点)[M].济南:齐鲁书社,1980.
[15]严 羽.沧浪诗话(郭绍虞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6]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M].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48.
Charm in Wordlessness and the narration Art of Blankness in Conrad’s Fiction
DENG Ying-ling1,JIAN Jian-fen2
(1.Foreign Studie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2.Changsha Aeronautica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Changsha,Hunan 410124,China)
Artistic blankness is a universal art form in fiction creation.Joseph Conrad is adept in employing the technique of blankness to add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his fiction,to increase its vitality and to reinforce its artistic appeal,which gives the reader more freedom of appreciation as well as more aesthetic enjoyment.This paper aims at interpreting the art of blankness in Conrad’s fiction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language deletion and ambiguity,indirect narration and nonlinear narrative structure.It holds that the technique of blankness in his fiction enables Conrad to depict the complicated modern experience and changeable social reality more objectively and multifacetedly,and at the same time enrich the implicitness and ambiguity of his fiction.
Joseph Conrad;fiction;art of blankness;aesthetic appreciation
I106.4
A
1000-2529(2010)05-0112-04
(责任编校:谭容培)
2010-01-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二十世纪英国小说的空间诗学研究”(09YJA752007);湖南省教育厅青年资助项目“现代小说中的空间结构类型及叙事功能研究”(06B060)
邓颖玲(1965-),湖南醴陵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简剑芬(1975-),广东丰顺人,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