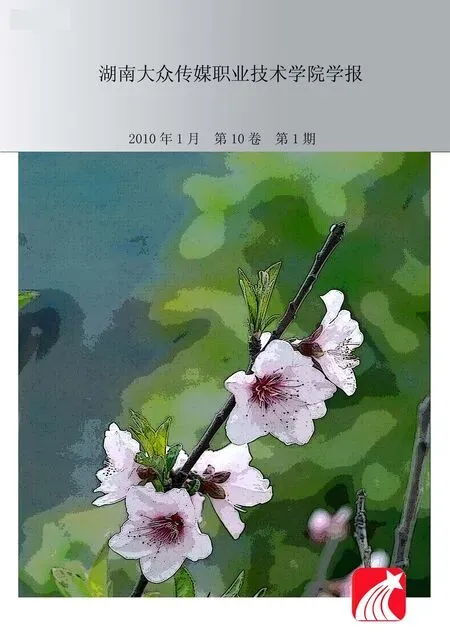试析王韬的报刊角色观
李 滨
(湖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江苏苏州人,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他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又具有丰富的西方阅历;怀抱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却不得不长期寄身报界。“王氏固热中名利之徒,非山林隐逸者流,既引进无门,乃致力著述,以求空文自见。”[1]
自寓居香港、游历欧洲以后,王韬逐渐成为一个对西学的热忱鼓吹者。他在《循环日报》发表的文章最能体现这一点。王韬主张借西国之法以自强,在中国进行全面改革。政治改革是王韬思想中最为激扬的部分。他尤为赞赏的是英、意、西、葡等国的君民共主制度:“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慧得以下逮,都俞吁昲,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2]王韬多次以“三代以上”这一中国古代带有理想色彩的政治境界来称许英国的君民共主制度。上下之交畅达无碍是这种制度的基本特点。在《重民》篇中,王韬反复强调了这种观点:“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在王韬看来,英国之富强,正是由于上下不隔的结果:“英国至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本固邦宁,虽久不变。”[3]与之相对的是专制政体下的君民隔阂:“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2]而君民隔阂即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于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4]通达与隔阂之分构成了近代英中两国命运的强烈对比,则“开议院”以求“通”的政治改良不亦宜乎!
应当指出的是,沟通君民上下之情的思想,早在王韬之前就有人提出了。1859年2月,郭嵩焘就向咸丰帝提出过“通下情为第一义”的建议;[5]在1861年刊行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冯桂芬根据自己对西方的了解,认为中国有五个方面“不如夷”,其中之一即“君民不隔不如夷”。为此,冯桂芬还特别提出了“复陈诗”以通上下之情的主张。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详细阐述了通过报刊求“通”的思想:视报刊为沟通上下的桥梁。
君民共治制度在“通”的政治设计上,主要是“开议院”,然而报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王韬注意到了西报在泰西诸国的重要地位:“其达彼此知情意、通中外之消息者,则有日报,时或辩论其是非,折衷其曲直。有时彼国朝廷采取舆论,探悉群情,亦即出自日报中。”[6]他在分析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时指出:“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7]泰晤士报在当时之崇高声誉,也得益于该报迅速、准确的消息报道。有人甚至认为,该报“声誉是靠首先获得可靠的信息取得的”。[8]但也不能由此而否定王韬的观察。日本新闻学者小野秀雄就表达过与王韬类似的观点:“‘泰晤士报’自二代Walter时期业务蒸蒸日上。他首先使用蒸气和机器在印刷上,布置内外的通讯网,登载著名作家的作品,尤其主笔庞兹(Burns)笔锋尖锐,甚被政界所重视,十九世纪中叶已执伦敦报界的牛耳。”[9]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对泰晤士报“几如泰山北斗”的原因分析:持论必为“庶人清议”,立论公平,居心诚正,反映“人心之所趋向”。在此,王韬实际上是将报刊视为民间“清议”的一个反映和抒发渠道。王韬以他的观察发现,西方政府对报刊“清议”十分敏感,报刊对政府政策的走向常常会产生影响。为此,王韬甚至多次提议,中国宜在欧洲发行西文报纸,以影响西方舆论。他看到,遇有中外交涉之事,在华的西方报纸往往抑中扬外,甚至黑白颠倒。而这种对事实的扭曲又会波及西方的报纸,因为它们的消息来源往往依赖中国口岸城市的记者。国人自设西文报纸则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俾泰西之人秉公持论其间”,“以挽回欧洲之人心也”。[10]
立足于中国现实,王韬还力证了报刊之于“通”的重要意义。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一文中,王韬联系中国古代有关的历史事实和观念,对新报关于“通”的社会角色作了更为直接明确的阐释:
诚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非博采舆论,何以措置咸宜。是以盛治之朝,唯恐民之不议,未闻以议为罪也。及周之衰,上不求谏于下,而下亦不敢以谏其上,然国风、小雅犹能依类托讽美刺,并陈太史采而登之于朝,朦瞽习而播之于乐,则民情之向背,政治之得失,犹恍然而可见。及风雅废而人主益无所闻,奸宄益无所忌矣。夫至人主无所闻、奸宄无所忌而欲久安长治也,其可得乎?昔厉王监谤,而召公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而子产不毁。然则今之新报抑亦乡校之遗意也。[11]
王韬在此突出强调了“新报”的议政职能,认为其承担的正是古之乡校的角色。这种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论证新报合理性的表达方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然更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报刊作为“清议”的一个传播平台,通过将民间对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以公开的方式上传,期望为当局的施政提供借鉴和参考。同时由于其交通上下的地位,对当政者也具有一定的劝惩作用:“其睹一善政也,则忭舞,形诸笔墨,传布遐方;其或未尽善也,则陈古讽今,考镜得失,蔼然忠爱之诚,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由是言之,即新报亦未尝无益也。”[11]
王韬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报刊政论作者。在香港时期,王韬为《循环日报》撰写了为数众多的论说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评论中外政治时事;二是宣扬变法改良,内容涵盖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用人制度、经济政策和外交方略等方面;三是议论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防火、防盗、禁赌、救灾等等。“狂夫之言,圣人择焉”,[12]这些言论以具体的方式实践了王韬的报刊主张。
王韬倡议开议院、通民情,但他向往的是君主立宪而非民主立宪,“议院”的功能也限于“君惠下逮”、“民隐上达”的层面;他热情介绍西学,扩大西学的传播,但又有“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的主张。[13]他的“重民”思想,也是从君主角度谈抚民、厉民、养民、爱民的问题,“旨在为改革晚清的君主专制体制提出建言”,其实质仍是“中国自古以来《尚书》所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民本思想”。[14]这些观念似乎都昭示着王韬的思想整体上仍停留在传统的“君臣之伦”的范围之内。而王韬在报刊与清政府当局的关系的处理上,也印证了这一点:“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15]“君以求治为心,臣自以治乱之道备陈于上前矣。君既与臣下略分言情,则臣自倾城输纳,毋敢隔阂矣。是以古之君臣,际会则风云,契合则鱼水,而有以联家人父子之欢。呜呼!今其见之哉!”[16]
由此观之,王韬虽然对西学西报有广泛了解,但其报刊思想仍然植根于中国古代“文人论证”的思想传统。报刊之传播活动,根本目的是求“通”,以裨补时政、强中攘外。或许可以作一个略嫌简单的总结:在王韬看来,以当政者言之,报刊是“博采舆论”的工具;以办报者言之,报刊主要是建言陈情的平台。只是王韬的建言鲜有见用,令其徒有空言之叹:“四十余年中所以驾驭之者,窃谓未得其道也,草野小民独居深念,惄然忧之。时以所见达之于日报,事后每自幸其所言之辄验,未尝不咨嗟太息而重为反复以言之,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也。”[17]
报刊不仅以“清议”而使下情上达,其日常的传播活动也必然具有“通”的效应。王韬并未无视报刊传播信息、刊载新闻的重要性。从他主办的《循环日报》看,在内容安排上第一版为“香港目下棉纱匹头杂货行情”和“各公司股份行情”的经济新闻;第二版、第三版为新闻版,先后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第三版左上角还刊登有“香港、黄埔、澳门等处落货往各埠”的船期表,此外也常转载《申报》等报纸的文章及报道;第四版为广告。为了争取报份,该报十分重视报道的时效性,每天都发行“行情纸”,遇有最新的重要信息,则出版“号外”。可见,该报的“新闻纸”特质是十分显著的。作为民营报刊,这也是该报得以立足香港报界的重要基础。然而王韬对报刊传播的整体关注,仍然是其“通上下”的政治功能:“一曰知地方机宜也。……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11]
以上分析了王韬对报刊角色的基本定位。另外,王韬也有对报刊教化作用的论述:“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11]不过,这种教化主要源于报刊公开传播引发大众评议而对当事者产生的某种警戒作用。如上文所言,王韬还提出过创办外文报纸以“达内事于外”的主张,其目的是要争取舆论,以在中外交涉中获得道义支持。这就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报刊还可能兼具的角色:社会教化机关和国家对外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