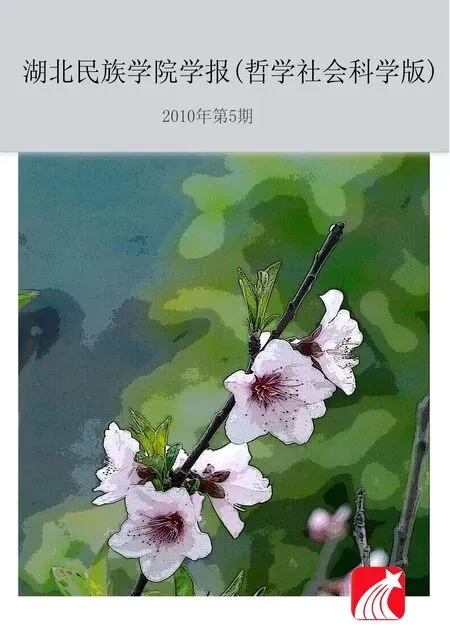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制度分析
潘 宝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制度分析
潘 宝
(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民族文化作为社会多样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受制度的影响而呈现出其特有的形式。但民族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又并非是制度的被动接受者,民族文化通过制度使民族内部与外界建立联系,促进交往,并主动地参与到资本化的过程中并确立自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从而使民族文化以经济的力量保存下来并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化过程中。
民族文化;制度;资本化
民族文化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制度作为这一过程秩序的维持者而决定着资本最终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在各种社会领域中,民族文化的展现本身就是文化作为制度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符号意义的再现,它以民族为划分文化的标准,从而将人类社会区分为不同群体,而不同群体在面临自身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时,对经济力量的谋求与获得就成为民族文化得以不断彰显的动力。群体在利用文化区别与他者不同,也在利用文化努力融合于其他群体之中而避免被边缘化甚至消亡。但当民族文化转化为符号成为群体象征之时,社会各种力量因素如政治、宗教等会随着民族文化资本化这一过程而嵌入彼此的关系网络之中,民族文化资本化也就成为受这些因素构造的制度制约的过程。
一、民族文化特质与制度
民族文化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所塑造出来的,而在民族的框架下审视人类的时候,人类自己也就获得了不同群体多样化的表达,其所表达的事实并非是多个单一社会的简单罗列与叠加,而是各种社会存在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通过对其进行简单的割裂谋求理论意义上的表达。民族文化也就不再是单一民族区别于他民族的标识,而是在与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符号。而制度在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赋予了这种独特符号以意义,就决定了意义表达的方式和途径。各个民族的交往在民族共同体的外部形成了区别于内部的制度,而正是在共同体的边缘民族的特质才表现出与他者的不同。这种内外部制度的融合必然使得民族得以在我者与他者身份的交流中不断认识自己、理解他者。
制度作为社会规则的代表者,其对于民族文化来说似乎是两个互不相关的客体,因为并没有多少人的因素,或者说,人作为制度与民族文化的接受者反过来对其进行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值得商榷。这种制度的惯性也使得民族可以在时间的前后顺序中来追溯自己的历史。无论是民族内部的比较还是民族之间的比较,民族中个体的人的行为是要通过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制度也就在个体的生活过程中巩固了自己并得到个体的自觉遵守,而在这种表面化的制度与行为背后更深层次的是制度所产生的社会事实:制度“使被神圣化了的个体相信,他们的存在是正当的,并且他们的存在具有某种目标”[1],个体的行为也就变成了民族文化作用的行为,其个体色彩在共同文化中能否显现出来或许不是民族真正关心的问题。
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就变成了群体在制度约束下的表达。民族交往中各种方式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人类学的许多资料表明,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从组织生产直到产品的消费都在一定的制度下展开。每个民族的经济活动都与该民族的文化整合行为紧密相关。构成整个经济过程基础性要素的,是一套“人——物”组合。也就是说,经济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二重性的存在”[2],从而民族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社会性的产物,其在经济交往中所表现的自然性也使得各个民族的文化找到契合点,为民族文化的融合提供了制度支持,由此制度的内部约束也同样对外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作用。从而为民族文化提供了资本化的制度支持,交往的动力也就来自这种资本化过程中制度的边缘重合。
作为人类不同群体的一种特质,民族文化在交往过程中也就不再仅仅是自身生活方式区别于他者表达的途径,而是与他民族互相融合、学习的过程,民族文化也就不再纯粹是本民族的原有的、未交流之前的文化,民族若无交流就无文化意义上的展现,“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某些既存特征,但相反,一个民族从不会局限于遗传联系中,也不是一些互不渗透的因素作用的简单结果”[3]。民族文化也就是在吸收了他民族的文化才形成的,民族文化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特质的区别因素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是不同民族不断交往的必然结果,由此也形成了制度来调和不同民族的矛盾与冲突。
因此可以说,民族文化表面所展现的特质与其民族的交往并非是本民族的独立文化,而制度也并非是本民族自己的制度,民族文化与制度在交往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及民族文化本身的制度特性就决定了民族文化与制度不可能独立二分。在经济过程中,资本化的制度性与民族文化制度性两者的结合也就成为一个契合点。民族自身的发展也是通过文化表现出来,虽说外界制度可以影响本民族的文化,但最终还是要通过民族自身主动的改变自己去适应外部世界才能使自身保持已有的优势,“民族的发展有时是一种在受到外力冲击下,自身的一种调适,而最为根本的却是民族文化内部具有的自身发展要求而造成的一种变化。资金、技术的不足是可以用经济学的图表轻易表示出来的,而在这些不足的后面隐藏着的巨大的与经济嵌合在一起的文化上的巨大反差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看到的。历史使我们只能在自身丰富的文化基础上起步。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合理性的根本意义是人类能够发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使各个民族可以尽可能地发挥自身文化的优势”[4]。通过资本化,民族文化原有特质不但可以得到保留而且也在不断的加入进新的元素,而这是民族文化得以保存的根本源泉,也只有在交流与变化中的民族文化才可能成为资本化不断寻求利益的对象。
同时,资本化的制度特质也使民族文化得以更好的与其他民族交流,各个民族在共同利益的追求下可以不断减少民族隔阂,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来使得各种生活方式在交流中被理解并接受与模仿。人类的多样性、多元化是不会随着资本化的表面单一利益的诉求而泯灭的。资本化的过程既是民族发挥象征资本权力谋求自身话语权以便取得更好的发展空间,更是为了不使那些逐渐被边缘化的民族消失的可能途径之一,也就保护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民族文化的特质是会随着资本化而变化的,这种特质的保有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制度是不会因为外界对民族感性的判断而停止其对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也就变成了制度模式下的一种可能性,制度随时间的不确定性正是民族文化特质在民族共时情况下差异性表现的因素之一。
二、制度规制下的民族文化资本化
资本作为社会经济力量的主导因素渗透入社会各个角落,而人类活动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会使各种力量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来谋求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及话语权。而资本转化又不是人主观任意妄为的,而是要受到社会制度因素的制约。民族文化在形成与传承的过程中自身就受到本民族各种社会行为的制约,而当民族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谋求经济利益从而转化为资本之时,民族文化并非是经济过程的被动接受与改造者,而是主动积极地适应资本化之所需的条件。因为经济的非市场化运作在民族文化发展中已经表现了其自身的特殊性,如何把民族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在资本化过程中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则需要遵循制度的秩序,无论这种资本化是追求物质上的货币资本,还是追求精神上的象征资本,抑或其他。“在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场域中的各种资本转换的机制是十分重要的,这就要求人们对资本实现的制度性保障给以特别的重视”[5]。
民族文化的形成正是由于社会制度模式的不同造成的,也因为制度模式的不同,民族才得以以文化来作为自己区分他者的标识。而当经济进入全球化之时,我者变成他者,我者与他者的界限逐渐模糊,民族文化作为对抗现代而以传统自居的中坚力量之时,传统力量的减弱与民族群体中个体接受与消化现代生活模式似乎是不变的格局。现代在消磨个体差异的同时也在力图把民族的标识性特质逐渐以国际标准代替。民族文化资本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可能,其对资本的追求即是对全球经济扩散的制度反应,也是自身对这种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无论这种接受是主动还是被动。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资本化在经济制度的制约下,其自身的存在在问题还未扩及之时,资本化就不失为自身一种主动适应的可能选择道路之一,任何民族文化的存在都与自身和外界的互动密不可分。而制度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纽带,其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在随着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过程而不断调整。一方面,民族文化资本化制度的出发点差异决定了资本化结果的差异,尽管其结果都是为了经济资本反作用于自身的保护;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在资本化的过程中也在建立着区别于他者的新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就会在资本化作用下进一步凸显原来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殊性。面对制度,与其说民族文化是被动的牺牲者,不如说民族文化也在主动参与新制度的构建,因为民族文化已为自己确立了不同于外界的制度规范模式。因此,资本化就不是对自身的全盘否定与简单的模仿他者,而是在资本化过程中使自己不断确立新的地位和经济发言权。当民族文化因自身的特殊性与资本化结果的普遍性融合之时,民族文化也因制度而使内部与外部建立联系,就会不断得到外界接受而获得更多发展空间,从而“理解一个民族文化,即是在不削弱其特殊性的情况下,昭示出其常态。……把他们置于他们自己的日常系统中,就会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他们的难于理解之处就会消释了”[6]。因此说,因制度的联合也使得在资本化过程中,民族文化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契机,从而使自身更好融入与适应经济的制度模式之内。
我们在看到民族文化的这种制度影响下的主被动置换的时候,也应看到无论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无论什么样的制度,当其在资本化的同时,各种社会因素在制度上的反应就变成社会场域之中力量交织的共存关系网络,“社会的各个场域的权利运行、相互间的权利转换以及不同的文化之间所进行的资本的价值转换与实现,都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框架,民族文化资本化也就会因这些转化而实现不同制度间的融合,使民族的文化要素获得新的价值实现的空间”[7]。可见,制度不仅仅是民族文化资本化的规制因素,其同时也为民族文化创造了更好的自我生存与发展空间。由此可以说,民族文化资本化是在制度规制下自身适应经济环境的方式之一,其自身所接受的经济规制与民族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习俗的不同是在资本化过程中需要通过制度调和的两个方面,资本化既非民族文化元素的逐渐丧失,也非民族文化的表面形式,资本化所表现的实质性内容是民族群体保留自身社会生活方式并继续彰显人作为类文化模式的不同。资本化在经济进程中所追求的满足民族生存的物质条件同时,更是为了保持与更新民族的象征资本。制度也就是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多样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激励因素。
因此,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与制度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资本化必须在制度的规制下才能进行,才能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同时制度又对资本化过程中的特殊性产生普遍化的影响。资本化既使民族文化得到了他民族的接受和理解,又使主体民族因为民族文化在经济上的影响而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以利于自身更好的发展而不致于因无法与外界制度融合而遭受排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8],资本化也只有以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作前提条件与其他民族交往,从而使得生产力在民族之间得以流动,促进交往民族的发展。所以说,民族文化资本化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就扮演着主动接受他者文化的角色并努力让外部民族接受自己。
三、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的制度构建
民族文化若想借助经济力量实现资本化,现有制度的存在并非使得资本化过程顺利进行。资本化的制度是在市场条件作用下的经济活动,民族文化如何适应这种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式,是需要主体民族深思的问题。若现有的制度不能使民族文化更好的资本化,代表民族文化的主体就应对旧有制度进行重新的构建,使之适应自身民族文化在市场条件下的运作。
市场各方能否在民族文化上获得利益是其能否资本化的关键。但大部分现有的民族文化自身似乎都缺少与市场完全接轨的制度。我们也就看到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大多由政府所主导的现象。政府以公共管理者为角色对其对象进行经济事实上的干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利益最大化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行政在民族文化上的作用也正是民族文化象征资本利益的实现,这种资本化过程中政治色彩的浓重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自身制度构建的缺失,从而也使得民族文化背后的民族得以在国家背景下通过行政来构建制度推动资本化的实现。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即是这一表现形式之一。但我们应该明白,民族文化自己是不会搭台的,“搭台”这一行为必然是在民族文化具有经济潜力的情况下一种政府行政行为,从而也说明民族文化只有在取得政府所规定的合法地位才能“搭台”。“民族节日符号就这样通过制度化的活动起到了增加民族凝聚力、向外宣传本民族文化、加强与其他民族交流情感的作用的同时,隐蔽地起到了象征资本的作用”[9]。
由此,我们既看到了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了民族文化资本化如其自身一样,是社会场域各种资本博弈的结果,民族文化资本化并非一厢情愿。以民族文化自身的现实情况来说,那些民族节日、民族服饰、民族工艺等只是民族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众多的形式在构成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在质疑外部世界、反思自身——所谓的民族文化即是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所表现的制度方式在资本化运作的情况中在多大程度满足了人们不使民族特色丧失的情感需求?又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行政利益而盖以地区经济包含民族经济的普遍化事实?所以,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制度构建就不是民族文化主体自身主观的构建,而是民族内部与外部不断交往的结果,没有交往就无所谓民族文化。而在资本化之后的民族文化是否还是原汁原味,对于资本化来说没有多少实质意义,“有时,这些影响会把那些不和谐的东西重制成一种新的和谐,从而获得一种和他们的原有文化根本不同的结果,但是他们的行为中又带有原来那种文化的痕迹”[10],资本化过程中的制度构建也就是在调和资本化前后民族文化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而表现的结果。
另一方面,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其资本化,围绕着制度所构建的还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至于这种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在群体之内的归属是无法用制度精确测量的。制度构建也就只获得了民族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臆想,因为民族文化抽象为一种符号时,符号是不能通过制度构建对其进行有规律的资本化,资本化的对象是民族文化通过对符号施以经济上的变革,而资本化又是经济制度的反应,“符号与制度结构间的这些关系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这些符号并没有形成社会中的某个独立王国;它们的社会相关性在于人们运用它们来证明或反对某种权利安排,以及在这种权力安排中有权力者所处的位置。它们在心理上的相关性在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成为依附或反对某个权力结构的基础”[11],由此也就明白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中,政治力量的介入及制度构建的官方色彩。而作为资本化对象的民族文化及其代表者民族来说,或许就是在这些力量所形成的关系网中无意识的随着制度而改变。
民族文化资本化也就变为民族、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由这些因素组成的社会的相互影响的结果,而这些因素背后所形成的运作制度是否与这种资本化一起再次被制度化?资本化的过程已经说明了围绕着民族文化所形成的各种力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是无法继续存在,各种力量的矛盾冲突也正是资本化必经之路。于是对于资本化过程中的制度构建也就成为这些因素各自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当民族文化是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以工业化、城市化和商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进程中[12],民族文化的资本化也就不再仅仅简化为民族自身的存在问题,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M].褚思珍,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0.
[2] 马翀炜.制度要素与社会发展[J].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3):22.
[3]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M].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2.
[4] 马翀炜.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J].南宁:广西民族研究,2001(2):29.
[5] 马翀炜,陈庆德.民族文化资本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248.
[6]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8.
[7]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
[8] 马翀炜.经济转型期的云南少数民族节日符号[J].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2):71.
[9]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08.
[10]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9.
[11] 平锋.生态性原则:现代化语境中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基本原则[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72.
责任编辑:杨光宗
G03
A
1004-941(2010)05-0157-04
2010-08-20
潘宝(1985-),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