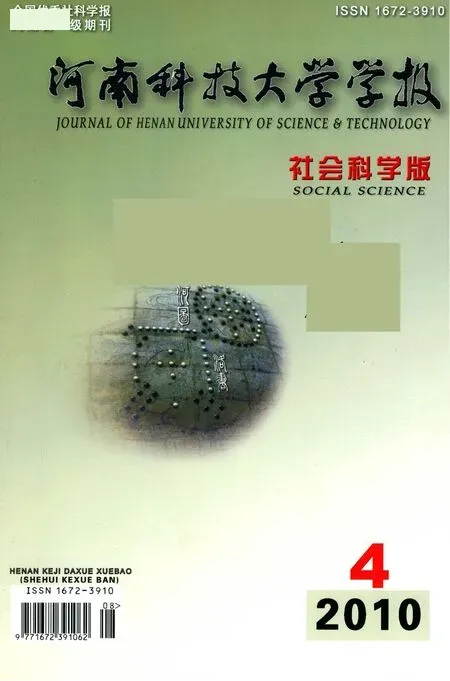试析《红楼梦》之“情”
谢德俊
(泉州师范学院应用科技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试析《红楼梦》之“情”
谢德俊
(泉州师范学院应用科技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红楼梦》;“情不情”;钗黛合一;秦可卿
《红楼梦》写情主要围绕贾宝玉与黛玉、宝钗之间的爱情关系铺开,在三个人的情感纠葛中,折射出作者所要表现的“情”。一个“情”字贯穿《红楼梦》始末,深入分析《红楼梦》之“情”,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复杂而微妙的情感脉络,而且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悲剧主题。
一、“情不情”:贾宝玉的情感特征
《红楼梦》①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来源:邓遂夫校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 (修订版)》(作家出版社 2006年版)。“楔子”指出“其中大旨谈情”,围绕贾宝玉与以钗黛为首的众女儿之间的情感生活,充分地展示了一个“情”字,“情”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贾宝玉是曹雪芹编织的爱情童话里的中心人物,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②本文所引《红楼梦》脂评来源:朱一玄辑录《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 1986年版)。(庚辰本夹批,第四十六回),其情感触角几乎渗透到小说里所有的年轻女性,对两性的认识从根本上颠覆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态度。在宝玉看来,男人的世界代表的是现实世界,充斥着权力的争斗和利欲的争夺,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令他感到厌恶和痛恨。然而,深藏闺阁的女儿则保持了人性的纯真与善良,即便如宝钗那所谓的“圆滑”,亦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本能意识,她们经常身不由已,命运被男人世界所主宰,这一切都让宝玉充满深切的同情。
脂批曾提到《红楼梦》原稿中有个“警幻情榜”,对小说主要人物的情感特征进行归总评判,“宝玉系情不情”(甲戌本眉批,第八回)。所谓“情不情”,即以“我”为中心而生发的情感,而不论情感投射的对象于“我”是否有情。贾宝玉的“情不情”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好“情情”与“不情之情”,前者为钟情于有情之人,后者为对无情于他者而用情。在林黛玉与薛宝钗身上明显地区分了宝玉的这两种感情。宝玉与黛玉之间是前世缘定的“木石前盟”关系,两人之间似曾相识的心灵感应源于感情上的默契,是一种建立在精神层面上,双方相向而生、不带世俗功利目的的情感;宝钗来到贾家本是为了皇家聘选妃嫔,她与宝玉的“金玉良姻”之说,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符合封建世俗要求的一种结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利益关系,因此宝钗对宝玉来说是“不情”之人。尽管宝钗经常提起的“经济仕途之道”引起宝玉的强烈反感,但并不影响他对宝钗的爱慕之情,是为“不情之情”。就连与他心息相通的黛玉也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第二十八回)
“情不情”的两层涵义在宝玉身上还有不同表现,这就是“情”和“欲”的区别。“情情”以“纯情”为主“欲”为次,如宝玉与黛玉两人,即使同处一床也不会产生非分之想;“不情之情”则以“欲”为主“情”为次,第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宝玉要看宝钗腕上的红麝串子,“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他身上’”。“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褪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而黛玉和宝钗的两个影子式的人物睛雯和袭人,在表现贾宝玉“情”与“欲”的区别上更为直接、明白。第七十七回,睛雯被王夫人疑为勾引宝玉而逐出大观园,宝玉前去探视,晴雯说出心里话:“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可见两人之间有情意而无淫欲;反观袭人,第六回宝玉就与她“初试云雨情”了。可见宝玉并非纯情主义者,小说其他情节也透露了他与丫环之间的淫欲行为。如,碧痕服侍宝玉洗澡,前后足有两三个时辰,“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第三十一回)
警幻仙姑在太虚幻境对宝玉说的一段话,是作者借警幻之口对“情”的阐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宝玉的情感特征:“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第五回)在警幻仙姑眼里,“情”是一个整体,包含了美色 (欲 )和纯情,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情 (纯情)”和“欲”分割对立起来对待。淫欲只是人的自然生理和心理需求,因为产生的动机不同,淫欲行为区分为“好色之淫”和“知情之淫”,这才是区别淫欲是否合乎规范的标准。警幻对没有情感的“好色之淫”不以为然,称之为“皮肤淫滥”。但同时,她也批判“好色不淫”和“情而不淫”,认为这些都只是“饰非掩丑之语也”。可见,警幻并不反对淫欲,即所谓“好色即淫,知情更淫”,这是人性化的情欲观。对于宝玉的“痴情”,警幻则推崇为“意淫”,即为只可心会神通的“知情之淫”。“意淫”从本质上诠释了“情不情”的情感特征,是“情”的最高境界。当宝玉听到自己被警幻称做“天下古今第一淫人”时吓了一跳,急忙矢口否认,他哪知道,自己“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正寄寓着作者对“情”的深刻理解。
二、“美中不足”:钗黛的情感缺憾
读者通常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对宝钗和黛玉作出价值评判,于是形成了“尊黛抑钗”和“尊钗抑黛”两种看法。[1]事实上,钗黛同为才情绝色女子,一个令宝玉倾情,一个最终嫁给宝玉,是对宝玉的人生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人。作者显然是把钗黛作为“双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上下”[2]的两个主要女性形象加以刻画的,两者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样重要。
虽然钗黛形象分别满足了不同人的审美情趣,但“钗黛优劣论”的存在至少说明她们并不是完美的。我们仅从二者的情感特征上进行比较。
黛玉在“警幻情榜”上的评语是“情情”,(己卯本夹批,第十九回)意指林黛玉用情专一,只对自己有情的人用情。比如她只对宝玉情深意重,而对其他人则极少流露自己的感情,即便“葬花”,也只是对花感已,并非纯粹“怜花”。因此,黛玉的情感特征鲜明地表现出精神的个体性,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第二十回《林黛玉俏语谑娇音》,宝玉因和宝钗在一块招来黛玉的奚落,宝玉以“亲不间疏,先不僭后”来解释,林黛玉则啐道:“我难道为叫你疏他?我成了个什么人了呢?我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九回,宝黛因为史湘云的金麒麟而又起冲突,黛玉先是讥讽宝钗:“(宝钗)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后又无端指责宝玉:“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她心中暗想:“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这‘金玉’,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林黛玉把全部的感情投注在宝玉身上,而戴着金项圈的薛宝钗和拥有金麒麟的史湘云,都是对她的爱情产生直接威胁的人。当贾宝玉以“情不情”的态度对待她们的时候,她却始终以“自我”的情感一遍又一遍地试探着意中人。宝玉的情感内涵显然更为丰富,黛玉之疑是因为不能完全理解宝玉的情感世界,他把自己的“纯情”给了黛玉,而把“欲”给了宝钗。因此,当黛玉不理解自己的感情时会气得脸黄眉竖,“下死力砸玉”。宝黛情感冲突的根本原因就是“情情”与“情不情”之间的冲突。
宝钗在“警幻情榜”上的评语,因脂批中没有提及已无法确切知道。根据其情感表现,有人认为是“情时”。[3]宝钗安分随时、少言寡语,在人际关系上显得融洽、和谐,以封建伦理和价值评判标准来看,她是完美的。在感情方面,首先要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如对金钏之死和柳湘莲出家的问题上,她不会去体谅金钏和柳湘莲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而是把他们当做封建秩序的破坏者来对待。另一方面,她又会对湘云体贴细致,用雍容大度化解黛玉的“小家行径”,令黛玉把她认作知己;与宝玉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纠葛,有的只是诚心的规劝与合乎礼仪规范的关心。宝钗的情感不能说是虚假,却不同于黛玉那种自然流露的情感,“情时”的特征非常明显。
“《红楼梦》中有两个贾宝玉,一个是年轻的锦衣玉食时的贾宝玉,他反抗一切传统的束缚,他的口号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作的骨肉’,鄙视‘禄蠹’,鄙视礼法,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他的确更倾心于林黛玉;一个是‘中年后的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贾宝玉,即小说开头出场的那个深自忏悔,痛感‘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我’、‘作者’、‘自己’。此时他关心的是事业,后悔自己做了败家子,因而薛宝钗在他心目中增加了分量。”[4]后一个贾宝玉,在审美情趣上已经与作者一致,即已认可宝钗的“情时”,但仍然因为失去黛玉的纯情而感叹“美中不足”。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对黛玉和宝钗着墨相当,从而形成“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人物格局,表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即“情情”与“情时”的合二为一,这也是宝玉“情不情”的情感需求。事实上,钗黛的情感特征是既对立又互补的两个极致代表,无法互相取代更不可能真正融合在一起,秦可卿的存在可以说是作者将这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理想终归是理想,作者这种尝试不但导致了秦可卿人物形象的模糊不清,青春夭亡的结局也表明作者实际上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能够适合“钗黛合一”的理想人物存在的土壤。
三、知“情”之人:秦可卿
贾宝玉生命里的两位重要女性,黛玉痴情而不识“大道”,宝钗守礼克己而寡情,都不能真正理解宝玉的情感世界,因此无法堪任宝玉知“情”人的角色,真正的知情之人只能是兼美钗黛的秦可卿。
首先,谐音隐义是作者曹雪芹贯用的艺术手法,秦可卿作为《红楼梦》“隐喻性人物系统里的重要成员”,[5]一般被认为是谐音“情可轻”或“情可亲”。[6]这种理解可以部分地解释作者对“情”的态度,但谐音“情可情”也许更能体现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本来意图。老子《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很难想象,对道学思想颇有研究的曹雪芹,在拟出“秦可卿 (情可情)”三个字的时候没有受到《道德经》开篇这句话的影响,因此,“情可情”接下也可以是“非常情”。“情可情,非常情”可以理解为:情是可以用情来意会的,但这个情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情。“非常情”提示了《红楼梦》之“情”的整体涵义,即包含“欲”与“纯情 ”之情,“情可情”则暗示贾宝玉“意淫”的“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强调必须是有相同的情才能真正互相体会,而秦可卿就是这个契合了贾宝玉情感特征的人。
其次,《红楼梦》写花往往具有特殊含义。如宝玉旧号“绛洞花王”为“诸艳之冠”,(庚辰本回前总评,第十七回)即“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之意。又如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以各人抽到的“花名签”给在场的各位女子画像:宝钗是“艳冠群芳”颂称牡丹,黛玉是“风露清愁”清水芙蓉;探春杏花,李纨老梅等等,与各人情感气质甚相符合。因此,《红楼梦》里的花更是“情”的象征。第七回《送宫花周瑞叹英莲》,薛姨妈拿出十二支宫花送与荣府三位姑娘、黛玉和凤姐,凤姐又分出两支送给宁府的秦可卿。这一回的回前诗很有深意:“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谁是惜花人?相逢若问名何氏?家住江南本姓秦”。据作家刘心武分析,秦可卿就是惜花人,可是喜欢索隐的刘先生只盯住“宫花”不放,此回前诗也成为他证明秦可卿宫庭皇室身份的重要证据。[7]其实,“宫花”出自专门供应御前用品的薛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十二花容色最新”,作者以花寓情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如果只看诗的前两句,人们可能会觉得作者意指林黛玉,可是出乎意料地暗示这个“惜花人”竟是秦可卿。这难道不是告诉我们,只有秦可卿才是真正的知“情”之人?
第三,由于秦可卿的早逝,与她具有共生关系的香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的替身,[8]在表现香菱与宝玉的关系上明显留下秦可卿的影子,即作者通过描写香菱与宝玉的特殊关系暗示秦可卿与宝玉的关系。小说中表现香菱与宝玉的两个主要情节,分别是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和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前者写香菱与荳官等人斗草玩,相互追逐中将一条刚上身的石榴红绫裙污湿了,宝玉“正巧”拿来了一支并蒂莲,见此情形,让袭人取一条同样的新裙给她换上,解了香菱的困境,于是发生了“呆香菱情解石榴裙”的情形。事情到此本还算正常,但在袭人走开之后,香菱却看见宝玉做出了一件“使人肉麻的事”:“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的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抠了一个坑,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好,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这个情节应与“黛玉葬花”对应来看。“黛玉葬花”是预示自己的爱情与命运悲剧,而“宝玉埋草”是对自己无法成真的爱情理想的祭悼。“夫妻蕙”和“并蒂莲”所隐喻的不会是宝玉与香菱,因为作者认为,只有秦可卿才是宝玉的知“情”之人,堪与宝玉相配的只能是在太虚幻境与宝玉有过肌肤之亲的可卿。后者写众人坐位排列的隐喻 (香菱与宝玉正对)以及香菱所掣“花名签”的喻意 (画:一根并蒂花,题“联春绕瑞”;诗:连理枝头花正开),也暗示了宝玉与香菱非同寻常的关系。关于第六十三回,陈婴的《香菱与宝玉——〈石头记〉中的爱情悲剧》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9]但是该文作者仅仅着眼于挖掘作者所暗示的香菱与宝玉之间的特殊联系,而忽略了香菱与秦可卿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得出“贾宝玉和香菱之爱是全书的重要内容”的错误结论。
最后,警幻仙姑在太虚幻境警诫宝玉之时,“警幻仙子之妹,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作为秦可卿在太虚幻境中的化身,与宝玉同领警幻的“意淫”之说,她对“情”的理解不会比宝玉逊色。反观黛玉与宝钗,一个痴情寡欲 (为还泪而生),一个有欲薄情(为选妃进京),皆非完美。因此,秦可卿是作者精心设计安排下的宝玉知“情”之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精神的个体性与伦理的社会性之间始终存在冲突。”[4]曹雪芹以其深邃的人生洞察力和纤敏的人生感悟,在《红楼梦》中对“情”进行了整体诠释。如果说,作者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情感触角让我们感受了丰富多样的情感世界,那么,“美中不足”之叹又让世人认识到,所谓“钗黛合一”式的“兼美”理想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可实现。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也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1]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 [M].北京:中华书局,1964:286.
[2]俞平伯.红楼梦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1.
[3]张之.红楼梦新补 [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12.
[4]陈文新,欧阳峰.礼乐并重与钗黛合一——兼论扬黛抑钗倾向所反映的社会心理 [M]//冯天瑜.人文论丛(1998).武汉:武汉大学生出版社,1998:72-77.
[5]詹丹,林瑾.论秦可卿的存在方式及其哲学隐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5):70-76.
[6]崔莹.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 [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5(6):9-17.
[7]刘心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M].第 2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
[8]谢德俊.秦可卿是《红楼梦》的“败笔”吗[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2):76-79.
[9]陈婴.香菱与宝玉——《石头记》中的爱情悲剧 [J].红楼梦学刊,1996(2):190-204.
Em otions in“A D r eam of Red M ansions”
X IEDe-jun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 logy,Quanzhou N orm a l University,Quanzhou 362000,Ch ina)
Emotions in“A D ream of Red M ansions”can be described as far-reaching imp lication.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of Jia Baoyu is“Q ing buqing”,and it is an inc luded“Sex”and“Innocent”emotional world,sustenance of the author of the“Q ing”ideal.L in Daiyu’s“Q ing-qing”and Xue Baochai’s“Q ing-shi”on behalf of the two emotional dem andsof Jia Baoyu,but can not have both.Q in Keqing hasboth advantages Xue Baochai and L inDaiyu,as the understand ing of Jia Baoyu“Q ing”of personal,is a b lend of two kinds of emo tion w ith a try.Fu ll of the aesthetic ideal of Q in Keqing and early to exit the stage,the outcom e of the novel lay the tragedy of the tone.
“A D ream of Red M ansions”;“Q ing buqing”;unity of Xue Baochai and L in Daiyu;Q in Keqing
I207.411
A
1672-3910(2010)04-0040-04
2010-03-08
谢德俊 (1973-),男,江西婺源人,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