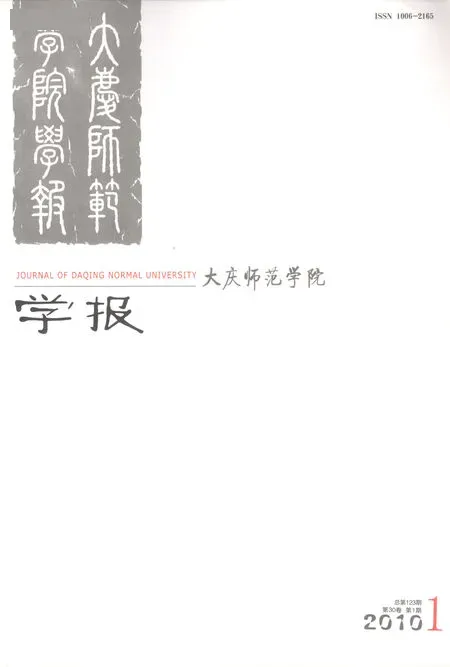西美尔论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
陈立勇,刘晓华
(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
西美尔论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
陈立勇,刘晓华
(大庆师范学院,黑龙江大庆163712)
西美尔认为现代文化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命的目的臣服于手段;二是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离异。他通过对现代社会中文化困境的社会学梳理,选择货币和以货币为基础的关系形式来理解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整个内涵,认为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本质在于人的内在生命感觉的萎缩。
西美尔;现代社会;文化危机
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是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与17世纪科学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在自然时间跨度上,它始自欧洲历史中从三十年战争结束(1648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这一段时期;而在思想领域中,它常常开始于从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1620年)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这一现代思想新纪元以来的思想发展历程。而我们所谓的“文化危机”,正发生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可以简单地把它界定为特定时代的主导型文化模式的失范,即“生活于这种文化模式之中的人们原有的文化模式正在逐渐失范和消失,而新的文化模式尚未形成。原有的理解、思维、活动和范式在应付新的问题时已经失效,而新的框架尚未造就”[1]10。德国宗教社会学家西美尔(Simmel,1858—1918)从主体精神活动的视角,通过货币和以货币为基础的关系形式来理解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内涵,认为现代文化危机的本质在于内在生命感觉的萎缩。
一、文化危机及其表现形式
西美尔把文化视为属人的形式和力量,他认为文化是生命产生出来用以表现和认识自己的某种形式,是由生命与形式构成的整体存在样式。生命是文化内蕴的精神,是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最终动力因,而形式就是用以承载生命的框架。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生命与形式的永恒冲突与对抗。西美尔说:“生命只能以特殊的形式取代自己;然而,由于它本质上是永不停歇的,所以它永远不停地同自己的产物进行斗争,这一点是不变的,不以它自己为转移。这个过程表明旧形式为新形式所取代。……生命总是持续不断地在死亡复活——复活死亡之间运动着。”[2]24从本质上而言,只有那些遵循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目的与稳定性的形式才能表现内在生命,而这些规则、目的以及稳定性是从一定的自主性中生成的,它们不依附于创造它们的精神动力而存在。西美尔认为,生命与形式之间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创造性的生命总是产生一些与生命对抗,甚至会摧毁生命的东西;另一方面,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的形式,生命将无法表达自身。“这一悖论是真正的、无所不在的文化悲剧。”[3]175形式同生命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形式,生命便不能称其自身为生命。但是,用来表达生命的形式一经出现,就会立即要求有一种超越特定历史阶段和摆脱生命律动的效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生命内在超越性和自在性之间的张力。“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在各个领域内表现出来;并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危机。”[2]25
生命与形式之间永不停歇的冲突和斗争,构成了西美尔深为忧虑的文化困境。西美尔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而且它们发展的速度已经将后者远远地甩在了后面。”[3]173大抵而言,现代社会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制度性维度,表征为“人的手段”,即强调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必然、整体、技术、秩序和利润;另一个维度是审美性维度,表征为“人的目的”,即张扬人文理性和个体精神、偶然、审美、感性和反叛。在现代社会中,制度性维度在工具理性强盛之际压迫审美性维度,导致人的目的臣服于手段,这也正如西美尔所言,目的与目标的地位正逐渐被手段与方法所篡夺。西美尔认为,文化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灵魂的改进,这种改进不能直接在灵魂内部完成,“它是间接完成的,经由物种的智力成就其历史的产物:知识、生活方式、艺术、国家、一个人的职业与生活经历──这一切构成了文化之路”[3]171。也就是说,主体精神在这条文化之路上能够使自身达到一种更高级更进步的状态。由此一来,一切能够增进文化发展、进步的行为,都会以手段和目的的形式堆积在一起。在纯粹的思想层面,我们需要在相对意义上强化目的,但如果仅仅将所谓的“终极目标”作为动力,那么主体精神将逐渐衰减。面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全面扩张,西美尔不无忧虑地说:“飞速发展并蔓延开来的技术——不单纯局限于物质领域——形成了一张手段之网,而我们深陷其中,从手段到手段,愈益增多的中介阶段蒙蔽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自己真正终极目标。”[3]172现代人仅将所谓的“终极目标”作为动力,主体精神将逐渐衰减。面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的全面扩张,西美尔认为,这是极端的内在危险:一方面,它威胁着一切文化的发展、进步和完善;另一方面,导致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
现代文化危机的第二个表现形态是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离异。具体而言,主体文化是一种个体文化、精神文化,而客体文化则是一种物质文化。西美尔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之间、新形式取代旧形式之间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和谐状态破碎了,“事态化、机构教养文化及客观思维文化正日益复杂、精细,其扩展范围无穷无尽,它们的内在统一关系都归向文化整体,而文化整体又拒绝把各种个体文化归结到自己之中。”[4]96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离异、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压制,已经阻断了主体素质向完善状态的演化之路,在一定意义上而言,这才是现代文化困境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货币是透视文化危机内涵的标的
在西美尔看来,任何社会行为或关系都可以成为理解整个社会生活世界的方式,甚至成为了解社会生活世界重要面向及意义的方式。因此,西美尔选择货币和以货币为基础的关系来窥视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整个内涵。他在以《货币哲学》及《现代文化中的金钱》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性的观点:货币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新上帝。
货币经济的出现是现代社会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它改变了交换的形式,由此转变了人们对于价值的看法。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入,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摧毁了前现代社会自然经济中物物交换的单一形式,以及物物交换经济中很典型的个性与物质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货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越来越具有纯客观性和纯技术性特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货币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符号,就其内在价值而言变得越来越中性。”[5]85与马克思关心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西美尔所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考察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和精神内在性问题。西美尔认为,货币的纯客观化和纯技术性特征在现代社会中意味着货币的非人格化,它隐去了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形态,以一种数量关系来取而代之,在原则上,人人可取而用之。货币的纯客观化和纯技术性通过交换关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个人之间原有的个性与情感因素已不复存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用以调节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被客观化为计算方法。于是,“整个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和事物的本质都成为了可计算的,而文化的客观化则是这种客观化趋势的最终结果”[6]75。
“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4]265-266西美尔观察到货币的交换功能是其本质特征,对文化领域的作用意味着货币成为价值的符号表征,货币即价值,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将所有不可计算的价值和特性化为可计算的量,在货币的度量下,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一切都被量化。
现代货币经济生活中主体生存感觉的异化以及终极价值的丧失是西美尔货币—文化论的最终落脚点。“客体的质的本性由于货币经济而失去了其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根据货币的价值客体持续地被要求进行估价,这最终使之成为唯一有效的评价方式;人们越来越频繁地在那些无法用货币方式表示出来的事物的特殊价值旁快速掠过。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从我们的手指间一次次溜走,确定无疑的满足感越来越罕见,所有的努力与活动实际上都没有价值。”[3]101社会朝向绝对理性和非个人化的方向发展,而个体的选择性却在现代社会中慢慢隐去,被逐渐忽视掉。于是,现代人不再满足于事物自身的内在魅力,反而看中自己的感官刺激;不再看重自己的生命感觉,而是看重自己和别人拥有什么东西以及所拥有东西的数量。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体化,造成的是终结追求和意义的失落;现实客观世界的发展进步,却以人的精神生活的衰退为代价。
当然,西美尔并不否认货币经济的出现对于人身解放与个性自由的贡献。但他认为由金钱所引发的人身解放与个性自由转瞬即逝,到头来剩下的只能是无聊和空虚感充斥在整个生命中。正如西美尔所言:“我们迈出第一步时是自由的,而迈出第二步时就是奴隶了。”[5]159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上,处于世纪之交的尼采(F.W.Nietzsche,1844—1900)借助疯子之口庄严宣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把上帝杀死在最后的道德避难所中,宣告了上帝所承载的传统价值的崩溃。虽然上帝已死,但它本来的位置依然保留着,尽管这已经是一个空位了。海德格尔说,这个空出的位置“要求人们重新去占有它,用别的东西去代替那个消失了的上帝”[7]。西美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日常生活层面上敏锐地观察到,货币已经占据传统上帝留下的空位,成为现代人的新上帝。
三、文化危机的主体视角:内在生命感觉的萎缩
货币古已有之,在任何时代个人对货币都是贪婪的。但在西美尔看来,最为强烈的、最为广泛的对货币的欲望却只发生在一些特别的年代里。“在当前——犹如希腊和罗马的衰落时期——以及在远离个人内心世界的地方,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客观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染上了铜臭。”[5]165-166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它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和信仰满足的需要。特别是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直接导致的就是主体内在生命感觉的萎缩。
西美尔认为,以货币为中心的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同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产生的生命感觉在形式上具有相似之处:上帝的观念超越了世间所有一切相对的事物,是终极性的抽象综合。在上帝观念中,生活的矛盾获得了协调统一,生命中所有不可调和的东西找到了和谐。同样,货币也超越了所有具体的事物,似乎可以调节一切生活矛盾。人们相信货币万能,就如同信赖上帝万能。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是人们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而在现代货币经济社会中,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却变成了对货币的渴望和永无止境的单一追求。正如西美尔所说:“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5]161西美尔认为,货币是手段变目的最为极端的例子。在现代社会里,金钱成了现代生活中唯一的和最为直接的目标,现代人的一切以货币为绝对中心旋转不停,货币成了个人此在与社会发展的“永动机”。大多数的现代人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相信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追求的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8]10。人们将情感、价值、终极追求等都寄托在金钱之上,生命感觉注定要萎缩。现代人正是在这种永无止境的此在追逐中迷失了方向而无法到达理想的彼岸,于是成了栖居在桥上的无家可归之人。
在现代社会中,手段被当成目的,目的臣服于手段,把内在与外在生活的理性秩序搅成了一团乱麻;客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发展速度之快,已经把独立赋予对象物以重要性的主体文化远远抛在了后面。作为整体的文化实际上已经难逃“巴比塔”的厄运。现代人面对着日益繁盛的以货币为代表的外在物的增长,陷入了一种近似病态的自我陶醉中。人无法永远栖居在桥上!这不仅是西美尔对于整个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很严厉的针砭,更是提醒现代人的一句警示恒言。对于现代人来说,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寻求出路。
人要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向生存目的回归,将人的存在理解为终极的、无条件的存在中心,它关乎人之生命、关乎人之命运,关乎人之生存目的。
[1]陈树林.危机与拯救——蒂利希文化神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西美尔.现代人与宗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4]西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1.
[5]西美尔.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赵卫华.消费的社会结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4(1).
[7]海德格尔.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李伟]
陈立勇(1982-),男,黑龙江大庆人,大庆师范学院科研处科员,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和文化社会学研究。
B505
:A
:1006-2165(2010)01-0013-03
:2009-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