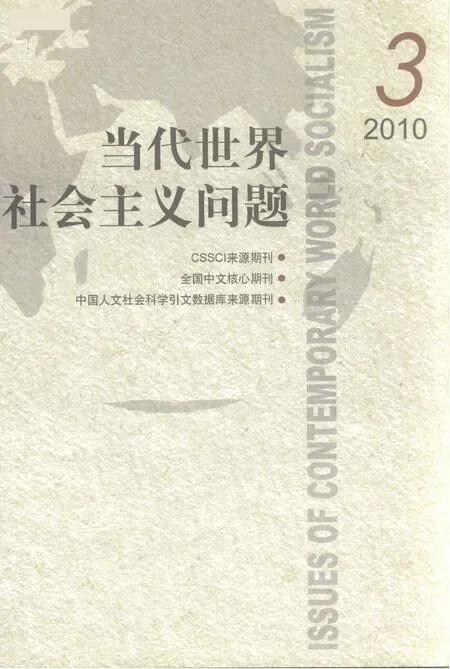威廉·弗雷、雪松谷公社与俄国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实验*
原 婧
威廉·弗雷、雪松谷公社与俄国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实验*
原 婧
活跃于1875-1877年的雪松谷公社,是美国公社浪潮时期唯一一个完全由俄国民粹派人士建立的公社,威廉·弗雷在该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雪松谷公社的实践与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理想完成了一次有机的结合。
威廉·弗雷;雪松谷公社;俄国民粹派
自19世纪中期起,在北美大陆 (主要是美国)开始了一个社会主义理想和公社的实验浪潮。到1881年,仍有67个这类公社在活动①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1965,p102.。其中,位于堪萨斯州雪松谷镇,由俄国人威廉·弗雷 (William Frey)领导的雪松谷公社 (Cedarvale Community)极为独特,其成员多为流亡美国的俄国民粹派人士,其政治理念也迥异于其他公社②据笔者检索,目前国内学界对该公社尚无系统研究。1965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俄国文学批评家Avrahm Yarmolinsky的《A Russian’s American Dream——A Memoir on William Frey》一书,其中描写了弗雷建立公社的过程;俄国侨民作家Mark Aldanov在《Russian Review》(1944年第4卷第1期)发表《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一文,对雪松谷公社建立及失败的过程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对弗雷、马林科夫、柴科夫斯基三位公社主要成员分别进行了介绍;发表于《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1946年5月第5期的David Hecht的《Lavlov,Chaikovsky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文,从柴可夫斯基的角度介绍了雪松谷公社的运行情况及他对公社的看法。国内学界目前仅见秦晖教授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提及雪松谷公社 (http://view.news.qq.com/a/20090121/000004.htm)。。
一、威廉·弗雷其人
威廉·弗雷 (1839-1888)原名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基恩斯 (Vladimir Konstantinovich Geins),俄国人,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毕业于俄国总参军事学院,25岁时成为总参谋部的上尉,同时还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他年轻时曾与俄国革命者有过交往,但在27岁时突然遭遇精神上的危机,开始对军事、战争、革命失去信心,对俄国的环境感到厌恶。起初,他打算建立一个移民公司,为俄国开拓第一个海外殖民地。1867年,他在彼得堡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了对威廉·H·迪克逊 (William H.Dixon)《新美国》的介绍,从中得知,在美国有许多公社实验,由此萌生了到美国去办公社的想法。《一个俄国人的美国梦》的作者亚莫林斯基指出,其实“这时美国公社实验的兴盛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位易受影响的俄国人没有看到这一点”①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1965,p6.。总之,基恩斯“做了一个突然的决定——长期,也许是永远地离开俄国”②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in Russian Review,Vol.4,No.1,1944.p32.。1868年2月12日 (俄历),他与新婚妻子离开俄国,于4月12日 (公历)抵美,并改名为威廉·弗雷,由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美国生活。
三个月后,弗雷见到了威廉·H·迪克逊在《新美国》中特别介绍过的“奥纳达公社”(Oneida Community)的领导人,并在次年收到加入公社的邀请。1870年,弗雷夫妇加入了“重聚公社”(Reunion Community),他后来一直主张的素食主义、精神批判等,都是从这里学来的。
1870年底“重聚公社”分裂后,弗雷决定自己建立一个公社。1871年1月,他购得位于霍华德郡雪松谷镇的一块土地,建立起了“进步公社” (Progressive Community)。1874年秋,进步公社获得堪萨斯州法律的认可,被州政府称作是“为了慈善和教育的目的”。公社由一批与弗雷几乎同时来到美国的俄国人以及一些当地人组成。报纸《进步的社会主义者》,是公社向外界宣传自己的重要工具③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49.。由于各种原因,1875年3月弗雷带领俄国人离开了进步公社,又建立了一个为期短暂的“研究公社”(Investigating Community)。
同年,弗雷被邀请参加由流亡美国的俄国民粹派人士刚刚建立起来的雪松谷公社,并成为公社无可争辩的领导者。在雪松谷公社,弗雷奉行的原则与在进步公社时基本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进步公社、研究公社、雪松谷公社都位于雪松谷镇,且相去不远,但只有后者才是以“雪松谷”命名的,它就是我们在本文中所研究的对象。
雪松谷公社仅坚持了不到两年时间,其成员的绝大部分即那些民粹派人士,都返回了俄国。弗雷一家在雪松谷一直住到1879年夏,秋天时全家搬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在这里,弗雷开始系统学习孔德的人性宗教。其实,早在初到美国时,他就曾接触过孔德的著作,并把那时说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④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3.。而此时的弗雷,则经历了思想上的一次大转变,成为一个狂热的实证主义者:他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实证主义的作品,用英语和俄语作演讲,鼓励人们改信人性宗教①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96.。即便如此,他的公社理想仍旧没有改变。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引发俄国大规模的排犹运动,大批犹太人移民美国。弗雷为他们建立起名为“新敖德萨”(New Odessa)的组织,实行公社管理模式,同时宣讲实证主义。这个公社一直存在到1887年。
1885年,弗雷来到了当时实证主义的中心——伦敦,以烤制和出售“美国手指面包卷”为生,同时积极参加实证主义者的活动。此时他已经是美国公民,因而被允许回俄国游历。亚莫林斯基说弗雷是“一个天生的劝改信仰者”②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92.。的确如此,弗雷希望俄国人意识到,实证主义、人性宗教是比暴力革命、东正教更好的解决俄国当前问题的方式,这一点在他劝说列夫·托尔斯泰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③雪松谷公社一位名叫阿列谢耶夫 (Alexeyev)的成员,在回到俄国后担任了托尔斯泰家的家庭教师,因此弗雷得以与托尔斯泰结识。托尔斯泰还与雪松谷公社的其他几个成员有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思想。。1885年,弗雷回到俄国不久,便在阅读托尔斯泰作品的过程中发觉,托尔斯泰的思想与实证主义有着诸多近似之处,于是他便试图说服托尔斯泰改变信仰,并开始与托尔斯泰通信。同年10月,弗雷被邀请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在这里受到热情款待,参观了当地的乡村学校,并向人们讲述他在美国时的故事。从此,他与托尔斯泰结下了友谊。在弗雷返回伦敦后,他们仍多次通信,托尔斯泰甚至仿效弗雷过起了素食生活。然而,弗雷劝说托尔斯泰改信实证主义的目的没能实现,阿尔达诺夫曾引用《弗雷书信集》中的一段话,来证明他“在这件事上的失败,显然使他濒临暴怒的边缘”④参见 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43.。在弗雷离开庄园不久,托尔斯泰在写给亲人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关于他,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让人联想到美国的生活,那个新鲜、有力、年青而又广阔的世界。”⑤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112.可见,比起实证主义,托尔斯泰似乎对弗雷在美国的公社生活更感兴趣。
1888年春,久病缠身的弗雷终于决定返回祖国定居,但由于美国使馆拒绝为他更新护照,这一计划没能实现。11月,年仅49岁的弗雷病逝于伦敦,当地的实证主义者纷纷以重温弗雷生前演讲的形式对其进行纪念。
弗雷在美国、英国居住近二十年,不断受到各种西方思想的影响,但纵观他的一生,我们仍会发现,在他身上无处不体现着鲜明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他早年就离开了俄国并改换姓名,誓与旧世界决裂,这其中既有反叛与极端的情绪存在,但更多是自己的抱负在国内无法施展时的一种不得已的逃避;直到晚年,他仍期望以实证主义改造俄国人的思想,改变俄国现状。可见,在他心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强烈的爱国热忱。救世主意识和过分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他的身上同样存在,这也正是他能与民粹派人士达成一致、共建公社的原因之一。不过,相对于那些参加雪松谷公社的民粹派人士而言,弗雷拥有更多、更强烈的自我约束、自我反省意识,这正是支持他数十年如一日忍受公社艰苦生活的精神动力。虽然他的行事风格略带专制,但却不曾动摇他在各个公社乃至后来实证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可以说,他正是俄国人所崇拜的那种“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尽管托尔斯泰最终都未接受弗雷的劝说,但却对其人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个人,因其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我们,而且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铭记的人之一。”①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foreword,vi.
二、村社理想与雪松谷公社
雪松谷公社作为在美国唯一一个完全由俄国民粹派人士建立和构成的公社,与俄国固有的村社理想是分不开的。
俄国村社 ( М и р或 О б щ и н а) 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渊源。这是一种相对稳定、半封闭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农民共同体,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村社成员中自然产生一些公认的“真理” (и с т и н а)。村社的自我管理和村社成员的相互监督 ,除了依靠国家法律和教会的有关规定外,主要依靠的是长期形成的、由村社成员共同创造并世代相传的村社原则和道德规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俄罗斯社会曾经摆动于东西方两条发展道路之间,在政治上经历了改革和革命的强烈震动,在经济上经历了农奴制的危机和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的异常发展,并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冲击,但村社制度却一直保存下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
亲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打击的赫尔岑,在其思想回归的过程中,开始到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中去寻找答案,发现了独具特色的俄国村社制度,并从中看到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希望。他在1849年发表的《俄罗斯》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称之为俄国社会主义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来源于土地和农民的生活,来源于每个农民实际有一份土地,来源于土地的再分配,来源于村社占有制和村社管理——并且将同劳动者的组合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所普遍追求的和科学所承认的那种经济上的正义。”②[苏联]马里宁著,丁履桂等译:《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简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5页。1851年,他在用法文撰写的《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又指出,俄国人民本身最具有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拥有村社的俄国要比西方国家更接近社会主义:“西欧曾经拥有过村社,但在朝向封建主义的发展中,以及罗马私有财产向一极集中的发展中失去了它。而俄国不同于西方,它还很年轻,因为它仍然拥有村社。……村社组织顺利地维持到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时候,这种情况对俄国是极端重要的。……村社没有消灭,个人所有制没有粉碎村社所有制,这对俄国该是多么幸运的事。俄国人民置身于一切政治运动之外,置身于欧洲文明之外,这对他们该是多么幸运的事,因为这种文明本身已通过社会主义而达到了自我否定。”③ГерценА.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енений.М.,1986.в ы п.2.Т.2, С.179.他认为,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用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因为他们就生活方式来说天生就是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共同掌握土地本能上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①Володин А. И. Утоп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М.,1985.С.38.
赫尔岑对俄国村社、农民和村社社会主义的认识,直接推动了19世纪70-80年代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潮。民粹派不再停留于理论层面,从1873年开始,他们发起“到民间去”的运动,深入农村,考察农民生活,了解农民要求,发动农民起来反对专制制度。可是,民粹派运动并没有把农民发动起来,反而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1875-1876年间,民粹派开始从“游击式的”鼓动过渡到在农村建立长期巩固的基地。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 60 年代建立的 “土地与自由社” (З е м л яив о л я) 传统而新建的同名团体,是这种基地的代表,从此“民粹主义运动由自由分散的活动进入了统一集中领导的新阶段”②徐觉哉:《社会主义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由于雪松谷公社的最初建立者与主要成员都是在这一时期流亡美国的民粹派人士,就使这个存在于美国土地上的公社带有了鲜明的俄国色彩,体现了这一时期民粹派运动的主要特征。公社的两个主要建立者是亚历山大·卡皮托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科夫斯基。马林科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上过大学,早年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他创立了一个既非宗教也非教派的名为“神人”(Godman)的组织,宣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神性,……必须唤醒它,找到人们身上的上帝。为了让压迫不复存在,上帝将会在人们的灵魂中解决一切,每个人都会变得正直而友善”③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4.。他的信徒,也就是后来追随他到雪松谷的那群人,多为民粹派分子,他们都自称“神人”。据阿尔达诺夫介绍,“神人”们总共也就大约十五个人,其中包括早在青年时代就与革命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柴科夫斯基④柴科夫斯基曾是“彼得堡青年革命者协会”(St.Petersburg circle of you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成员,但他在25岁之前就已脱离了革命运动。。
1874年,“到民间去”运动遭到沙皇政府镇压,“神人”们被捕入狱。然而有趣的是,当马林科夫向审问他们的法官宣讲上帝与爱之后,他们都被释放了⑤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72.。马林科夫看到自己的理论在俄国无法实现,便于1875年夏天率领信徒来到美国,并找到了居住在雪松谷的弗雷——弗雷当时已经因为建立公社而在美国很有名气了。不过,雪松谷贫穷、饥饿的环境与他们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弗雷夫妇甚至还穿着美国内战时期的蓝军装⑥David Hecht,“Lavrov,Chaikovski,and the United States”,inA 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Vol.5,No.1/2,1946,p152.。此外,弗雷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任何欢迎,也不鼓励他们加入“研究公社”。于是,“神人”们便自己在距“研究公社”四英里的迦南河畔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雪松谷公社。
但这个公社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神人”们虽然对土地充满热爱,但却根本无法胜任耕种、做饭、洗衣、挤牛奶这些日常劳动,因而陷入了完全无原则、无秩序的状态,遭到堪萨斯州政府的警告。于是他们决定邀请“研究公社”加入,希望弗雷的经验能够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弗雷来到雪松谷公社后,立即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将公社中原来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到更加极致的程度:公社就像一个家庭,财产公有,成员工作各有分工,种植玉米和小麦,并拿到公社外去卖;成员间的冲突不付诸法庭解决,任何决定都通过投票方式作出;起床、吃饭、睡觉、工作都被规定以严格的时间。美国当局曾一度对雪松谷公社很感兴趣,并派了一些人来调查,调查结果“令堪萨斯的公众舆论满意,‘神人们’和他们各自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在雪松谷一定不存在‘共妻’的现象”①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8.在原文中,阿尔达诺夫用的是“妇女的社会化”一词。美国当局存在这样的担心是有原因的,因为当年著名的“奥纳达公社”就是由于实行“性自由”制度而遭解散的。。不过,比起这些,弗雷似乎更强调社会主义原则在生活细节方面的体现,而这也成为促使公社迅速解体的最直接因素之一。
然而,弗雷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善公社的状况,似乎反而加重了“神人”们的痛苦:人们被要求过一种近乎禁欲主义的物质生活。弗雷从“重聚公社”学来的并一直被他严格奉行的素食主义,被引入到公社中:“弗雷的基本理论是,人们应该只吃那些以其自然形态存在的食物。”②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8.发酵的面包是不可以吃的,酒肉当然更是被禁止的,咖啡、茶、糖甚至盐也不允许。后来,吸烟者也被禁止进入公社。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还是对药品的禁用,弗雷建议人们用在大木桶中蒸浴的方式来代替奎宁。此外,他们唯一的一座房子也破烂不堪③参见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merican Dream,p76.。
更糟糕的还是精神生活层面:“大家规定,公社成员彼此之间不可以有秘密。即使是丈夫与妻子间的耳语,也会引起反对。”④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8.在每周例行的精神批判大会上,每个人都要分别说出其他成员一周以来所犯的过失,哪怕是像谁没有洗干净盘子或是谁多吃了一口饭这样的小事。后来,自我悔过制度也被引入,无论是付诸实行的还是仅停留在精神层面的“罪过”,都要一一通报。同时,弗雷性格中古怪的一面也与日俱增,他在公社中专制的行事方式引起成员们的失望。马林科夫因不能忍受公社压抑的气氛而搬到河对岸的小木屋居住,柴科夫斯基则把那里的生活叫作“精神阉割”。思乡的苦楚同样纠缠着公社成员们。当他们离开俄国时,觉得国内的气氛要让他们窒息了,因而急于到美国开拓一片自由的新天地,可是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可能永远都无法适应美国。
弗雷对人们的抱怨统统报以蔑视,他要求每个成员都必须摧毁自己身上的分离倾向,变为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一场以“奎宁”为口号的暴乱发生了:人们趁弗雷外出的时候,宰杀动物,大吃大喝①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39.。在弗雷的一再坚持下,雪松谷公社坚持到1877年夏天。此后,农场被变卖,财产被分发,大部分公社成员追随马林科夫返回了俄国。在堪萨斯州1877年7月9日的一份特许状里这样写道:“这个被称作‘雪松谷公社’或是‘雪松谷慈善与教育社’的社团,是为了互相帮助和不可或缺的教育之目的而建的,它的名字将永远存在。”②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79.
三、威廉·弗雷、雪松谷公社及其历史回声
在返回俄国游历期间,弗雷曾这样回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在美国,我做过各种无需专门技能的工作,同时也参加了许多旨在不通过暴力和革命,而是以对正当生活以身作则的方式来改善生活的社会主义事业。在美国的全部时间里,我都在忍受着最悲惨的物质贫困,社会活动带给我的是最残酷的失望。但是,在那里我却经历了人所能达到的极乐。而且,在美国的十八年间里,我学到了许多好的东西,当我由于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而不得不返回欧洲时,我对这个已经接受我的国家深怀感激,对它的政治制度、正直的公职人员、众多的人民……怀着深刻而真诚的敬意。”③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foreword,vi.可见,虽然公社实验一波三折,最终也没能成功,但弗雷仍未对美国失望,而是对美国的一切都充满赞赏与感激,在他心目中,美国依然是其实现人生理想的乐土。
作为一个新大陆和新国家,美国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对自由的人文环境以及对各种社会力量较强的包容性,而有别于欧洲大陆,长期吸引着心怀宏志的社会主义者的目光,成为他们建立公社的试验场。英国人欧文1824年在此创建了“新和谐”公社,法国人卡贝创建了“伊加利亚之旅”,这都是社会主义者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实践其社会理想的著名范例。然而,这些公社实验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关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屡屡碰壁的原因,讨论由来已久,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桑巴特的“物质替代”理论。秦晖教授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文中,也对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解释进行了详细评述。
就雪松谷公社的实践来看,来自俄国的民粹派对土地和农民深怀热爱,而堪萨斯州则有着适宜农业发展的优越条件;虽然弗雷的专制作风令人难以忍受,但公社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全面控制,与俄国村社中靠世代相传的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行自我管理和相互监督的生活方式不无相似之处。这也正是民粹派人士能够与弗雷合作的原因。雪松谷公社的主要成员是民粹派人士,但却接受了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弗雷的领导,因此它并不是民粹派运动在美国的简单翻版,而是俄国式“农民社会主义”与这一时期美国公社实验相结合的一次特殊尝试。从历史上看,这些“乌托邦式”的公社无一能够逃脱失败的命运,但与“奥纳达”等维持多年的公社相比,存在时间不足两年且充满矛盾与斗争的雪松谷公社,其失败应该有更多的自身原因。弗雷就曾感慨:“神人”们的失败正在于他们对规矩的厌恶①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 merican Dream,p80.。无论是在俄国还是美国,民粹派都并非是为建立公社而建立公社,他们更希望通过建立公社来实现个人生活乃至整个俄国社会的改变。俄国人极端主义的性格,无论在弗雷还是在民粹派人士身上,都体现得十分明显,这可以说是雪松谷公社较其他美国公社存在时间更短的原因之一。
雪松谷公社解体后,其主要成员的去向似乎也代表了俄国后来发展的两种趋向。回到俄国的马林科夫平静地在家乡生活到1904年,并继续受到追随者的爱戴;他与东正教和解,成了虔诚的东正教徒;还在铁道上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养活一大家子人。柴科夫斯基先是流浪到费城寻找工作,后辗转移居伦敦。许多年后,他在写给弗雷的信中说:“再血腥的革命也要好过这种缓慢的、持续的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嘲弄。”②Avrahm Yarmolinsky,A Russian’s American Dream,p77.他加入了俄国社会革命党,并于1905年返回祖国。1917年,他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之一,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18年,他则成为俄国北部省份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首脑,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与弗雷不同,雪松谷公社并没有成为这些民粹派人士生活与理想的全部,也并没有“在他们周围的人中,更不用说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甚至是最轻微的一点影响”③Mark Aldanov,“A Russian Commune in Kansas”,p41.。
A81;D0
A
1001-5574(2010)03-0044-08
原婧,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蒋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