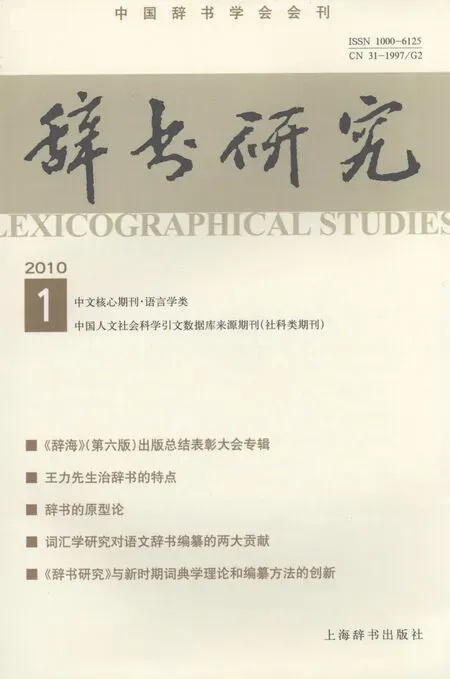王力先生治辞书的特点
曹先擢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北京 200010)
我国现代辞书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于中叶,到70年代日臻成熟。在这个过程中,王力先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先生治辞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945年王先生写了《理想的字典》一文,1946年编写了《了一小字典初稿》,前者谈理论,后者是注释样稿,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1974年至1978年编纂了《同源字典》,前面有一篇“同源字论”。1984年编写《古汉语字典》,该字典的长序不是写在全书完成之后,而是与撰写同步进行的,该序概括了字典的八个特点。1985年秋全书近三分之一写就后,先生的健康情况急转直下,便将余下的工作交给了唐作藩等六人。1986年先生仙逝。此书后改名《王力古汉语字典》,由中华书局出版。王先生对辞书理论的探索和编纂实践,主要表现在上述作品中,时间延续40年,充分反映了他对发展我国辞书事业的执着追求。吕叔湘先生在《悼念王力教授》中说:“王先生对于分析字义,特别是古今字义变迁,一直很留心,前后写过《理想的字典》(1945)、《了一小字典初稿》(1946)、《新训诂学》(1947)等文章,后来主编高校教材《古代汉语》的时候又特地辟《常用词》一栏。然而这些都还是小试其锋,非常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机会让王先生主持一部大型词典的编纂工作。”(1986年 5月16日《人民日报》)的确,这是我们时代的损失。
对王先生的辞书理论和编纂实践,下面作简要的介绍。
一、《理想的字典》
这是一篇具有经典意义的辞书学理论文献,发表在1945年3月的《国文月刊》第33期上。我认为应当联系辞书编纂的历史背景,这样才能领会得深一些。
文章开始为“小引”,讲“小学”与字典(dictionary)的关系,使我们了解“小学”的训诂、字书、韵书与字典的异同之处。我们谈字典离不开传统,有一个今古对接问题。对接的目的是接受传统小学的优良的东西,扬弃不符合科学的东西。对此,王先生分五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中国字典的良好基础。古代释义有五点值得肯定:1.天然定义。如百,十十也;千,十百也。2.属中求别。如《说文》:“粳,稻属。”有时在一个大类名之外再加一个修饰成分。如:羝,牡羊也;缨,冠系也。3.由反知正。如:旱,不雨也;拙,不巧也。4.描写。如:馆,客舍也,周礼以五十里有市,市有馆,馆有积,以待朝聘之宾客。5.譬况。如:黄,地之色也;黑,火所熏之色也。现代世界最好的字典,也离不了这五种方法。
第二,古代字书的缺点和《说文》的流弊。大致说起来,《说文》共有四个缺点:1.文以载道。2.声训。3.注解中有被注解的字。4.望文生义。
第三,近代字书的进步。第一步是知举例;第二步是知举篇名。这两个方面王先生的举证有200年前的《康熙字典》和1936年出版的《辞海》。王先生所说的“近代”“其时段比较长”,这是因为我国辞书的历史长。刘复说:字书之学,吾华发达最早。远如《说文》《玉篇》之属,姑置勿言,即如人人习知之《康熙字典》,在吾人犹以为一种近代的著作,而其纂成之年,实为公立1716年。其时英国第一词典大家Samuel Johnson尚只7岁,而《法国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Académie Franaise)之第一版(1694),在法人今日已视为一种古远之书,实亦不过早出22年也。王先生说的近代与刘半农讲的是一致的。在与西方辞书历史作比较时,我们当注意我国辞书史的特点。至于举例问题,因为古代辞书历史长,不要一概而论,而要作具体分析,例如宋本《玉篇》例子较少,而从日本传回的唐代的写本《玉篇》零卷,其中举例却很多。
第四,当时辞书的缺点。这个问题很重要,王先生是怎么看的呢?他说了两点:1.古今字义杂糅。文章以《辞源》的“管”为例进行分析。王先生抓住了当时辞书释义中存在的这种通病,使我们进一步领会到吕叔湘先生“王先生对于分析字义,特别是古今字义变迁,一直很留心”这句话中的深意。这是一个语言分析中的历史主义观点问题,是辞书编纂时必须坚持的一个大原则。但是许多辞书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疵瑕,著名的《国音字典》(1949)也未能例外,只举其“刀”的注释:“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小船,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见《诗经》。”第一义是古今兼通的,第二、三义则是古代的了。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就只注释现代意义了:1.(刀子、刀儿)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一把菜刀,单刀,镟刀。2.纸张单位(数目不定)。为什么当时的辞书会存在古今字义不分的问题?为什么《新华字典》将古义与今义区分开了呢?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是编纂者理念不同,当然客观上与白话文尚未普及有关。2.以一字释一字 。以一字释一字,是当时辞书中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牵涉面广,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以一字释一字如何避免?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中有分析,可参考《吕叔湘全集》12卷。
第五,理想的字典。前面是从字典好的方面与不足的方面谈的,下面就转而谈应该怎么做,也就是理想的字典了。
理想的字典有三个要求:
1.明字义孳乳。字义孳乳的考察不限于上古,包括秦汉以后。王先生指出普通字典如果提及某义为某义的引申,也是有好处的。如《辞海》“信”下云:“信,诚也。按诚信有不差爽之义,引申之,凡事之以期而至无差忒者,皆谓之信,如风信、潮信(按:还有信炮、信风)。”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指出引申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字的意义,特别是深层的隐性的意义,如风信的“信”字之义。字义的孳乳,常常与语音的变化相结合。补充我学习中的例子。《王力古汉语字典》:“宿”,古入声字,息逐切,有住宿等义,中古分化出去声,息救切,读 xiù,指星座。到北京话里,入声消失,息逐切在北京话里有文白两读,也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读sù,文读,指住宿 ;读xiǔ,白读,指晚上。北京话里“宿”有 3个读音,其中xiù/xiǔ,只是声调不同,好像很近,其实相当远,处在不同的历史层面。
2.分时代先后。能否判别词义的产生和使用的时代,与我们的语文水平相关。王先生所举的例子都很有意义。这里我再补充几个例子:友直友谅友多闻,谅是什么意思?指诚实,而不是今日所指“原谅”。同一个字代表不同的词,叫“同形字”,如“菌”读阴平,指细菌,这个字义(概念)产生于近代,而读去声的,古已有之,如“朝菌不知晦朔”(庄子),二者不得相混。“女性”、“特性”,分别有两个“性”字,但是意义不同、来源不同,时代差得很远。特性的性,指事物的本质,《论衡·本性》:“性,生而然者也。”又如人性、天性、水性、药性等。女性的性指sex,是近代由日本传来的西方的概念词,上世纪30年代,北京有位教授说“人之初,性本善”的性指sex,闹了笑话,遭到周作人的批评(见《知堂书话》)。“胡”本指兽类颔下垂下的肉,后来指称胡人,对此,历史上三位大师都曾研究。顾炎武是从本土文化出发来研究的,认为战国时将戎称作胡,“是以二国(赵国和燕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种族),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又说《考工记》“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以此考知“《考工记》之篇亦必七国以后之人所增益矣”。(《日知录》卷三十二)王国维与陈寅恪则是从中西交通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王国维有《西胡考》。陈寅恪先生在《五胡问题及其他》中说:“五胡谓五外族。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著Hu,故音译曰胡。后世以统称外族。”在《史记·孝武本纪》中“有龙垂胡须”指龙颔下垂下的须。王力先生说“胡须”连用,最初表示“像胡人一样的须”,是定中结构,至确;后来胡有了胡须(并列结构)、胡子的意思。
3.尽量以多字释一字。王先生举了《辞海》的来、去、往、适四字说明:
《辞海》 《广韵》 王先生评论
来 至也 至也 从他处到此处曰来
去 往也,行也 离也 舍弃原所在地而他徙曰去
往 去也 之也,去也,行也,之也 从此处到彼处,不带宾语
适 往也 往也 从此处到彼处,必须有宾语
这些都是行为动词,还可以从行至、行自两个方面考察 。来,讲行至;去,讲行自(孔子去鲁,指离开鲁国,鲁是行为的出发点;现代“去”指行至,古今不同了,“我去上海”,行为终点是上海)。往,讲行自;适,讲行至。王先生说其不同,是不带宾语与带宾语的不同,这是考虑语用的问题,语法的问题。讲字义,要考虑词汇、语法、语用三个平面,这是近一二十年大家注意到的事,王先生早就考虑到了。
二、《了一小字典初稿》
《了一小字典初稿》开篇有一个说明,讲初稿编写的考虑:“理想的字典,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得一班人合作不可。在理想未实现以前,我想独立写一部小字典。几经易稿,非但在考证上未能满意,连体例也觉得未妥。现在先发表一些`样子',希望读者指教。”王先生对编字典事,非常认真,将其看作自己要实现的一个目标,直到晚年仍为此而奋斗。《了一小字典初稿》分析了45个字:人、仁 、仇 、仍 、化 、介 、什 、仆 、仉 、从 、他 、仙 、付 、仕 、仗 、仔 、仞 、仡 、仟 、仝 、仨 、件 、任 、休 、仰 、伕 、伐 、仲 、伊 、份 、伙 、伉 、仿 、企 、价 、伍 、伎 、仳、伈 、伋 、伃、伕 、仵 、你、伯。下面我们以“仍”字为例,来追寻王先生的思路。
仍 ①动词。以以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如“明时宰相称大学士,清仍之”。此义今罕用。②形容词。表示连续不绝之状态。如“灾祸频仍”。此义今白话罕用。③副词。今白话往往作“仍旧”或“仍然”,表示行为之连续。如“仍旧不动”。又表示行为之重复。《红楼梦》五十一回:“你们仍旧坐下说笑。”又四十四回:“便仍然奉承贾琏。”又表示行为之目的在于恢复原状。《红楼梦》五十一回:“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拈了两块速香放上,仍旧罩了。”【语源学】“仍”字古音在蒸部。《广韵》如乘切,蒸韵。等韵曾摄,日母,开三。《说文》:“仍,因也,从人,乃声。”按,“乃”古音在之部,之蒸对转。“因”者,“因袭”也。第一第二两义上古已有之:《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汉书·王莽传》:“吉瑞累仍。”第三义起于近代。古文于此义用“犹”、“复”之类,不用“仍”。“因袭”为本义。物之因袭者必相重,故又有“重”义、“屡”义。《国语·周语》“晋仍无道”,《汉书·武帝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皆“屡”义也(屡义用作状语,今成死义)。《尔雅·释亲》:“晜孙之子曰仍孙。”则“重”义也。由“重”之义用为副词,渐变为现代“连续”、“重复”之义,更由此义引申而表示行为之目的在于恢复原状。
从以上分析可见其主要有四个特点:明字义之孳乳;明时代之先后;充分而典型的例证;透彻而简要的分析。先生几经易稿,非但“在考证上未能满意,连体例也觉得未妥”,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学界常常有一个认识误区:编字典没有什么学问。有的词典谈不上学术水平问题,但是有的可以说学术含量极高,王先生的《了一小字典初稿》便是这样。
三、《同源字典》
《同源字典》是王先生在1974年至1978年,用四年时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重要著作。王先生以大智大勇,去完成这件文化工程(1974、1975年仍处在“文革”时期)。1975年在广州召开全国辞书规划会议,王先生无缘参加,我因为右倾(不同意在辞书里搞无产阶级专政)被剥夺参加会议的资格。后来朱德熙先生说,编大词典、大字典,主编人选不易找到,他说只有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这样的“大儒”才能担任,说自己也不够格。现在我读吕先生悼念王先生的文章,说“非常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机会让王先生主持一部大型词典的编纂工作”,更感到其中的深意,感到吕先生、王先生之间深厚的学术情谊。王先生自己来追求他编辞书的梦想,这就是《同源字典》,在学术史上应该大书一笔的。
该字典序的题目是“同源字论”。分四个小节:1.什么是同源字;2.从语音方面分析同源字;3.从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4.同源字的研究及其作用。我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工作,我觉得,辞书编纂者都应读读这部学术著作,视所编辞书的需要,将自己学习、研究的体会,充实到辞书相关的释义、辨析等里面去。例如书中说“合”、“盒”同源,盒的特点是盒盖和盒底合起来,用时打开。像饭盒儿、墨盒儿等。《新华字典》“盒”释义为“底盖相合的盛(chéng)东西的器物”,从形状、功能简要解释了“盒”字的意义。《新华字典》的注释讲“知其然”,而同源字的分析解决“所以然”的问题。在《同源字论》中专门用一节讲“数目”,说:一,数目;壹,专一。二,数目;贰,二心,副职。三,数目;参,成三的集体,三分;骖,驾三马。四,数目;驷,一乘为驷,四马的集体。五,数目;伍,户口五家为伍,军队五人为伍。《王力古汉语字典》有一、壹的辨析:“一是数词,壹是形容词,意思不同。《荀子·解蔽》:`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一句之中`一、壹'并用,可见`一'与`壹'是有分别的。`壹'的意义是专一。专一的意义可以写作`一',但数目不能写作`壹'。后人在单据上为了防人涂改,才用`壹'代`一'。《诗·召南·驺虞》:`壹发五豝。'本是`一发'。数目壹贰叁肆等字,皆唐武后时所改。”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版”说“明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王先生分析可与诏版用字相印证。骖,指驾三马。曾参,字子舆,此处的“参”就是“骖”字,骖由“驾三马”转指三马驾的车,这样曾参的名与字就相配了。(《古今人名解诂》,吉常宏、吉发涵)参商的参,指参星,为什么称“参”?因为“是根据中央三颗亮星而命名”(《天文名词解释》,北京天文馆)。
分析同源字,主要从语音和词义两个方面入手。词义方面,王先生说大概有三种情况:1.实同一词;2.同义词,包括完全同义和微别;3.各种关系,列了15种。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的。我曾很不深入地研究了其中的第15项“使动”,写了一篇文章《汉字的自动义和使动义》。有的一些训诂上难解的意义,实际是自动义与被动义的不同。例如“闻”,自动义指听到,使动义指使听到,即告诉、报告。《尚书·酒诰》:“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1962年,张永言先生认为这是“闻”指嗅觉的最早例子。(《中国语文》)殷孟伦先生认为是指“让上帝知道的意思”。(见《子云乡人类稿》)我认为殷的意见是正确的。
四、《王力古汉语字典》
王先生在《序》里讲了这部字典的八个特点:1.扩大词义的概括性;2.僻义归入备考栏;3.注意词义的时代性;4.标明古韵部;5.注明联绵字;6.每部之前先写一篇部首总论;7.辨析同义词;8.列举一些同源字。要注意前四卷是王先生写的,是这部书的大亮点。上面讲到“一、壹”字义的辨析,便是王先生写的,又如“不”字的注音:“bù 分物切 ,入 ,物部 ,非 。今读逋骨切,没韵,帮。职部。”请注意后面的补充“今读”云云,涉及字音的古今变化,很重要。“不”字《广韵》反切为“分勿切”当读fú。“分勿切”小韵有20个字,如弗、绂 、绋 、黻 、綍 、芾 、帗 、冹、髴、柫等,皆读 fú ,而“不”却读 bù ,属特殊的变异。这种变异发生在宋代的口语中,“不”的读音已经脱离“分勿切”而跑到“逋骨切”里了。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谈到“不”有补没切、甫勿切、甫九切、甫鸠切。“补没切”(同逋骨切)是新起的口语音。宋代孙奕的《示儿篇》说:“世俗语言及文字所急,惟`不'字极关利害。韵书中如府鸠、方久二切,施之于诗赋押韵无不可者。至于市井相与言,道途相与语,官吏之指挥民庶,将帅之号令士卒,主人之役使仆妾,乡校之教训儿童,凡一话一言出诸口而有该此言者,非以逋骨切呼之,断莫能喻”。由“分勿切”到“逋骨切”这是一变。“分勿切”与芳无切、防无切、方六切、房六切都读fú,都是合口三等。“分勿切”与博故切、普故切、裴古切、薄故切都读bù,“分勿切”是合口三等,而其他博故切等四个反切都是合口一等。按规律合口一等读[b],合口三等读[f]。“不”是“分勿切”读[b],不合一般的演变规律。王力先生说:“常用字往往在音变上是一种`强式',不随着一般的变化。`不'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语史稿》上册)古无轻唇音,“不”的声母在宋代维持了上古重唇音的读法。宋代的“逋骨切”,到北京话的读音,是第二次变化了。“逋骨切”与“补没切”相同,为帮母没韵。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的“没”韵所列的字:
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帮滂並明精清从心斜影晓匣喻来日
骨 兀咄 突 不 勃没卒猝 忽
“没”韵在北京话里韵母有两个:[u]、[o]。凡是声母属舌音、齿音 、喉牙音的,读[u],如突、卒 、猝 、骨、忽等 ;声母属唇音的读[o],如没、勃。“不”属唇音字,循例当读[o],但是它却跑到读[u]的队伍里了,读bù。我们要注意字音的时代性,有时遇到的问题比较复杂 ,如“不”。又如“具”、“俱”的辨析,是王先生写的 :“俱,举朱切,平声;具,其遇切,去声,二字不同音,亦不同义。`俱'字用作动词时,不能说成`具'。`与之俱'不能说成`与之具'。用作副词时,古多说成`具'。如《诗·小雅·节南山》:`民具尔瞻。'《弁》:`兄弟具来。'后来`俱'、`具'有了分工:二人以上同做一事叫`俱',一人把一切事务都处理了叫`具'。`俱'指主语的范围,`具'指宾语的范围。《史记·项羽本纪》:`项伯乃夜驰之沛公,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俱去,曰:`毋从俱死也。'”这里“具告以事”不能说成“俱告以事”,“俱去、俱死”不能说成“具去、具死”。故“俱”、“具”不是同义词。《说文解字》有“阅具数于门中”,中古时代“具数”何指,已经不太好懂,徐锴注释“一一数之也”,王先生说“用作副词时,多说成具”,“指宾语的范围”,准此,对“具数”我们就不难理解了。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故有成就的作者大多有一篇序,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所编撰的著作的内容,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叙》、陆法言《切韵·序》、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等。近代这个传统逐渐淡出,王力先生继承了这个传统。
今年是《辞书研究》创刊三十周年,这是很值得纪念和庆祝的,谨以这篇文章表示我的祝贺。辞书事业的发展,必须把辞书理论的建设和辞书编纂结合起来。1979年以来,我国的辞书理论建设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辞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辞书研究》的意义是不同凡响的,应该特别提出的有两点:第一,现实意义。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辞书学论文,既有丰富的实际内容,又有不同程度的理论深度,配合了我们蓬蓬勃勃的辞书编纂工作。有些论文是编纂工作理论总结,反过来又指导编纂实践,形成了良性互动。再好的理论如果读者看不懂,用不上,它的效用会大打折扣。《辞书研究》有很好的口碑,真正成了我们深感亲切的良师益友,在推动我们辞书事业的发展中起了好作用。《辞书研究》成了大家的学术家园,由此培养了一支辞书学的理论队伍,提高了辞书编纂者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我想对此大家都有深切的体会,并非我一私之见也。第二,历史意义。我们在上面提到,我国有重视辞书理论的传统,一本辞书编成了,作者就有相应的理论说明。《辞书研究》则以一种新的做法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辞书研究》组织了有针对性的理论讨论,如辞书编写的阶级性、辞书与规范化、辞书编纂的中国化、辞书学的学科地位等。对具有原创性、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辞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新版《辞海》、新版《辞源》等,刊登有一些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帮助人们认识这些辞书。经常介绍国外辞书学理论的新发展。《辞书研究》是中国辞书学会会刊,在配合学会开展学术活动方面起了大作用。辞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辞书研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