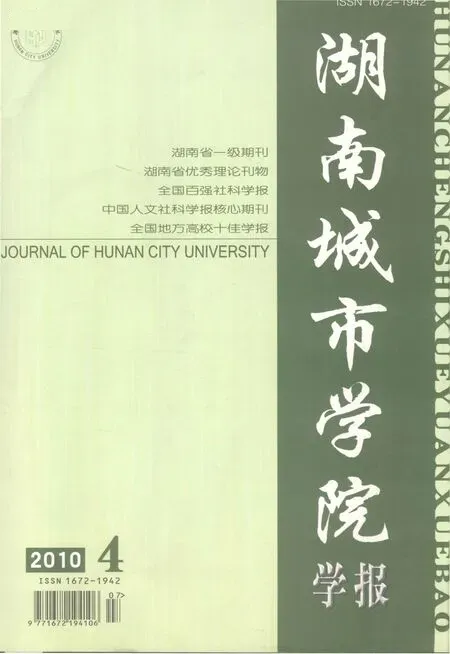庄子“心斋”“坐忘”的美学价值
秦忠翼,秦 科
一、追求逍遥游的人生自由境界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受现实的各种束缚,理想愿望常常不能自由随意地获得,从而生发出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忧愁。更何况庄子生活在无道的社会,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草菅人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时连性命都难以保住,更何能侈谈什么自由呢?这是客观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体的人的自由的限制;从主体方面来说,人常常陷入自设的藩篱之中也无法获得自由。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现实的人,“他们睡眠时精魂交构,醒来后身形开朗;跟外界交接相应,整日里勾心斗角。有的疏怠迟缓,有的高深莫测。小的惧怕惴惴不安,大的惊恐失魂落魄。他们说话就好像利箭发自弩机快疾而又尖刻,是与非由此产生;他们将心思存留心底就好像盟约誓言坚守不渝,那就是说持守胸臆坐待胜机。他们衰败犹如秋冬草木,这说明他们日益消毁;他们沉湎于所从事的各种事情,致使他们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有的情状;他们心灵闭塞,好像被绳索缚住,这就说明他们衰老颓败,没法使他们恢复生气。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1]29-30这就是庄子描绘的现世人生受缚于各种名利勾斗之中而困顿疲惫、执迷不悟的情景,也就是人间世的悲剧。但是,庄子却试图超越现实的种种羁绊,作精神上的逍遥游。游,本义指水中行;游与逰自古相通,逰为后起字,专指陆地的行走活动。游的引申义有闲放、游乐、浮动的意态。《集注》云:“游者玩物适情之谓。”逍遥游,庄子也叫优游,是一种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绝对而惬意地闲逛。这是一种“无所待”之游,不像大鹏展翅而飞九万里,凭借的是“海运”,“海运者,六月之龙卷风也。”列子的御风而行,更有所待,蝉与斑鸠们的一窜之游,更是渺小可笑之极。庄子所追求的逍遥游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3意思是说,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他还仰赖什么呢!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神人”,心目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从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庄子所追求的就是那种“至人”、“神人”“圣人”的境界。庄子在《逍遥游》中借肩吾向连叔求教的故事说,在遥远的姑射山上住着一位神人,那神人皮肤润白像冰雪,体态柔美如处女,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神情那么专注,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年年五谷丰登。肩吾认为这是虚妄之言,一点也不可信。连叔听后说,不仅形骸上有聋与瞎,思想上也有聋和瞎,他认为肩吾就是思想上聋和瞎的人。连叔赞美那位神人说:“那位神人,他的德行,与万事万物混同一起,借以得到整个天下的治理,谁还会忙忙碌碌把管理天下当成回事!那样的人呀,外物没有什么能伤害他,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天下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焦裂,他也不感到灼热。他所留下的尘埃以及瘪谷糠麸之类的废物,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人君来,他怎么会把忙着管理万物当作己任呢?[1]10在《大宗师》中,庄子称赞真人是真正通达大道境界的人。什么是“真人”呢?庄子说:“古时候的真人,不懂得喜悦生存,也不懂得厌恶死亡;出生不欣喜,入死不推辞;无拘无束地就走了,自由自在地又来了罢了。会忘记自己从哪儿来,也不寻求自己往哪儿去,承受什么际遇都欢欢喜喜,忘掉生死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本然。这就叫做不用心智去损害大道,也不用人为的因素去帮助自然。这就叫做“真人”。像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他的容颜淡漠安闲,他的面额质朴端严;冷肃得像秋天,温暖得像春天,高兴或愤怒跟四时更替一样自然无饰,和外界事物合宜相称而没有谁能探测到他的精神世界的真谛。”[1]137庄子在文中所描述称赞的姑射山神人和古代的“真人”就是真正通达大道境界的人,就是能够顺应万物发展规律,忘其生死,无己无功无名而能遨游于无穷的人。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自然无为的自由人生境界。
二、“心斋”和“坐忘”是通往大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真人、神人所享有的大道境界,一般人如何才能达到呢?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心斋”和“坐忘”,才是通往其境界的唯一途径。
何谓“心斋”?庄子在《人间世》中说,孔子的学生颜回听说卫国的国君,他还年轻,但办事专断,轻率处理政事,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轻率用兵不顾人民的死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走投无路了。他想到平时老师的教导:治理得好的国家就要离开,治理得不好的国家就要到那里去,就好像医生门前病人多一样。因此,他想去卫国思考治理卫国,帮助恢复元气,他便去请教老师孔子。孔子告诉他,恐怕去卫国就会遭到杀害,自身难保,更何况拯救国家。颜回向老师求教方法,孔子告诉他斋戒清心,如果怀着积极用世之心去做,难道是容易的吗?如果这样做也很容易的话,苍天也会认为是不适宜的。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之斋。”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42
孔子认为,使你的心志专一,不要用耳朵去听,而是要去用心体会;不仅要用心去体会,还要用气息去感受。耳朵的作用只是听,心的作用只是去体会而与外物符合。气息就是空虚而能容纳事物。大道都是集于虚明的。虚明就是指心斋。心斋,就是指心的虚静状态。这是庄子借孔子之名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是庄子为文的特殊方式,常常借名人或神人或虚构的人物之口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样使抽象的哲理表现得生动活泼。
何谓“坐忘?”,庄子在“大宗师”中,借孔子与颜回的一段对话,阐明了“坐忘”的涵义。
颜回曰:“回益矣。”
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
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
曰:“何谓也?”
曰:“回坐忘矣。”
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
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矣也。”[2]80
“忘”要有一个过程。要达到“坐忘”的境界,首先就要摒弃功名利禄等各种杂念;其次要“离形去知”。所谓“离形”、堕肢体“,就是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所谓“去知”、“黜聪明”,就是从人的各种功利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通过“坐忘”,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心境。据有的学者论述,所谓“无己”,就是庄子一再强调的“忘我”,将自己对功名利禄、祸福寿夭的考虑,以及自我本身统统忘掉,达到齐万物,等生死,泯物我的境界。所谓“无功”,就是“无为而尊”、“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所谓“无名”,就是如天道那样的“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复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无己”“无功”“无名”是一种超功利的自然无为之道,是天人合一的、超越“人之道”的自由境界。[3]272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冯友兰先生的注释是:“由于他超越有限而与无限同一,所以他‘无己’。由于他顺物之性,让万物自得其乐,所以他‘无功’。由于他与道合一,而道不可名,所以他‘无名’”。[2]243
“心斋”、“坐忘”的目的是为了得“道”,现实的人只有通过“心斋”和“坐忘”才可以得道。庄子在《大宗师》中说女偊悟得了道,南伯子葵问女偊怎样才能学到道。女偊告诉他:守持三天,能够忘怀天下;已经忘怀天下了,又守持七天,而忘怀万物;又守持九天,能忘怀心性,而后能够一旦间豁然开朗。一旦间豁然开朗后就能见到常人所不见的境界。从而体悟大道。庄子说,“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鱼畅游于江湖中便忘记了一切,人悠游于道途也忘记了一切。得道的人,即使遭遇灾难,也能保持等闲置之的宁静自由心境,因为道之为物,往昔无不送,来者无不迎,一切皆其所毁灭,一切皆其所成全。庄子举子舆生病的例子说,子舆因为生病,把他变成了一个十分丑的人,他的朋友去看他,子舆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据庄子描述,子舆变得鸡胸驼背,五脏脉管在上,面部隐于肚脐之下,肩膀高出头顶,颈椎朝天。阴阳之气紊乱失调,但他心境安逸悠闲,若无其事。他的朋友子祀问他:“你厌恶这样吗?”子舆回答说:“不!我为什么要厌恶呢?如果造物主渐渐地把我的左臂变成鸡,我就要以此司晨报晓;如果渐渐地把我的左臂变做弹丸,我就要借此去打了鸟烤着吃,如果渐渐地把我的尾椎骨变做车了,把我的精灵变作马,我就正好乘而坐之,哪里还需要另驾车马呢?况且所谓得,乃是适时而成的结果,所谓失,乃是运应而去的趋势。能够安心适时,顺应世运变化的人,哀与乐不会入于心中,这就是古语所说的解除倒悬。不能够自我解脱的人,是被外物缠缚住了。自古以来,人不胜天,我又为什么要厌恶呢?”[2]71-72庄子借子舆的一番话,说明一个人只有得道,顺天之自然,才会不为物所缚而心地平静自如,这实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据说庄子妻死的时候,他鼓盆而歌;当面对好朋友施惠的责问时,他解释说人的生死乃气之聚散,如四时更替般。忘却人事,解除束缚,才能做到天人合一,达到自由的境界,与造物者为伴,在天地一气中遨游。
庄子认为,人世间的人都已经进入了藩篱,被套上了枷锁。欲望、名利、仁义等实质上就是套住人们的枷锁。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1]69意思是说,道德的毁败在于追求名声,智慧的表露在于争辩是非。名声是互相倾轧的原因,智慧是互相争斗的工具。二者都像是凶器,不可以将它推行于世。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夏桀杀害了敢于直谏的关龙逢,商纣王杀害了力谏的叔叔比干,这些贤臣都十分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而以臣下的地位抚爱人君的百姓,同时也以臣下的地位违逆了他们的国君。所以国君就因为他们的道德修养高尚而排斥杀害了他们。这是喜好名声带来的恶果。当年帝尧征伐丛枝和胥敖,夏禹攻打有扈。三国的土地变成了废墟,人民差不多死尽,国君自身也遭受杀戮,原因就是三国不停地使用武力,贪求别国的土地和人口。这些都是求名逐利的结果。名声和实行,圣人都不能超越,何况一般人呢?身被缚于外物的人是没有好结果的。《庄子》杂篇中的《外物》描述说:因为阴阳错乱,天地就会大震,于是雷霆大作,雨中夹着闪电,大树就被焚烧。人过度忧虑陷于利害之中就无法逃脱,警惕不安而没有成就,心就好像悬在天地之间,郁闷深沉,内心焦灼,内心欲求的清宁克制不了内心的焦急,于是精神颓废道已全无。这便自毁了。另一方面,庄子认为,山上的树木皆因材质可用而自身招致砍伐,油脂燃起烛火皆因可以燃烧照明而自取熔煎。桂树皮芳香可以食用,因而遭到砍伐,树漆因为可以派上用场,所以遭受厉斧砍裂。所以说求名利,显露智慧的人必然招致杀戮。所以庄子主张“离形去知”,排除一切外界干扰,顺乎自然,进入清宁无为的自由世界。这才是人生所应追求的。庄子因生于乱世而提出的这种人生追求的境界,虽于现实是一种悲观消极的态度;但这种精神追求却是人生追求的一种很高尚而自由的审美境界。这大概也就是西方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诗意的栖居”的存在状态吧。
三、追求“真人”境界的美学价值
庄子追求的“真人”境界,是对主客观的超越,是庄子追求精神自由的一种人生理想。庄子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有待”的逍遥游,是“无穷”之游和无己无功无名之游:“无己”才能物我两忘融入自然,“无功”才能无为,“无名”才能摆脱世俗利禄荣辱的束缚。“无穷之游”是游于“无何有之乡”,显然这是一种虚拟的境域,是对现实的超越,庄子不仅崇尚虚无,而且崇尚自然。追求超然物外的那种天然状态。“游心”是指主体的精神以超功利、无目的、非逻辑的态度与自由交往,是摒弃一切世俗得失、是非、善恶观念的以物观物,神与物游。庄子在《应帝王》中把“游”与“无”相联系,他说:“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是指在虚静中的体认,超出于外物而不损于天性,不违背自然规律。这些都是标举自然。[4]49由此看来,庄子强调“心游”的目的是追求人生的一种自由境界;“游”的主体是心,是指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不是指肉身超脱现实而升天成仙;游的方式是心游,是追求精神自由的方式,是思维运作和精神活动的无拘束无干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时空可以自由延展,物我交融,自由往复,意象可自由组合拼接,从而自如地实现对现实、范畴、观念、关系、秩序和思维规则的超越。“心游”是一种改变所处位置环境的自由自主的精神活动和运作,其本义有具体的超越身观局限的内涵,其要义是思维定向的扩大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但这只是一种精神的超越。
处于社会不公而层出不穷却无法矫正的生存境界,跋涉在怀才不遇、坎坷困难、无道和诱惑丛生的人生旅途,怎样从苦闷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怎样治疗心灵创伤,恢复心理平衡,只有“逍遥游”的超越,才能轻松地走出自我,走出世俗,走出社会,投向自然,享受自然赋予的灵慧,畅游生命。并用“万物一势”“千年一瞬”的胸怀和眼光对待世事。只有这样才能淡化和消除生存的苦闷与悲哀,求的精神上的自由和舒适,这对于庄子来说,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对必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人要获得自由,首先要摆脱社会强加于个人的压迫和剥削,这只有消灭残暴的剥削制度和社会动乱才有可能,显然这在庄子所处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其次,人处于社会和自然环境之中,人只有在认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之上,遵循着必须遵循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法则去进行活动,谋求生存,才能获得自由,在遵循必然规律的基础上,人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去改造其客观条件,才能使自己生活得更自由更美好。庄子所追求的人生的自由境界是放弃自己的主观努力,放弃一切现实的需求,而仅仅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具有空想的性质。再次,庄子的这种意识自由观是一种缩命论思想的表现。因为庄子认为社会生活中的贫福贵贱生死祸福等差别,都是出于“天”,出于“命”,人是不能抗拒的;只有自己在意识中取消这一切差别,人就得到了解脱,得到了自由。这其实完全否定了人的一切主观能动的现实创造能力。从来不想从现实中去解脱自己,也就取消了主观的一切能动的努力。这怎么能获得现实生活的自由?自由也就成为了一种精神性的空想。
庄子追求的“真人”境界所强调的心态是进行创造性活动包括审美创造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态。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游”能实现精神牢笼的彻底解脱,使主体获得敏锐灵动的原创力,思维想象在无障碍的运作中能够自由地驰骋、跳跃、变幻、组接。拘泥于自然物的自然法则和现实关系网络,主体就不可能无挂碍的作精神上的“逍遥游”,也就没有了艺术构思的充分自由。这种对客观属性、现实关系和法则的摆脱,只有在审美创造的领域才能实现,在客观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这种心态和思维状态下,主体的心理功能的能动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艺术创造活动才能顺利完成。在《庄子·杂篇》中的《田子方》中有一个故事: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致,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丰。有一史后至者,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这个故事把两类画师作了对照多数画师因为奉命为国君画画,精神状态都很紧张,各就各位,精心准备,十分拘束。只有一位画师与众不同:见国君本来要快步走的,他却慢吞吞的。接受国君的揖谢之后也不急于就位准备,却回到住所,光着身子盘腿而坐,很不拘礼节。但是宋元君却判断他是真能画画的人。[5]117-118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多数画师心中充满了“庆赏爵禄”,“非誉巧拙”等各种考虑,缺乏一个审美的心胸,即庄子所说的空明的心境。独有后者却超脱了“庆赏爵禄”,“非誉巧拙”等利害观念,他的心境是空明自由的,他的创造就不会受到束缚而能够得到自由的发挥。庄子之“游”的核心是对自由和超越凡俗的追求,趋向于精神和思维境域层次的提升和原创力的解放,这只有在艺术领域才有最适宜的发展空间。本来艺术活动是一条释放智慧生命原创之真力、宣泄情感积郁,进行自我调节放松的渠道。庄子之游,是哲学思考之表达,也是一种精神游戏和艺术创作,而且宣示了一种艺术创造的机制。[4]26-28《文赋》中有“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文心雕龙·神思》中的“神与物游”,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以物观物”、“无我”、“赤子之心”等皆突出主体心灵的高度自由,这与庄子“无待”的逍遥游相通,是庄子“逍遥游”之深远影响的体现。
庄子追求的“真人”境界,实质上是一种人生的审美境界。“游心”是庄子哲学中的特殊范畴。庄子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出了“游心”的概念,庄子在《人间世》中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已。”“乘物以游心”是指顺应自然获得精神活动的自由。在《德充符》中说:“……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游心乎德之和”是指摆脱感官知觉的束缚而在“德之和”的精神境界中悠游、陶冶。在《应帝王》中借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游心于淡,合气于漠”是指去欲忘己,将心灵游处于淡漠之中,融合予自然。古人认为,“心”是思之官,主思维的器官,是感情和智慧创造的渊数,是人之精神、魂灵之所在。“游心”是智慧人类所独具的思维和精神活动,是无挂碍的心灵遨游。“游心”是庄子一种精神性的感性追求,是对人类生命方式的一种审美式思考:人类在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忘却物我差别,淡化和摆脱对于物的束缚和欲求,对于死的恐惧和悲伤,畅快地享受自然赋予人类生命的乐趣。这是一种审美式的人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愉悦。庄子所生活的时代,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自由愉悦的生活方式。所以庄子所追求的“真人”境界,是人生的一种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在庄子时代不可能成为现实,只能是庄子理想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庄子提出并追求这种人生理想的审美境界,对于人类追求未来的理想生活方式具有永恒的审美魅力。
[1] 张慧, 汪燕.庄子[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2] 冀均.庄子[M].北京:线装书局, 2007.
[3] 王建疆.修养、境界、审美——儒道释修养美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涂光社.庄子范畴心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5] 叶郎.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心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