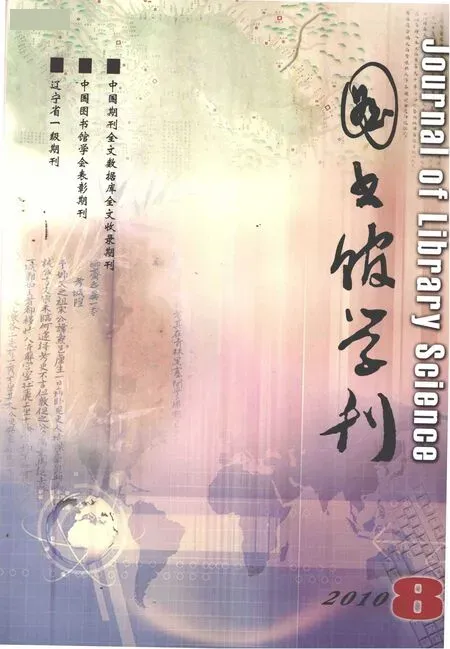中国校勘学学科体系发展研究综述
汪小琴
(安徽工业大学综合档案室,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校勘与典籍相生相伴,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被称为校书之开端。及至孔子,广搜博采,校雠整理,编《诗》、《书》、《礼》、《乐》,定《春秋》、《世本》。因此,段玉裁说:“校书何仿乎,仿自孔子。”俞樾也说:“校雠之法,出于孔子。”其他诸如子夏校“三豕涉河”、孔子不校《春秋经》误缺之类的记载还有很多。这说明,先秦时代,校勘的确已经存在。
但是,校勘作为一个有系统知识或理论的专门学科出现,则在西汉,后经魏晋至明末1000多年的发展,至清代进入全盛。清末至今的百年,随着社会的巨大进步,校勘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笔者拟就不同发展阶段各举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著作若干对中国校勘学学科体系发展进行综述。
1 蹒跚起步始于两汉
汉以前,兵祸不断,天下典籍散乱,典籍的地位无足重轻,校勘也不可避免地只能是无组织的自发行为。汉立,情况大为改观。汉廷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天下典籍尽搜。至武帝时,国家藏书已具相当规模。为合理收藏并利用所求典籍,汉庭设书目编制专职,又命人专司典籍抄录。
在长期的历史流转中,典籍难免出现讹误,缺乏可信性,不能直接引用。于是校勘开始作为一门学科,伴着汉立正式登台亮相。
两汉时期校勘学的代表当数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及东汉郑玄与高诱。
1.1 刘向、刘歆父子:中国校勘学奠基者
汉河平三年,刘向奉成帝诏整理校勘国家藏书。他检校不同校本,删重校异,并于校毕就所用校本、校勘过程及刊定本的篇目内容等撰“书录”奏于朝庭。刘向逝后,子刘歆承父业。他总结当时的校勘工作,写了著名的《七略》及《别录》。
刘氏父子为校勘学奠基,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校勘篇章。先广求校本,再校核篇目,删重去同,刊定篇目及篇目序次。至于校本间,虽为同一种书,不仅篇目不同,书名也不一致者,则还要定书名。以《战国策》为例,在未定书名之前,各校本“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刘向则认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因而,《战国策》并非原书名,乃是刘向所定。其二,校勘文字。关于这一点,刘向在书录里常有提及,如在《宴子书录》中,就提到《宴子》校本,“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汉书·艺文志》也有刘向校勘字句的记载,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其三,编列目录。刘氏父子把所校的书分为六大部分,即六略,每部分再分为若干种及若干家。他们仔细说明书的要旨,并对各家的学术源流加以阐述。
刘氏父子校书,规模空前,涉当时所有典籍,使其中绝大多数有了定本,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功不可没,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刘歆的《别录》与《七略》,更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是我国校勘学史上的图书提要之祖,后者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堪称编目之宗,对于研究目录学及各门类学术思想及学科分类的发展,都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基于此,刘氏父子被公认为我国校勘学和目录学的创始人。自刘氏始,我国的校勘学走进了体系时代。
1.2 郑玄:校勘群经,校勘学成为经学附庸
郑玄是汉代“通儒”之首,先后习今古文经学,“网罗众家、通融为一”,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后世称其经学成就及其学术流派为“郑学”或“通学”。
郑氏以校释的形式全面校勘了群经。他精古文字、通古音韵,深究古经讹误之因,创立了诸如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等校经之法。他“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兼录异文,考订疑误”,“博采通人而不轻信”,不擅改谬误,“有疑则阙,而不主观臆说”。有人叹其校勘之功曰:“校书千古之大业,未有盛于郑康成者。郑君之学,不主于墨守,而主于兼综,探其本原。”(段玉裁《经义杂记序》)
郑氏校经,重在考镜源流,厘析篇帙。其毕一生之功编辑、整理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他“辨章六艺、条理礼书;理查群书、注述旧典;校正错简、补脱订伪;审音定字、通假区分。”(张舜徽《郑氏校学发微》)
经学的今古文之争,自西汉至东汉,历200余年,既不利学习,又阻碍了学术进步。郑玄确定了几种经不分今古文的权威定本,使校勘学与训诂学一样,专为经学服务,成为经学的主要附庸。
1.3 高诱:校释《淮南子》等,校勘学始向发展时期过渡
高诱,略后于郑玄,以校勘闻于世。其注以训释为主,偶作一些校勘,校语常作“一作某”、“或作某”,不下断语。如《淮南子·天文》:“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其注:“专一作旉。”又《淮南子·精神》:“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乃性仍仍然。”其注:“仍仍或作聆聆,忧闻了。”
高氏著有《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战国策注》等,以《淮南子注》为最。
高氏注中的校勘简单明快,常引早期别本作对校。东汉以前,鲜有为经书以外的古籍作注者,高氏校注经书之外的古籍,是校勘学发展的重要转折,是由开创时期向发展时期的过渡,自此,校勘不再为经学附庸。
2 高歌猛进魏晋至明
自魏晋至明末的1400年,中国校勘学高歌猛进,校勘对象更广泛,内容更充实,方法更先进。这个时期,校勘不再专为经学服务、作经学附庸。代表性校勘家有唐陆德明、颜师古及两宋朱熹、彭叔夏等。
2.1 唐朝较勘
2.1.1 陆德明:著《经典释文》
陆德明,初唐著名经学家和训诂学家。其校释常从注音、校勘及释义三方入手,尤重前两者。治校态度谨慎,主张能定是非则定之,不能定则并存,认为“余既撰音,须定纰谬,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经典释文》)
其《经典释文》30卷,是一部注解群经的著作,旨在考证字音,兼及释义,涉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庄等14种经书,分称《音义》(如《周易音义》),合则称为《释文》。
陆氏被视为校勘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链条,对唐以后的校勘学发展影响甚巨。黄侃先生评价说:“详陆书体例,可谓闳美;虽尚有漏阙,待后来之补苴。”《四库全书·经典释文提要》则称其“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
2.1.2 颜师古:著《汉书注》、《匡廖正俗》
颜师古,唐贞观年间生人,曾参与唐初的五经考定工作,盛唐时著名校勘家。
较诸前人,颜氏对字词的训释更加系统且深入。其辨别字形,自成体例,与《说文解字》类字书辨析字义的方式相异,主要是采用“某,古某字”形式注释,用通用字来训释古字;其注释音读,目的明确,有直音法、反切注、比拟标音法等;其说解语义,形式多样,结合古今殊俗,详考名物、典制、史实等文化元素。
颜氏注书体例采用集注的形式,他广征诸旧注,或直接援引旧注,或先列举旧注音义,再辨析真伪、补充推衍。集注还含颜氏自己的释语若干。至于难定真伪者,则把异说或疑问同存。颜氏这样介绍自己的注书体例:“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至于诡文僻,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惑蔽。若泛说非当,芜辞竞,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汉书叙例》)正是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科学态度,使得颜氏《汉书注》成为《汉书》最重要的注本之一,其说多为孔颖达《五经正义》引用。
颜氏著《汉书注》120卷,含史实考证、词语训诂,并涉大量校勘。该书对《汉书》正文史料起到了补充阐释的作用,成为后世了解秦汉社会生活真实情况的重要线索。
为纠正当时经史版本及释文之谬误,颜氏又著《匡谬正俗》,其中论及校勘者甚多。该书为札记的首创之作,对训诂学发展贡献颇大。内容可概括为考释古籍正文、纠正古注误训、探求俗语来源等。以上两书在编写体例、研究课题、保存资料3方面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2.2 两宋校勘
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术问世并推广,书籍得以广泛流布。但由于失之校勘,讹误渐增。宋庭发现此弊,于是开局设馆,延请硕学名儒校订古籍。同时,民间校勘也很繁盛。两宋时期,校勘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代表人物有北宋朱熹和南宋彭叔夏等。
2.2.1 朱熹:著《昌黎先生集考异》
理学大家朱熹,深通训诂,精于校勘。其校勘成就悉见其所著《韩文考异》。朱氏“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同时,“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又各详著其所以者,以《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参伍而笔削焉。”
朱氏校勘,先对校、本校,然后用理校断是非。在理校中,其强调文势义理,在对校中“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这种求是的校勘态度超越了一般的校勘家,为后人称颂。
2.2.2 彭叔夏:著《文苑英华辨证》
彭叔夏,南宋校勘家。其校书“实事是正,多闻阙疑”。认为“书不可妄改”。彭氏常不以校本篇目为次,而以误例分类编列,开了“校例”之先河,后世校者多有仿效,如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淮南子》62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以及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等,都由借鉴彭氏体例而来。
彭氏著有《文苑英华辨证》10卷。该书实例丰富,文字简约,精密条例和清晰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世。
《文苑英华辨证》留下了宝贵的校勘财富飨食后世。《四库提要》将其校勘经验概括为3个方面,即实属承讹,在所当改;别有依据,未可妄改;义可两存,不可遽改。陈垣在谈到自己的《校勘学释例》时,认为其“以较彭叔夏之《文苑英华辨证》,尚欲更进一层”。显然,其校勘实践与校勘理论大部自彭氏处借鉴而来。
3 臻熟繁茂有清一代
清代是校勘学的全盛时期。有清一代,校勘学人才辈出。清初学风厌弃宋明理学,崇尚朴学。清代的朴学涵义很广,遵循汉郑玄等经师治学精神,并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对经传及其他古籍作校订、注释、考据。所以较诸前代,清代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更深入周密,更求真务实。此外,清代专书校勘深入而广泛。这些都为校勘学进入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清代校勘,方法多样,手段科学。清代校勘家严肃批判盛行于明代的随意改书之风,主张不可妄改古籍,他们注重总结典籍体例,归纳致误条例,在校勘时广泛利用多种材料与其他学科知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清代校勘代表有顾亭林、皖派及吴派校勘家、章学诚等。
3.1 顾亭林
清代朴学的开创者,提倡“博学于文”。他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所著《日知录》,每谈一事,详其始末,语必有证,证必多例;其引据很多,而无抵牾之处。这是后来考据学的典范。又著《音学五书》、《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石经考》等,为清代校勘学奠定了基础。
3.2 吴派及皖派校勘学家
顾亭林之后,清代较为有影响的有吴派及皖派校勘学家,分别以吴人惠栋及皖人戴震为代表,后人以为两人治学方法不同,称吴派、皖派。惠氏推崇汉儒旧说,比较谨守家法,所以泥于保守,偶有创新破旧之处,表现在其所著《九经古义》一书。吴派校勘家还有嘉定人钱大昕及吴人顾广圻等。前者治学态度严谨,有同于惠氏,但其所著《十驾斋养新录》及《廿二史考异》,其治经、治小学、治史都不专守一家、不迷信古本,精辟绝伦,突过前人。阮元说他的《考异》是“订千年未正之讹”,确非过誉。吴人顾广圻是惠栋的的弟子,一生从事校书,是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家,校勘态度审慎,提倡“书必以不校校之”。
皖派校勘学家的领袖是戴东原,治学主张同与顾亭林。他以治小学为基础,“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主张学《说文》,通六书,为治学之本。戴氏校书,均先审字音、字义,寻文理,然后用本校、他校,证成其说。其成就以校《水经注》为最著,观点多为后人采用。皖派另一代表卢文弨,为清代第一流的校勘家,治学严谨,每校一书,必搜罗众本,反复钩稽。校书极为精密谨慎,认为“古书流传,讹廖自所不免,果有据依,自当改正”。卢氏一生校书数万卷,自刻全书如《新书》、《春秋繁露》等20种,凡263卷,汇成《抱经堂丛书》,另有数十种仿《经典释文》体例,只录校记,成《群书拾补》30卷。
段玉裁,皖派领袖戴东原弟子,校《说文解字》及其他经传,极为精辟。段氏在校勘中勇于改字,但也有武断之处,以自信太过。
其他较为著名的皖派校勘家还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曾从戴东原学,所著《广雅疏证》、《读书杂志》最为精审。王引之承其家学,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这4部书是清代训诂学、校勘学的代表著作。
3.3 章学诚
章氏系浙江会稽人。校勘理论丰富,见解独到,认为自三国以降,目录编纂形式单调,失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效,主张“理有互通,书可两用”,以便查检。至于索引,章氏认为各种书籍所涉人名、地名、官阶、书目等“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都应大致仿《佩文韵府》,遇有疑难即“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关于方志,章氏提出了“详近略远”、“据事直书”及“求其实用”等论见,堪称精辟。
章氏图书目录编纂理论悉见其专著《校雠通义》。另主编了两部索引,所涉著录范围、条目内容及排列方法等,皆合法度。清代后期,索引品种及数量迅速增长,诚章氏之功。章氏还用史书体例编写地方志,立“志”、“掌故”、“文征”三书。
章氏是目录学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者,同时又是杰出的史学评论家,其《文史通义》也为后世所称道。
4 万象更新辛亥及今
自辛亥革命至今,生产发展,文化进步,校勘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版事业发达,印刷技术进步,许多原来罕见的古版书籍(善本)得以大量印刷发行,校勘古籍必不可缺的字书、类书也大量搜集重印。此外,还出版了一定数量的专书词语索引,发现和整理了大量竹简、帛书、敦煌遗书、碑刻等。现在许多图书馆、大学等都编写善本书目,以便人们按图索骥,借用善本。这些都为开展校勘工作创造了客观条件。
这一时期的校勘,人才济济,出现了王国维、周祖谟、陈垣等校勘大家;成果喜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国维《水经注校》、陈垣《元典章校补》、周祖谟《方言校笺》、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张友鹤辑《聊斋志异》三会本、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等。
可以预期,我国古籍整理工作将以空前的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校勘工作以及校勘学研究,也必将随着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1] 狄九凤.孔子在校雠学领域的卓越贡献[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5):68-69.
[2] 李茉莉.刘向、刘歆:中国图书校勘学和目录学的创始人[J].兰台世界,2008(2上半月):60-61.
[3] 王霞.郑玄与校雠学[J].兰台世界,2008(1上半月):58-59.
[4] 钱玄.校勘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版:1988.
[5] 窦秀艳.论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雅学文献价值[J].东方论坛,2007(3):43-47.
[6] 余光煜.颜师古汉书注的学术贡献[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185-188.
[7] 闵晓莲,张洁.彭叔夏及其《文苑英华辨证》[J].江西图书馆学刊,2008(4):124-126.
[8] 胡喜云.清代校勘学研究综述[J].新世纪图书馆,2008(4):59-62.
[9] 苏嘉.章学诚和《校雠通义》[J].出版史料,20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