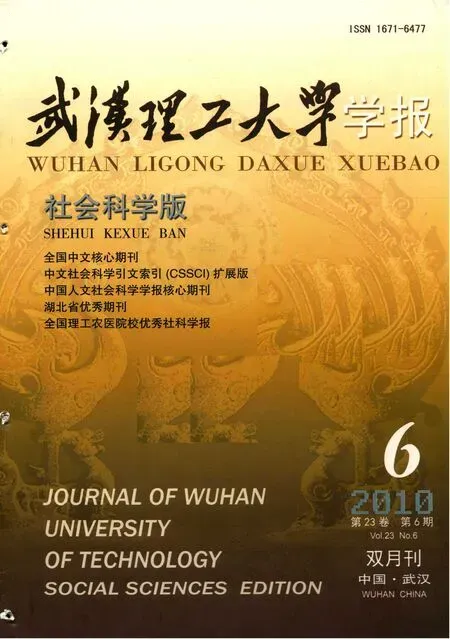中国互联网政治功能研究述评*
温琼娟,陈先红
(1.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中国互联网政治功能研究述评*
温琼娟1,2,陈先红1
(1.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互联网作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同传统的大众传媒一样,承担着社会系统的政治功能。从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政治沟通和建构公共领域四个方面对国内互联网政治功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述评。
互联网;政治参与;政治沟通;舆论监督;公共领域
关于传统的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美国的经验学派和欧洲的批判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经验学派侧重从体制内去探讨,而批判学派则侧重从体制外去探讨。
传播学的奠基人及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于1948年在其专著《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媒介具有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的功能,而施拉姆则在《传播学概论》中将这几点重新整理以后,确定了大众媒介具有监视(收集情报)、协调(解释情报,制订、传播和执行政策)、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等几项政治功能[1],概括了大众媒介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过程。而在现代民主社会,大众媒介体制内的政治功能具体体现为:其一是政治参与功能;其二是权力监督功能;其三是政治沟通功能;其四是政治控制功能;其五是议程设置功能[2]。议程设置是实现传播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成为功能,同时,在民主社会,政府或政党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实现政治控制的,因此,政治沟通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实际上具有相同的内涵。
然而,欧洲批判学派的学者则倾向于从体制外去思考媒介的政治功能,从而把大众媒介看成是公共领域的代表。公共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市民该应有相等的自由表达机会,并且能够自主地组成公共团体,其讨论的主题应以批评公共事务为主[3]。
在政治体制允许的范围之内,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影响政治系统的运行,而政府(政党或政治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沟通干预政治系统。前者的主体是公民,后者的主体是政府(政党或政治利益集团),两者在话语博弈的过程中形成了张力,由此构成了政治“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体制之外的客观存在,但是它对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进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传统的大众媒介的政治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与政治沟通,体制外的建构公共领域。这四个方面的政治功能的总结,采用了政治学的视角和传播学的方法,体现出两个学科在该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
而作为新媒介形态的互联网,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长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它在政治系统中承担着和传统大众媒介同样的政治功能。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性,使得它在承担政治功能的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一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搜索中国目前有影响的几家网络中文学术数据库,将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所发表的关于互联网政治功能研究的主要论文汇总筛选和分类归纳,并进行了述评,以期为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一、政治参与功能
政治参与指的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通过和实施的过程。通过政治参与,公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争取自己所得的权益,并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往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实现的。互联网作为新兴的大众媒介,它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手段,在提高政治参与程度和推进民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传统的政治参与相比,网络政治参与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具有平等的参与主体;自由的参与空间;低成本的参与手段;虚拟的参与身份等[4]。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为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平台;其次,互联网的应用有利于促进利益表达和利益聚集;再次,互联网丰富了政治参与的渠道[5]。尤其有意义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平等与自由,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6],从而解决了大规模政治体系中的协商民主问题,推进了“草根”民主的发展[7]。
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民通过网络直接向政府机关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参与重大事项讨论;表达一定的政治感情;监督政府机关的运行;进行政治投票[8]。而政治参与使用的具体的网络工具包括:BBS留言板、评论、博客、论坛等诸多方式。
然而,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并不必然地催进民主的发展。我们首先所面对的现实是,尽管我国已经有近3亿人口使用互联网,总量虽多,但相对人口总数来说,仍旧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在使用程度上也有明显的差异。由于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的差异所造成的人们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这种“数字鸿沟”必然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9],使得政治参与依然是小部分公民的参与,并且亦有可能成为社会分化和断裂的催化剂。
此外,还存在敌意参与、无序参与以及非理性参与等问题[10]。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网络政治参与不仅不能推进民主,而且还会威胁国家政治安全,贻害无穷。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既可能缓解政治冲突,促进政治稳定;也可能激发政治冲突,解构政治秩序。网络时代和谐与稳定政治的实现途径关键是政府和公民能否利用好网络媒介,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关系[11]。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从互联网本身着手,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主体精神,倡导理性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文化。但是,网络政治参与的社会现实性决定了民主不能仅从发展网络去建构,推动民主更需要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成熟,网络政治参与环境的改善[12]。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积极推进。而政府要实现这种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将传统的管理模式改变为服务型的管理理念,扁平化的管理组织,人性化的管理方式[13]。在此前提下,政府必须从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促进网络技术发展,规范网络秩序,加速国家信息化进程等多个层面入手,以推动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深化[14],并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和规范化。
网络政治群体的不断壮大,网络民意的理性聚集,网络与传统媒体的共鸣及政府开明的制度供给,这些都是网络政治参与有效性的基本保障[15],而这些,只有在解决了以上问题以后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二、权力监督功能
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权力监督是公民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了解和评论的过程,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重要手段。
而公民有效地实现权力的监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权力执行过程的透明化,或是对滥用权力行为有揭露之自由;二是公民具有对以上两种情况发表言论的空间,从而形成舆论,通过舆论监督权力。因此,互联网作为权力监督的工具,其作用也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作为信息来源,保证公民的知情权;二是通过网络舆论监督,实现公民的表达权。
(一)网络知情权
网络还民众知情权的成就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传统垄断媒体在互联网时代不得不拱手相让的。官方垄断媒体往往被禁止采访报道而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技术特点造就了自由、平等、兼容、共享的技术准则和网络精神,促成了小众话语、个体话语对垄断传媒话语的技术消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官方金字塔式权力控制模式[16]。
然而,通过网络争取知情权所反应的事实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知情权受阻,而网络提供了信息交换的平台,网民们通过信息“拼图”的方式,力图拼凑出事实的真相。从最近几年发生的众多“网络事件”来看,网络知情权并非具有制度化的保障,而更多是网民的自发行为,以及政府的被动行为。
于是,有学者认为,网络知情权不是具有现实性的政治权利,只不过是一种充满了崇高幻觉的虚拟权利。用网络知情权的方式代替真正社会权利的实现,这一点正是网络时代政治文化生活中值得警惕的地方[17]。
在民主社会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公众应当知晓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隐含着一个假定,那就是政府行为必须透明公开[18]。政府、立法及司法机构是公共决策的主体,因此,必须将决策及决策的依据告知公众,以说服公众,或者接受公众的监督。作为目前效率最高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可以用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推进民主社会的进程,亦可以沦落为散布流言的帮凶,损害政治稳定。
(二)网络舆论监督
舆论是公众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长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19]。因此,它必然对决策机构形成强大的压力,使得决策机构的行为展现在公众的关注之下,从而实现了对权力的监督。
因此,权力监督的第一步是公众知情,第二步就是公众形成舆论。而网络舆论则指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介而言,网络是舆论得以形成并传播的主要渠道。
传统大众媒介反映出来的舆论主要体现的是媒体组织的意见,而互联网使公众有了直接表达各种意见的渠道,其传播特性加速了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公众舆论在网上聚集放大,使公众舆论力量的体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独特的舆论形态[20]。传统大众媒介舆论监督的侧重点在于宏观、宏大的事件上,而网络舆论监督则很典型地体现出“草根性”,小处见大,通过普通网民发现的小问题,往往折射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天价烟局长”、“钉子户”,等。这是由于在网络中,由于传播与沟通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数量众多但分散、弱小、独立、细微的信息,网民“草根”声音通过聚合形成强大的话语场和传播效力因而形成了网络舆论的长尾效应[21]。这正好弥补了传统大众媒介舆论监督范围和力度的不足问题。
网络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事件的发生或热点、敏感话题的出现;各种意见通过论坛、博客、即时通讯等平台进行交流融会形成倾向意见;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振”形成舆论的立体传播[22]。网络舆论通过权力监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并且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23]。
然而,同时,网络舆论亦存在以下明显的问题:一是产生网络暴力;二是易于干预司法;三是制造虚假民意。
(三)网络暴力
不可否认,人性、道德和正义是网络暴力乃至人肉搜索的驱动力,然而,公民社会的前提是,所有的行为都必须在理性、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而网络暴力形成的“土壤”是网络表达中的非理性,网络暴力与网络中的“群体”直接相关,网络暴力还表现为自我纠结的道德困境,网络暴力体现了网民社会参与的不成熟性[24]。网络平台塑造了“非实体性”的舆论主体,网民以群内同质化、群际异质化的特点聚集,志同道合的网民群体易于出现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25]。非理性和群体极化很容易导致网络暴力的产生,从而扭曲网络舆论的真正内涵。
(四)干预司法
司法是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领域,网络舆论影响司法的最主要原因在于网络传播具有强化“议程设置”和弱化“沉默的螺旋”效果。“议程设置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个体可以很方便地将一个日常的案件通过网络传播来让大众知晓,从而成为社会性案件,并通过设置某一讨论主题来表达网络上的“民意”,以网络舆论来影响司法;“沉默的螺旋”弱化对司法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促进了司法的民主化[26]。
舆论与司法存在两种互动状态,网络舆论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以及网络舆论对司法的异化。良性互动促进司法公正,而舆论对司法的异化则会导致“媒介审判”,影响司法公正[27]。
(五)虚假民意
所谓民意,至少要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然而,网络舆论是否能够真的代表民意呢?而网络舆论的事实是,情绪化舆论往往形成一边倒之势,构成了社会民意的假象,误导公众,不利于公众的理性思考[20]。最为严重的是,被俗称为“网络黑社会”的势力,潜伏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论坛上,操控不明真相、缺乏理性思考的广大网民,从而制造虚假网络民意,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取利益[28]。虚假的网络舆论传递出欺骗性的民意信息,甚至会误导政府的决策。
面对网络舆论存在的以上问题,我们有必要找出良好的应对之策。首先,建立健全监管网络舆论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网络从业人员和网民的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道德观教育,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党报也应在引导网络舆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29];其次,促进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之间的互动,倡导协商型司法正义,为网络舆论设置边界,防止“网络媒体审判”,适度限制网络“公权力”,适当宽容网络舆论,加强司法公开和民主[26];最后,除了加大技术上的控制和立法的强度以外,政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根据不同舆论主体群落的不同特点,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针对网民易受权威左右的特点,加强引导者的权威性[25]。
三、政治沟通功能
“政治沟通”作为从美国引进的概念,对应的英语是political communication。在美国,political communication研究始于20世纪50—60年代,这个概念自诞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流派众多,从未有过清析的界定。而这个概念在中国则更为复杂,由于对communication这个单词理解上的差异,存在“政治传播”和“政治沟通”两种不同的译解。实际上,广义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应当被理解为政治传播,指的是大众传播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30];而狭义的political communication则应当被理解为政治沟通,是指掌握一定政治资源的政治主体如政府或政党,通过一定的媒介输送、获得和处理政治信息的行为或过程[31]。因此,政治沟通应当包含在政治传播的范畴之内,是政治传播的一个方面,是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和传播学经验学派共同研究对象。除此之外,传播学的批判学派及政治经济学派,致力于对媒介、权力和资本的共生关系进行批判性的政治传播研究。因此,也可以认为政治沟通是狭义的政治传播。
由于概念理解上的分歧,导致国内学者对政治沟通研究投入不足。本文认为,站在政府或政党的角度,探讨政治信息传播的技巧、方法和效果的论文,均属于政治沟通类论文,而不管论文中是否称这种形式为“政治沟通”。
在传统的大众媒介环境下,政府掌握了媒介的近用权和消息来源,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挑战了高度集中控制的媒体管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府与公众在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关系状态,呈现出政府近用新媒体能力的低下,垄断消息来源地位被瓦解,民众近用新媒体权力扩大,消息来源角色增强的二元博弈格局[32]。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信源的多样化及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使得“把关人”角色缺失,“议程设置”草根化,因此,很容易引发公共危机,从而损害政府公信力和声誉。而在突发性的公共危机状态下,由于危机态势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良好的政府声誉就成为社会公众预测和解释其未来行为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因素[33]。因此,在政治沟通中,政府声誉是一个关键因素。
而在公共危机传播过程中,通过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官方的政治沟通和民间舆论构成了双重话语空间[34]。官方模式主要有封闭控制模式、单向宣教模式和双向沟通模式,与之相对,非官方模式主要有揭露模式、抵触模式和肯定补充模式,二者一一对应形成双重话语空间的三种互动模式:控制封闭VS揭露模式;单向宣教模式VS抵触模式;双向沟通模式VS肯定补充模式。这三种互动模式分别呈现出积极或者消极的传播效果[34]。这几种模式为公共危机中的政治沟通提供了参考。
总之,政治沟通畅通,不仅可以使党和政府的决策合理化和民主化,维护和巩固政治秩序,而且还可以提升政府形象,促进公民相关政治权利的实现[31]。
四、建构公共领域功能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政治学概念。根据他的定义,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35]。
展江认为,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演进的论述,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线索,但这并不意味“公共领域”对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意义。在我国大力发展民主与法制,推进市场经济的情境下,“公共领域”的存在非常必要。他亦提出,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那么,新的传媒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建构有何种影响呢?这正是思考互联网对公共领域建构的切入点[36]。
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对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37],虚拟现实技术是在信息意义上对实体属性的实现,为现实公共领域提供了虚拟论域平台,人们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而充分进行的自由和交流性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为公共领域的重建带来契机[38]。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对互联网上言论最丰富的BBS和博客进行研究,网络虚拟社群具有拓展网络公共领域的意义[39];网络公共领域内的参与主体已经初步具备了哈贝马斯定义下的私人属性[40];中国大陆的“两会”博客是目前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41];“强国论坛”已经具有现实的公共领域的特征,可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42]。
然而,公共领域的形成首先需要外部制度化空间,还需要内部要素包括参与者、媒介和共识。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网络传播目前只能提供公众参与的意见平台,尚不能被看作公共领域勃兴的契机[43]。此外,由于进入网络空间受经济、知识等门槛限制,以及网络空间语言霸权、数字鸿沟等造成的不平等,仍制约着网络空间成为公共领域的可能[44]。因此,“强国论坛”可以称作是一种公共话语空间,而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45];尽管“华南虎”事件体现出了公众的平等参与及理性批判等能力,但是,公众舆论的意见集合与权力机关决策过程之间还存在断裂,此外媒体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还不能给公共领域提供全面发展的空间[46]。
当然,也不排除未来民主社会出现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第二条媒体通道,即在保留传统媒体的功能的第一条媒体通道之外,出现脱离第一通道控制,纯粹表达不同的个体或团体公众参与的意见和异见平台[43]。如果这条通道有存在的可能性,那互联网无疑是最理想的平台。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论证在网络舆论中,官方话语、民间话语之间存在着52%的意见中立者,这52%的中立者,大多数通过引导可以转化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47]。
五、结 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对互联网政治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领域与传播学领域,处于两个学科的交集点。由于互联网具有迥异于传统大众媒介的特性,因此,它从扩大政治参与,加强权力监督,促进政治沟通和建构公共领域四个方面承担着社会系统的政治功能。但同时,互联网亦有可能导致无序的政治参与,民意的被操控及司法的扭曲,它并不能决定其自身是否能够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不必然地推进民主。因此,要实现互联网的积极的政治功能,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民意识的觉醒,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保证是理性的主体在使用互联网;二是法律制度的完备,民主需要规则,没有规则的民主只会走到民主的反面。
到目前为止,尽管就互联网政治功能的四个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于网络知情权的研究非常有限,目前仅有一篇论文以此为主题,其他论文中仅有少量内容涉及,而知情权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其次,由于对“政治沟通”概念的理解难以达成共识,从而导致了这个方面研究的严重缺失。再次,虽然有关互联网政治功能的研究的广度蔚然可观,但欠缺深度。大部分研究仅停留在描述现象,总结问题,提出建议层面,并没有更深入的研究,而且,结论和建议少有创新。最后,科学细致的实证研究缺乏。仅有少量研究使用了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绝大部分研究停留于描述层面。同时,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假设,却鲜见有对假设的验证。这些不足有待我们今后的研究者着力改进和推进。
[1] 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陈 亮,周立方,李启,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2] 张 昆.大众媒介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1):96-100.
[3] 张锦华.公共领域、多文化主义与传播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97.
[4] 李尚旗.网络化政治参与的特点、双面效应及其应对[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4-18.
[5] 杜 洁.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3(1):70-74.
[6] 赵春丽.网络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新形式[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9-22(B07).
[7] 陈剩勇,杜 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5-12.
[8] 徐黎明,姜艳艳.论网络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意义[J].理论探讨,2008(4):20-22.
[9] 韦 路,张明新.数字鸿沟、知识沟和政治参与[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143-155.
[10] 安云初.刍论网络政治参与对执政安全的负面影响[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7(4):19-23.
[11] 郭小安.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新型关系及其影响[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72-76.
[12] 王有加.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民主再思考[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8(6):122-124.
[13] 张恩韶,文军.论政治参与和政府管理在网络空间的良性互动[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2-75.
[14] 刘 文.网络时代政治参与的难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03(6):14-18.
[15] 陶建钟.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分析[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6):100-107.
[16] 赖俊文.互联网络助推中国式民主进程[J].现代传播,2009(2):139-140.
[17] 周志强.“网络知情权”,一场虚幻的狂欢?[J].人民论坛,2009(5):40-43.
[18] 斯蒂格利茨.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J].环球法律评论,2002(3):263-273.
[19] 陈力丹.舆论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0] 刘正荣.从非理性网络舆论看网民群体心理[J].现代传播,2007(3):167-168.
[21] 周云倩,吴诗祺.网络舆论监督的长尾效应[J].新闻爱好者,2009(18):112-113.
[22] 樊金山.网络舆论视域下的执政创新[J].新东方,2009(3):42-45.
[23] 李雪芳.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9(29):184-185.
[24] 彭 兰.如何认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现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08-25(06).
[25] 郭光华.论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6):110-113.
[26] 杨 治.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以司法个案的分析为视角[J].法律适用,2009(1):41-45.
[27] 王 军,李王颖.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舆论监督与司法——以“杭州飙车肇事案”为例[J].现代传播,2009(4):42-44.
[28] 柴会群.网络舆论操控食物链[N].南方周末报,2009-03-26(A06).
[29] 田群兰.论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新闻知识,2009(5):60-62.
[30] 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1(3):68-77.
[31] 淦家辉.中国网络政治沟通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9.
[32] 陈先红.媒介近用权: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以汶川大地震为例[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25.
[33] 陈先红.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声誉指数测量[J].现代广告,2007(6):24-28.
[34] 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C]∥第二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主题发言论文,香港,2008.
[35]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
[36] 展 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123-125.
[37] 苏晋京.网络革命与中国公共领域的发育[J].重庆社会科学,2002(3):54-56.
[38] 张如良.虚拟现实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7-70.
[39] 唐大勇,施 喆.虚拟社群抑或公共领域[C]∥邓炘炘,李兴国.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0] 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J].当代传播.2005(3):52-54.
[41] 蒋艳芳.两会博客与公共领域的建构[J].青年记者,2006(10):63-64.
[42] 王君平.虚拟的网络社区现实的公共领域——浅谈强国论坛对公共领域的重构或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6):68-74.
[43] 陈 钢.公共领域型变的传播学观照[C]∥中国传媒大学第一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文,2007.
[44] 刘丹鹤.网络空间与公共领域实践[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71-74.
[45] 彭 兰.强国论坛的多重启示.关注中国[M]∥官建文.纵论天下:强国论坛这五年.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46] 胡忠青,邹华华.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华南虎事件”[J].新闻界,2008(1):56-58.
[47] 陈先红.中立的多数:双重话语空间的第三方立场和公关责任[C]∥第三届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主题发言论文,澳门,2009.
Review of Research on Political Functions of Internet in China
WEN Qiong-juan1,2,CHEN Xian-hong1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2.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81,Hubei,China)
Internet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a kind of new mass medium,which can undertak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social system just like traditional mass media.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internet political functions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power supervi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Internet;political participat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public opinion supervision;public sphere
G206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6.006
2010-09-10
温琼娟(1979-),女,湖北省南漳县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关系与广告研究;陈先红(1967-),女,湖北省武汉市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学及公共关系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课题(08BXW026)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