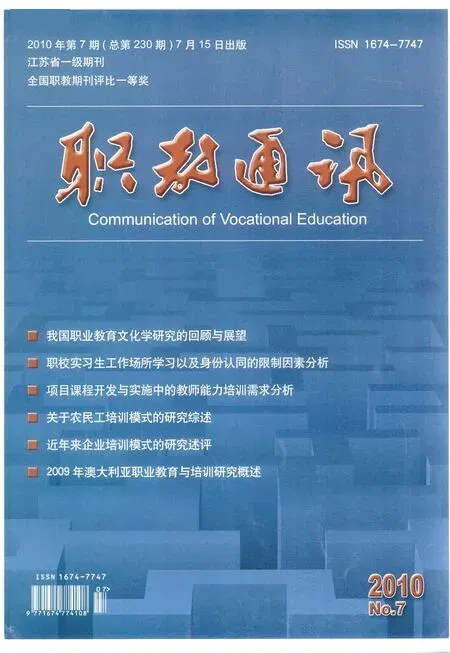一次与农民或者工人或者商人兄弟的对话
臧 否
一次与农民或者工人或者商人兄弟的对话
臧 否
我曾经在公交车上偶遇一位农民工兄弟,那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问我手机短信里的一个地名怎么读。他说他是阜阳人,“我只上了小学二年级,很多字不认识。我们那个地方很穷,所以我和老婆才到这里打工的。”
“那你在这边做什么?”我以为以他这样的知识水平,大概只能做苦力吧,他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焊工,有十年了。”
“电焊,那可是技术活啊。”说到工作,他的兴致也来了,“电焊早过时了,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气冷焊,比电焊结实多了。”我不关心哪个焊法更有效,就问道,“那你从哪学的技术啊?”
“跟老乡学的。我们有老乡在外边做这个,村里人就都跟他学,其实也不难,但学徒的时间挺长,因为学徒的时候,师傅只要给我们50块钱一天,而正常情况能有100块钱一天。这次去沭阳是想换个工作。有个老乡说在那边卖药挺赚钱,想去看看。”
他的话又一次让我惊讶,一个熟练工竟然如此随意的换工作,与我的想象大不相同,于是我问:“你现在一个月的收入也将近3000,而且还有一手技术,卖药不一定比现在收入高,也不一定更有保障吧?”
“哪有3000,我们是做一天拿一天的钱,一个月最多上二十几天班,下雨就得休息,厂里没活也得休息,一个月也就2 000多一点,老乡说,卖药比我现在的工作舒服多了,一个月大概有3 000块钱左右。做焊工也没什么保障,还不是人家说不要你就不要你。”
“焊工不是都有资格证书吗?有了证,你到哪里都可以吃饭呀!”
“我文化低,考不了。有人考了,他们能拿150一天呢,都是一样的活。做焊工太辛苦,我年龄不小了,再往后也做不动了,换个工作试试呗。”
我想鼓励他两句,“你也不过才四十岁左右嘛,怎么会干不动呢?”他不自然地笑笑,“我才三十五,我从小就显老。”我一下不知该再说些什么。好在车到站了,没有必要继续这令人尴尬的谈话了。他拎起行李箱,走进雨中,我也下了车,走向一个不同的车站。
我也有很多农村的亲戚在外打工,但这位兄弟给我的感觉更加真实,大概是因为在亲戚间的交流中人们更愿意表现自己光鲜的一面吧,我颇有感触,所以回到家就把这次谈话记录了下来。
“农民工”这个词实在是个很奇妙的发明,为什么有农民工,而没有农民商、农民学、农民兵呢?国务院《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把农民工界定为户籍身份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也就是说,这个1984年才被提出的概念涵盖了三个产业,农民工就是一群在三者间进行职业转换的人员,农民工与一般的产业工人或商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还拥有土地,所以在理论上他们从农民向工人或商人的职业转换是可逆的。但在实际中,这种可能性正在变小。
如果接受以上的定义,农民工现象绝不是一个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新事物,清末与民国时期就曾有过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研究指出当时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相比更倾向于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以这个视角看今天的农民工,也许还要加上年龄等因素。我遇到的这位兄弟至少已经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到商人的转换,看样子回到农村的可能性不大,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则因为从小就接受制度化的学校教育,技术水平明显更高,而且从未务过农,更加不可能回到农村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流行的话语把农民工定位于弱势的农民,显得有些过时。不知从何时起,农民工成为了一个关涉公平与正义、掠夺与剥削的沉重话题,也成了这个国度的痛处,引得无数自以为脱离了这个群体的研究者不断为这个问题附加道德议题。但这些道德讨论似乎只改善了问题提出者的生活,而与那些农民工没有关系,他们依然或艰难、或幸福、或既不艰难也不幸福地生活着,就像我碰到的那位兄弟。
我更愿意把农民工问题看作一个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动者的问题。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个心理学研究生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他署名“难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辩护:非技术工作并非没有技术,他花了一个星期才基本熟练起来。同样,农民工并非都没有技术,他们在岗位上习得了学校无法教给他们的经验与技能(也许这些都被学校定义为非技能),所以在骨子里,他们鄙视学校形式的职业教育,就像这位兄弟暗示的:“其实不难”的技术何必学几年?
随着新增人口的减少和高校录取率的增加,职业学校的转型无法避免,也许,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动人员就是未来职业学校最主要的服务群体。果真如此,职业学校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如何为低技术人员频繁的职业转换提供便利?我们是不是准备好重新定义技术与技能?我们是不是有能力为成人而不仅仅是未成年的学生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