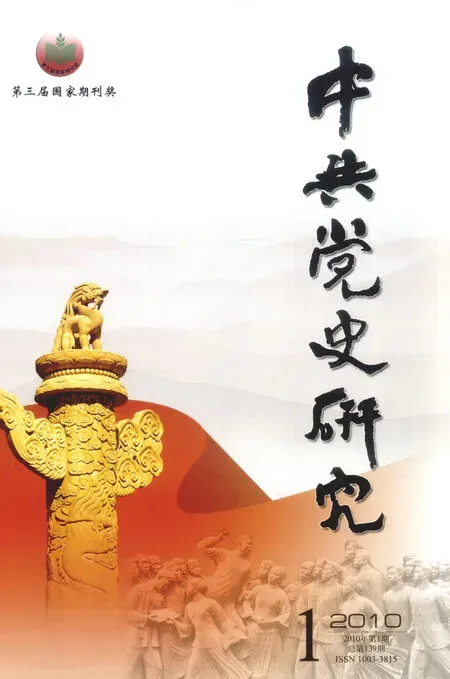对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中一些问题的探究
伍 星
对中共无线电技术侦察史中一些问题的探究
伍 星
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在这个科技、人才密集的斗争领域,共产党战胜了具有优势的国民党,创造了隐蔽战线上的奇迹。近年来,有关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侦察斗争的历史记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本文通过查阅和考证现有文献,走访诸多亲历者及其亲友,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寻其中的历史真相。
无线电技术侦察斗争;隐蔽战线;历史真相
Abstract:Radio intelligence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role in the CPC’s struggle to seize state power.In this science and talent intensive fiel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beat the Kuomintang and created a miracle in the covert front in spite of the latter’s obvious superiorities.Over recent years,historical narratives about 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the CPC and the K MT,in the covert front,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radio intelligence,have come into people’s view.Through looking up and investigat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ing those who personally took part in the work of this front and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the author tries to reveal in this article the historical truth in a realistic approach.
无线电技术侦察情报源自敌方机要核心,来源权威、准确、可靠,且及时、经济、安全,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在这个科技、人才密集的斗争领域,共产党战胜了具有优势的国民党,创造了隐蔽战线上的奇迹。近年来,有关国共两党在隐蔽战线,特别是无线电技术侦察斗争的历史记叙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为开展这一长期禁忌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一时间,文艺作品畅销,影视作品热播,演义出许多离奇的故事,这无可厚非。但确有一些文章,由于对特殊战线的工作缺乏基本了解,出现基本概念的偏差;更有一些文章,不顾史实地夸大其词。本文通过查阅和考证现有文献,走访诸多亲历者及其亲友,力图以实事求是和严肃客观的态度探寻其中的历史真相。
一、关于苏共的帮助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用了不少文字对中国工农红军中忠实精干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了介绍,并特别提到苏联为中国红军培养了密码破译人员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71~72页。。遗憾的是,那些好心向索尔兹伯里提供史料的人,并不完全了解这项事业创立的真实过程,而索尔兹伯里又未找到当时仍健在的早期参加技术侦察工作、特别是从事密码破译工作的同志加以核实。实际的情况究竟是如何呢?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无线电通信工作的早期,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确实予以了支援。
经过了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来的白色恐怖后,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逐渐恢复,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创立了红军,并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加强对各地党委和各红色区域的领导。而此时党内联系全靠秘密交通员在上海、江西间往返,一次需要两个多月,速度慢且不安全。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在上海着手建立无线电通信。10月周恩来开完六大回到上海,就决定让李强研制无线电收发报机,派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同年10月,中央特科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建立,科长李强。他和蔡叔厚、涂作潮等同志一起试制收发报机,奋战一年,终于在1929年造出自己设计的第一部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此时,张沈川在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第6军用电台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结业。自此,李强和张沈川一起建立起中共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负责报务工作的是张沈川、蒲秋潮、黄尚英。
此后,中央特科通过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机务和报务的人才。1930年3月,中央特科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由李强负责。学员有王子纲、黄尚英、伍云甫、曾三、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1931年6月,举办了一期机要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学员有宋侃夫、王逸群、朱邦寅、杨南石、蔡威等20余人,结业后多被分配到鄂豫皖苏区工作。①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年,第289~311页。
选调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28年夏天。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会后即提出要求,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已查到的文献显示,自1929年至1937年期间,先后有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29—1930)的毛齐华、沈侃夫(陈宝礼)、陈昌浩(提前回国)、程祖怡、方廷桢(方仲如)、李元杰,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信学校学习(1929—1930)的涂作潮、宋濂、谭献狄、刘希吾、段子俊,在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学习(1932—1937)的李春田、王东、加夫、毛城(女)、张培城、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等,接受了无线电通信技能的培训②李立、董建中主编《光辉的历程》第1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0~491页。。1930年,首批学成者奉命回国,从莫斯科到海参威,经东北回到上海。
1930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建立了电台通报。同年9月,报务员由伍云甫接替,以后由曾三担任。10月,毛齐华从苏联回到上海,着手建立国际电台的工作。③穆欣:《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第296页。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第一,特科时期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培养了早期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这些人后来多数成为党和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骨干力量。但并没有资料显示在特科时期开展过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第二,早期苏联为中共培养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在党的无线电通信的初创时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但并没有为中共培养无线电技术侦察人员特别是密码破译人才。经查,从苏联留学归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后也都没有进入无线电技术侦察领域工作。相反,据在延安军委二局工作的余湛回忆:“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后,可能是由于他的报告,苏联情报机关对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发生了兴趣, 于1942年派出他们的密码破译专家来到延安,同我交流技术和资料。我方诚实地满足了老大哥的要求,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对我方的相应要求,却给了一个‘没有这个任务’的回答。”
也许是向索尔兹伯里介绍的人把苏联为中共培养无线电通信人员的事,误说成苏联为中国工农红军提供密码破译技术;也许是索尔兹伯里误解了他们的话,以致以讹传讹。于是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一提到破译,就经常不断地出现苏联人的身影和声音,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关于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端与队伍的创立
中共内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特别是密码破译工作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在什么条件下开创的呢?为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中革军委二局初创时期的历史。
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端与其无线电技术队伍的创立同步发生。1930年12月和1931年1月,红军先后围歼国民党军张辉瓒师和击溃谭道源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在战斗中缴获一部半电台(另有半部砸坏),俘虏10名电台人员,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队伍提供了必要的人才、物质和技术条件。1931年1月6日红军第一次架起收报机,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开始对敌军电台进行侦听,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和7月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无线电侦察即发挥了重要作用。邹毕兆称,王诤、刘寅是红军无线电侦察的开头人①邹毕兆:《对前总二局密码破译工作的回顾》,《总参谋部回忆史料(1927—1987)》,解放军出版社, 1995年,第56~63页。。
与此同时,1931年1月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发出命令,举办无线电训练班,从红军中抽调年轻、有一定文化的可造就的青年学习无线电技术,培养出红色的无线电队伍来。自1931年2月至1933年5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先后举办了5期无线电训练班,另外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也举办了三期训练班,总计140余人,其中不乏日后在通信和技术侦察领域中的重要领军人物和骨干,如一期的胡立教、曹丹辉、李力田、曹祥仁(红3军团一期);二期的李白、罗舜初、邹毕兆;三期(红军通信学校)的钟夫翔、钱昌鑫(钱江)、肖森、赵宾玉(宾玉)、唐道德(唐明)、黄荣、李行律、雷永通;四期(红军通信学校)的江腾芳(江文)、胡备文、黄萍等人②李立、董建中主编《光辉的历程》第1册,第158、492~493页。。
由于技术侦察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1931年12月,侦察工作从通信部门分出去,单独成立红一方面军总部侦察科,由刚从上海特科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曾希圣任科长,建立专门的技术侦察台,领导总部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最早的报务员有胡立教、李力田等人。
1932年初,当国民党军发现其无线电通信严重失密,随即加强管理和开始全面使用密码通信后,红军的无线电侦察遇到了极大困难。1932年2月红军赣州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线电侦察困难而导致敌情不明③《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50~51页。。破译敌军电台的密码成为侦察科科长曾希圣所面临的首要难题。1932年5月,总部调来红3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曹祥仁参加侦察台工作。此时,红军侦察台抄收的敌军密电堆集了几大箩筐,行军时用扁担挑着,却一筹莫展。1932年7月,曹祥仁开始参与研究工作,他和曾希圣一起集中精力,猜译密码电报。曾希圣中文底子好,曹祥仁对电码熟悉,二人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对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展密”的部分电报稿反复研究,并结合不断侦收到的“展密”电报和敌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钻研,根据曹祥仁的回忆,于1932年10月将“展密”全本贯通。邹毕兆说:由于破译出“展密”,发展到全部破译出蒋介石及各系军阀的密码,“这样,国民党军队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红军全部掌握了”④《总参谋部回忆史料(1927—1987)》,第56~63页。。这是红色军队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革命性突破,从此确立了红军在信息战中的优势。张震评价:“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破开“展密”之后不久,1932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成立,曾希圣任局长。此时的侦收人员有曹祥仁(兼作破译)、胡立教、王震(与延安时期359旅旅长的王震同名不同人)、李力田、李廉士等,校译人员有李作鹏、卢伟良等。1932年12月,邹毕兆调入总部侦察台,在当班报务之余,积极学习、努力钻研破译技术,入门很快,并成为破译工作的行家里手。到1932年底,二局已破译敌军各类密码20本。在1933年1月的枫山埠战斗和1933 年3月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二局由破译密码电报所获得的情报比其他通过任何手段得来的情报都及时、准确,为红军总部脱离险境并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全面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933年5月,成立中革军委二局(简称后方二局),局长由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简称前方二局)局长曾希圣兼任,副局长为钱壮飞(负责后方二局)、谭震林(不久调走)。曾希圣、曹祥仁仍在前方二局。鉴于破译工作量大,曾希圣对二局进行了体制的调整,将破译工作专门化,成立破译科,曹祥仁任前方二局破译科科长,成为中央红军的首任破译科科长,承担着破译的主要任务。译电校对李作鹏、段连绍、叶楚屏、芦伟良、林茂元、吴元、陈仲山、李云卿;报务胡立教、李廉士、胡备文、李力田、赵宾玉、李建华、叶根、朱谋生。邹毕兆调到后方二局,负责后方二局密码破译工作。
在后方二局组建初期,1933年6月只有钱壮飞、邹毕兆、肖蒲德、邬一之几个人,随后从叶坪侦察台(撤销)调入的钱昌鑫(钱江)也到了。据钱江回忆:他来的时候,在二局的房子里,堂屋用来吃饭活动,堂屋两侧房间,东面钱、邹、邬等办公,钱、邬在里面睡,西面是报房,邹同肖在里面睡。钱江无处安身,住到上楼西侧。不几天由保卫局调来的戴镜元到了,他在东面睡。再往后(约7月)调来严重、王震,继有唐明、刘少宏、贺俊侦等。于是电台另成立科,王震任科长(电台负责人)。译电校对的主要力量是严重和邬一之。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在80多名二三等红星奖章受奖名单中(一等奖章获得者仅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三人),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同时还有默默无闻的红军密码破译三杰:授予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二等红星奖章、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和破译能手邹毕兆三等红星奖章。此时,二局已成功破译敌军密码100余本,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①《总参谋部回忆史料(1927—1987)》,56~63页。。他们在受奖群体中的出现,标志着红军的无线电技术侦察队伍已走向成熟。
邹毕兆在评论二局初创时期的工作时讲:“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抓紧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同志是创造者。曾希圣局长、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邹毕兆自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二局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后专司密码破译,成绩优异,事实证明他也是我军第一代杰出的密码破译专家。曾、曹、邹三个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后来被任弼时称为“密码脑袋”的红二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②王德京:《“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毛泽东1939年为王永浚题词》,《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和红四方面军的破译专家蔡威。
由于二局工作的特殊性质,作为隐蔽战线的战士,曾、曹、邹等人长期默默无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了解他们的功绩。现在,随着老一辈故去,尘封的历史更不为人知晓。而在目前出版的某些有关书籍中,红星奖章获得者、中央红军首任破译科科长、军委二局第二任局长曹祥仁竟被抹去,另一名红星奖章获得者、破译专家邹毕兆也仅是一名小小的报务员。这是有悖史实的。
三、关于破译与译电
2009年1月,林彪集团的最后一名成员李作鹏去世。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自有评论。但有一点很值得商榷,即他在长征中破译密码挽救红军的巨大功劳。当下流传的故事都出自于他当年的辩护律师。据云:李作鹏长征时,任中革军委纵队电台队译电科长,专门负责破译。李作鹏曾说:“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并说:“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李作鹏确是中央红军二局的译电科长,为红军作战作出了贡献,但他并不负责破译。实际上,将译电与破译混为一谈是有违常识的误导。
曾任美国密码协会主席的戴维·卡恩博士,在《破译者》①〔美〕戴维·卡恩著、艺群译:《破译者》,群众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对被称之为孪生科学或互逆科学的破译学与编码学,作了简明的阐述。编码是通过加密使明文(将要加密的信息)不为外人所理解。编码方法属于数学方法,如移位法和代替法。其中的代替法可有无数的演变,如用密表来替代字符。密表之上还可加上乱数,乱数似乎可以无限长,而又不重复。近现代又出现了机械加密和电子加密,以使破译更为困难。破译者则要凭借经验和测试,通过分析、假设、推断和证实(或否定),来剥除编码者的各类加密,还原明文信息。对破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速度,过迟破译的密电,往往失去了情报的时效和价值。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M209密码机,每8个小时就要变换一次密码,使敌方的破译跟不上美军加密的变化。
译电是根据被破译人员已经破解的加密方法(密本),译出密电的明文。打个比喻,破译相当于编辑双语字典,而译电就好比翻译。已经有了字典,进行翻译就好办多了。可见,破译和译电是两种不同的工作。破译与译电在难度上有很大差异,相比破译,译电要容易许多。将译电与破译相提并论是不正确的,故意这样说,更为不妥。
破译者要成功,必须熟知敌以往密码编制规律、报文形式和当前的敌情,并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在江西中革军委二局里工作的曹祥仁和邹毕兆,均是从红军无线电训练班毕业的优秀报务员,对明码本相当熟悉,在报务和对敌台的侦察中,不仅熟记数千字明码,还可迅速译出国民党无线电通信中使用的简单台密和通密。这是他们破译国民党当时以明码电报本为底本的密码,并成为红军第一代破译专家的重要前提条件。
早在江西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中,国民党军的通信加密不断升级,变化频率越来越快,红军破译者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加。邹毕兆说:“我们从蒋介石密码的低级水平开始,就掌握了破译的本领,并且在蒋介石密码的难度不断增大时,能够紧紧抓住,逐步提高我们的破译本领。”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之后,蒋介石的密码大多数已经是自编本,而且变换很快。为此,二局鼓励更多的同志参加破译,希望增加些破译人员。邹毕兆曾动员刘少宏来参加破译。曾局长找1军团首长要人,调来了张树材,可是张树材不肯参加破译,不久又回1军团去了。多年后,已是高级将领的张树材,见到邹毕兆时还谦虚地说,我这个材料,怎么能够搞破译那样的工作呢。还有的同志也曾想搞破译,但始终没有成功,于是又回到了译电科。二局破译核心仍是局长曾希圣和曹祥仁、邹毕兆,他们继续承担着巨大而急迫的工作压力,曹祥仁患肺炎发高烧、邹毕兆打摆子还要坚持工作。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的一年中,他们破译出了300个密码,而且大多数是新的自编本密码,几乎是平均每天破一个密码。
在长征中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英明指挥和军委二局情报工作发挥的突出作用使红军行军作战犹如神助,毛泽东对二局情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两个方面军领导层在进军路线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争议。1935年9月9日,面对张国焘凭借实力胁迫中央的危险形势,毛泽东断然决定,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由于行动仓促、秘密,连身边的一些作战参谋都没有通知。但毛泽东在下决心时即交代叶剑英参谋长,二局一定要带上,并嘱咐叫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走②《曾希圣传》,第103页。。从这段史实中可以看到二局的重要性以及从事破译工作的曾、曹、邹三人在二局的核心作用。当然,这也是二局全体同志的功劳。例如为二局挑运器材的运输员,由于不断有人生病、掉队,在长征途中补充了多达500人。所有参加长征的同志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译电和校译也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在校译过程中,对个别尚未还原的密电电文,校译人员必须边猜边译边验证,将全文贯通,这表明技侦系统的校译与通信译电不尽相同,也与破译却有本质的差别。只有厘清这一基本概念,才能对不同角色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评价。如红二方面军任弼时的夫人陈琮瑛,就曾长时间担任译电员的工作,但她从来没有吹嘘自己是破译能手。又如钱壮飞,利用偷偷抄录下来的密码本译出密电挽救了党的组织,他的功绩在于提供了重大情报而不在于直接破译了密电码。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就是密码编制与密码破译的关系。在破译反破译的斗争中,对立双方都在同时进行着攻防两条战线的努力。据曹祥仁回忆,周恩来在江西时问他,“你觉得我们自己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答,“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布置加强我军自身的通信保密。曹祥仁曾说,破译能力和保密水平相辅相成。一般来说,能破对方的密码,就说明我方密码水平比敌方高,我们的密码大体是安全的。反之,如果对方的密码你破不开,自己的密码就会被对方掌握。二局破译能力的不断进步,也在促进着我军通信保密水平的不断提升①曹冶:《永远的红军》(上),《传记文学》2005年第11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尽管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始终落后于对手,但在技术侦察、情报信息战领域,我军却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我军克敌制胜、最终夺取政权、在全中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我党将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情报“通报给国民党政府”并“迅速反馈给美国政府”等等。如此看来,为中外大众所熟知的重大历史纪录似乎出现了重大缺失,我军创下的“奇迹”竟然被埋没多年。稍稍查询一下就可以发现,对于这段尽人皆知的史实,该报道存在太多无中生有的编造。
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日军突袭珍珠港得手。日军的成功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日军对于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虽然美军在事先已侦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如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监视美军舰队并提供当地天气预报等,但这类情报并不能表明日本即将突袭珍珠港。最明显的可疑动向是,在开战的前一天日方用“紫密”(不是简单的LA密)电告其驻美使馆,准备提交对美最后通牒和销毁密码机。监控日方无线电通信的美军情报部门,在日军突袭发生数小时之前才敢于根据日本驻美使馆的异动,向美最高当局发出日军将要对美开战的警报。由于事前并没有关于日军要突袭珍珠港的确凿情报,美方判断日方军事行动最可能的方向是东南亚和菲律宾,而不是珍珠港。这使得驻珍珠港的美军来不及在突袭发生之前实施最高戒备。
在突袭的准备和行动过程中,日方严格控制无线电通信。1941年11月26日,日海军突击舰队向夏威夷进发时便更换了密码,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与此同时,日海军南进第三特遣舰队的发报量突增,意在用南进掩蔽突袭珍珠港的行动,实际上也确实增强了美方认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将为南进的误判。12月1日午夜,日本舰队更换2万个无线电台呼号,使美军技侦部门一时更加难以确定日军舰船的位置。12 月2日黄昏,突击舰队到达预定集结地,旗舰仅发出暗语电报:“攀登新高峰”,通知部队做好进攻准备。12月7日(美国时间)日军向珍珠港投下第一波炸弹后,同样也仅发出极为简
四、关于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情报
2009年6月19日,某报惊爆秘闻:中共传奇人物“破译日军密电助美击毙山本五十六”,单的暗语“虎!虎!虎!”报告偷袭成功。几十年来,可以接触密档的军事专家和历史学者不断对珍珠港事件进行研究,所有权威研究成果都表明,这次经过周密策划的袭击,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军方都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单位发出过明示袭击珍珠港的密码电报。美国史学家评论,日本用外交谈判和向南进军掩护对珍珠港的突袭,“突袭计划包藏在全密封的通信保密之中,致使没有一丝音响散布到电波中去”。这使得始终监控着日方无线电通信的美军也无从判断日本海军在战争初始就敢于对珍珠港实施大规模突袭。日军突袭珍珠港的密电从来就不存在,中共方面破译了日军要袭击珍珠港的密电是从何而来?
五、关于使山本五十六被击落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美二国的编码与破译能力最强,已为世界公认。1942年以后,美国军方全面掌握了日本的外交及军事密码。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空军击落,就是美军根据破译日海军的JN-25密电,得悉军令部拍发的山本巡察的详尽路线和以分钟计算的时间表而成功实施的设伏行动①吴明冰:《还原历史真相——美日中途岛战役和击毙山本五十六战斗中的密码情报战》,《舰船知识》2009年第10期。。某报报道中共方面某传奇人物破开了日方密码,并通过国民党方面转告美方,方使山本被美空军击落,云云,这种说法不知是从何谈起。
抗战时期,由于正面承受对日作战的压力大,国民党在开展对日无线电侦察工作方面,比中共起步早、能力强。池步洲等破译人员也具有一定水平,并获得实际成果,掌握了日方较为简单的LA外交密码。据池步洲讲,他所在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从破译的LA密电中掌握了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前的一些动向,并根据中日交战中的历史经验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且向美方作了通报,但没有得到美军方面的重视;军技室也从破译的日本外务省拍发的密电中侦悉山本五十六的行动计划,国民党也据此向美方作了通报。但国民党始终没有破译出密级更高的日本外交高级密“紫密”,更未破出日本陆军密和海军密。②池步洲:《我在抗日战争中侦破日本密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6卷第13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年,第38~77页。相对于当时已经掌握了用 IBM制表机自动剥除乱数的美国军方的技术能力而言,无论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是远远落后的。
共产党方面,红军到达陕北后,二局即开始进行对侵华日军的侦察,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所有侦收、破译、校译人员都必须学会日文。为此,从1936年6月开始,二局举办了数次日文学习班。1938年夏,曾希圣带邹毕兆等专程到武汉收集日本方面有关资料,并经李克农的精心安排,得到国民党破译人员杨肆秘密向我方提供相关资料。1938年冬,为了获取日军情况,曹祥仁带王进并同已是115师侦察科长的李作鹏等到山西交城一带对日军进行抵近侦察。1938年9月建立对日工作科,首任科长邹毕兆,是研究日军密码的主力,戴镜元为副科长。日本留学归来的屠廷容,日文能力强,成为工作中的技术骨干。随后又有一批奔赴延安抗日的青年学生经日文培训后进入工作。到1939年,日本方向的工作有了进展,并得到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表彰。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整体日文能力和技术力量薄弱,二局在对日无线电技术侦察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有效的成果记录在案。
同样,该报报道中所谓黄土岭战斗击毙阿部规秀的技侦情报,也是子虚乌有。姑且不说故事的真实性,过程也极不合理。无线电技术侦察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二局创建初期就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良好的分工体系,侦收——破译——译电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当时在安塞的二局,局部和破译、校译整编部门在碟子沟,侦收部门在黄崖根,二地相距数里。该报报道的所谓一人同时“负责对敌人的侦听和破译工作”,又将所获情报直接向千里之外的作战部队通报,这既不符合规定,也不可能。中共情报机构自20年代的特科起,一直有着极为严格的制度和规则。当时的军委二局根本没有直接向战区通报情况的任务和权力。
六、关于德军闪击苏联的情报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袭。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向斯大林提供了可靠情报。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利用其国民党上层的身份从国民党内部得知了这一信息。为此,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颁发了《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①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由于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为阎宝航诞辰100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的公开披露,特别是近年来中共安全部门对新中国成立前的许多秘密工作情况已经解密并大力宣传,这段历史内幕已广为人知。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共军委二局也在当时获得了这一事件的准确情报。
原二局老同志康立泽回忆,1941年夏,我们截获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获悉‘德军将于6 月22日进攻苏联,望注意核查’电文当即报告中央军委,中共中央迅速通报苏联,斯大林为此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②康立泽:《回首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73页。。
事实上,二局到延安后,组织了若干期破译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密码破译专门人才;二局局长曹祥仁建立研究室,撰写《密码学总论》,将经验总结提升至理论,同时进行高级密码破译研究③曹冶:《永远的红军》(上),《传记文学》2005年第11期。;密码破译专家王永浚在密本加表密码的破译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④王德京:《“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毛泽东1939年为王永浚题词》,《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4期。。对上述情报的侦破,二局的一些老同志有更为详细的回忆。当时二局对于这一方向的密码于1941年3月成功突破,破译员为陈松录。此后连续收到数份有关德军行动的战略情报,直至收到最后这份报告准确进攻时间的密报。据当事的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校译组长白枫(余湛)第一个拿到报后,感觉事关重大,又难辨真伪,马上和主管负责人彭富九一起找到局长曹祥仁。曹祥仁说:这事太重大!不管怎么样,马上报!曹祥仁立即骑上马,亲自赴延安汇报。还有老同志记得,事发一段时间后,许光达陪同当时苏联驻延安的联络组负责人专程来到二局驻地碟子沟,正式转达苏方对二局的感谢。
据了解,潘汉年也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这一情报。由此可以推断,中共向苏共提供的情报是综合了各渠道发来的密报的。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莎”计划于1940年12月完成,英国首相丘吉尔及美国总统罗斯福都根据他们得到的情报向斯大林发出过警告。1941年5月,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为当年6月22日。苏联通过许多渠道获得了这一情报,如在日本工作的著名苏联谍报英雄佐尔格报告了德军发动进攻的大体时间,苏联在瑞士工作的谍报员道拉更获得反纳粹的德国高级军官送来的准确进攻日期,并报告莫斯科。苏军部队侦察也提供了关于德军的大规模调动的情报。由于苏联最高当局对战略形势有一定的误判及其外交策略考虑,导致苏军事前未能做好充分准备,吃了大亏。
总之,隐蔽战线的历史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许多当事的老同志已带着秘密离去,给这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因此更要以严肃、客观的态度、怀着对他们的尊重去探究,尽可能完整地、全面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本文作者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教授北京 100088)
(责任编辑 薛 承)
A Probe into Some Problem s Concern ing the CPC’s History of Radio Intelligence
Wu Xing
K26;D231
A
1003-3815(2010)-01-05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