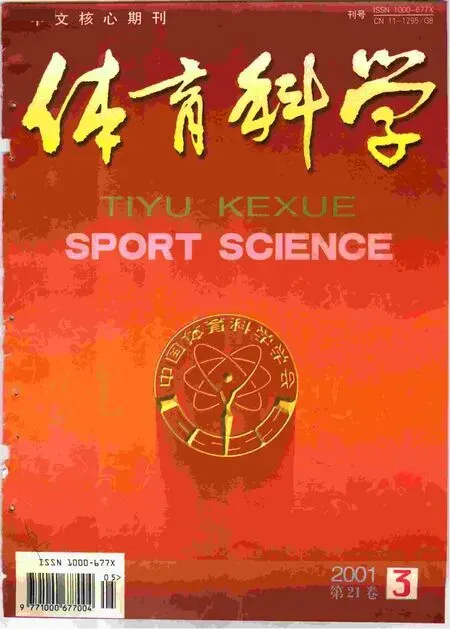身体的谱系
——基于西方哲学的构建
马德浩
身体的谱系
——基于西方哲学的构建
马德浩
身体是体育的载体和基础,身体谱系的建立可以为体育的价值定位提供依据。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追溯从古希腊到当代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哲学对身体定位的变化,并以这种变化为线索,建构身体的谱系。从身体的谱系中得出:身体与灵魂共同形成了人,身体是灵魂的载体,是人类第一位的存在,而灵魂则是身体的动力,是人成为人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将身体与灵魂协调起来,达到一种平衡,而体育则是促进这种平衡的有效实践。
身体;谱系;体育;哲学
哲学反映着时代,并影响着时代,而当今哲学又以西方哲学在全世界的影响最为广泛。那么,西方哲学是怎样定位身体的呢?这种定位的变化过程其实就是身体谱系的建构过程。又由于身体是体育的载体和基础,所以,对身体谱系的建构其实也是对体育谱系的建构。首先进行一下概念的界定,所谓谱系是泛指事物发展变化的系统[24],本研究中的身体谱系是指不同时期的哲学对身体定位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把理性和灵魂理解为同源,认为它们都是通过逻辑的思考形成的,与此同时,把感性和身体作为它们的对立面来对待,认为它们是除去逻辑思考以外的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人的情感、肉体等。此外,在本研究中,西方哲学是指欧美哲学,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为目的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1 身体谱系的建构
1.1 身体的转向
西方哲学是以古希腊哲学为起点的,而古希腊哲学又以古希腊神话为母体。德国哲学史家策勒尔将希腊哲学分为3个时期: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苏格拉底至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哲学,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4]。由于本文要建立的身体谱系以西方哲学的身体观为线索,所以,本文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构建。
1.1.1 荷马的吟唱
在希腊的伊奥岛上,有一座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一张神圣的嘴被黄土淹没了,那是诗人荷马,古代英雄们的整理者。而柏拉图更是用一句“荷马教育了整个希腊”把荷马推向了荣誉的巅峰。马克思也把荷马史诗视为整个欧洲文学的源头。那么,荷马史诗是怎样的史诗呢?它又怎样看待身体呢?
与所有处在人类童年时代的古老民族一样,古希腊人想象力旺盛而推理能力薄弱,他们往往只会凭借个别具体人物来表现共性,正如维柯所言:希腊人把英雄所拥有的一切勇敢以及由这种勇敢所产生的一切情感和习俗都归于阿基琉斯一人身上[19]。荷马正是根据希腊人的这一特点创造出各种“诗性人物”(即英雄)的性格。在荷马的史诗中,英雄的形象都是“高大”、“魁伟”、“英俊”的,他们力大无比,英勇善战,敢作敢为[20]。荷马对英雄的颂扬也促使希腊人崇拜身体和征服。于是希腊人开始想办法使自己的身体强健,他们想出了什么办法呢?答案是体育,希腊人通过跑步和角力使自己的身体强健。为此,他们还创造性地举办了奥运会,并以此为战场,来实现自己对力量的追求,来表现他们对身体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可以停止战争,因为,希腊各城邦约定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停止一切战争。荷马对英雄的颂扬以及对身体的吟唱影响了整个希腊文化,这种影响也促使那些古希腊的先哲们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世界的本源呢?到底什么才是人类所要追求的?
1.1.2 毕达哥拉斯的数
希腊人的哲学是用神学和“格言的道德”的形式将它自己从宗教中分离出来的[1]。当古希腊哲学的先驱们将荷马史诗中的神送到寓言的领域,并用原则和原因等名称来解释自然的时候,哲学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哲学产生于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之中。
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往往把目光倾向于自然,他们兴致盎然地追问世界的本源。在这些哲学家中,毕达哥拉斯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作为一个宗教的先知与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影响了苏格拉底和以后的整个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
毕达哥拉斯认为,事物是由数构成的,数的原则就是所有事物的原则。那么,毕达哥拉斯为什么会认为数是万物的起源呢?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兴趣始于宗教。他同所有的哲学家一样非常关注人的净化和不朽的问题,因为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神,他们和人一样地不道德,相互之间嫉妒和诋毁。因此,他们既不能成为崇拜的对象,也不能克服无处不在的道德的不洁净感,更为重要的是,毕达哥拉斯认为,他无法在诸神那里获得生命不朽的慰藉。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他转向了数学,并在数学中发现了比生活更纯粹的永恒,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其实,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一种基于逻辑的思维游戏,他在这种游戏中摆脱了生命虚无的痛苦,而这也是毕达哥拉斯诋毁身体存在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异乡人,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然而,我们决不可以自杀以求逃避,因为,我们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们的牧人,没有他的命令我们就没权利逃避。在现世生活里有3种人,正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3种人一样,即那些来做买卖的人属于最低的一等,比他们高一等的是那些来竞赛的人,最高的一种乃是那些只是来观看的人们。因此,一切中最伟大的净化便是无所为而为的科学,惟有献身于这种事业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学家,才真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从毕达哥拉斯的言语中可以看出,此时他已经不再聆听荷马的吟唱了,而是专注于他的数学,而这也意味着他将对身体的崇拜转化为对身体的歧视,这种转向深深影响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1.1.3 柏拉图的洞喻
如果说苏格拉底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关注的是自然的话,那么,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主题开始转向人自身[17]。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我们对他的了解更多是通过他的学生的记叙,苏格拉底有2个学生很有哲学禀赋,一个是色诺芬,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柏拉图。由于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广泛,因此,笔者以柏拉图的身体观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毕竟整个西方文明史其实就是柏拉图的注释史。
柏拉图在其《斐多篇》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一段自白:“心灵应当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心灵使万物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我担心,由于用肉眼观察对象,试图借助感官去理解它,这可能使我们的灵魂变瞎”[3]。柏拉图顺着苏格拉底的怀疑,把身体比喻成了一个洞,而我们的灵魂就被囚禁在这个洞里,使灵魂失去了自由。他甚至不再满足于这种委婉的比喻,而直接说:“肉体在所有的地方设置了障碍,扰乱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混乱,吃惊,其结果是肉体使我们看不到事物的本真。如果想纯粹地看事物,必须离开肉体,根据灵魂,关照事物”[3]。从柏拉图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肉体干扰了灵魂,使灵魂无法认识真理,所以,他认为只要灵魂拒绝肉体的协助,从肉体中独立出来,就可以摒弃附着在灵魂上的肉体的诸恶,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永生。苏格拉底的死更使柏拉图坚信灵魂可以摆脱肉体而永存,他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学习死亡,一直在练习死亡,而死亡意味着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拉底是幸运的”[3]。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不管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受到了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肉体干扰甚至束缚了灵魂,因此,主张摆脱肉体的束缚。如果说身体与灵魂的分离在毕达哥拉斯那里仅仅是初露雏形的话,那么,在柏拉图这里,这种分离已成为无法调和的灾难。
1.1.4 奥古斯丁的上帝
当柏拉图论及创世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由上帝赋予形象的原始物质,而亚里士多德也有如此的看法。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者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或建筑师。他们认为,物质实体是永远的而不是被造的,只有形象才出于上帝的意志。与此见解相反,奥古斯丁像所有正统的基督教徒所必须主张的那样,主张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
奥古斯丁把柏拉图置于所有哲学家之上。他认为一切哲学家都该让位于柏拉图:“让泰勒斯和他的水一道去吧,让阿那克西美尼和空气一道去吧,让斯多葛学派和火一道去吧,让伊壁鸠鲁和他的原子一道去吧。”他还以柏拉图为参照,重新审视了《圣经》,结果发现,《圣经》与柏拉图的哲学是和谐一致的,甚至还超越了柏拉图。于是他把自己神学的触角伸向了基督教教义。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言:受柏拉图影响的奥古斯丁,发现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相符时,他便将二者结合起来,同时,修正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形成了他的神学,并且,被基督教奉为最重要的思想
家[17]。
在奥古斯丁的神学里,上帝是整个存在的源泉,是永恒的造物者,也代表着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人是负罪的,这种罪恶来自于身体的欲望,由于人是罪恶的,所以,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只有对自己进行惩罚,来赎还自己的罪过,人才能被上帝所接纳,才能进入幸福的天堂。这种救赎的方式便是弃绝物质的享受,克制欲望,实行斋戒,进行忏悔,出家修行[5]。
奥古斯丁的哲学再次使人远离了自己而走向了上帝,这种思想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而奥古斯丁所主张的禁欲主义无疑把身体推向了苦难的深渊。于是,落落寡欢的修道院,身体羸弱的修道士成为了历史上最为可笑的风景,黑暗的中世纪拉开了它漫长的帷幕。
1.2 苦难的反抗
奥古斯丁垂死时,西罗马帝国走进了其死亡的坟墓。北方的蛮族,从诸多方向侵入边境。高卢与西班牙被征服了,意大利也受到了威吓。迄后,罗马覆亡,整个希腊罗马文明陷入绝境。在这场灾难中,只有教会幸存了下来,并主宰了人们的生活。在教会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被逼上了绝境,同时,人的身体也被逼上了绝境。人们沉浸在教会死板的教义里,压抑着身体的欲望,人们在黑暗中隐忍着,放逐着。但是,仍有那么一些勇敢的人在教会黑暗的统治下,进行着反抗。虽然这些人的身上仍带有严重的宗教气息,但是他们已经带着哲学的种子上路了。
1.2.1 阿奎那的曙光
安东尼·肯尼把阿奎那视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位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那么,阿奎那为什么能够受到如此崇高的赞誉呢?他又是怎样看待灵魂与身体的关系的呢?
阿奎那通常不仅被看作是第一个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人,并且也被看作是第一个试图表明上帝具有不同属性的人。在奥古斯丁和基督教那里,上帝是一种抽象出来的理念,他并不具有什么属性。但是阿奎那却认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来源于对世界中事物的认识,以及源自于在肯定上帝非世界中某种事物的前提下,我们对上帝的有意义地加以否定或肯定[23]。阿奎那想通过这表达什么呢?在奥古斯丁和基督教那里,上帝被定义为善良、完美、仁慈的形象,而把人定义为邪恶、充满欲望的形象。阿奎那认为,这种定义其实来自于他们的认识和想象,而非上帝本身就是那样。也就是说,在阿奎那这里,基督教的上帝是被基督教杜撰出的,正如我们对某个人的定义一样,具有不准确性。阿奎那认为,上帝是一种“自在之物”,是永恒的存在,而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他认为奥古斯丁和基督教对上帝的定义是主观的,存在错误的,是值得怀疑甚至是否定的。阿奎那这种观点的意义在于:那种把人定义为邪恶并因此被上帝所遗弃的观点是可疑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就为人类的翻身创造了可能,而人也可以摆脱禁欲主义的折磨。阿奎那同样否认了上帝是某种必须创造的存在者,按照他的观点,上帝的创造是完全自然的,正如肾脏排尿一样[23]。因此,上帝也不是因为原罪,要惩罚人类,上帝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一种能在“幕后推动事物前进的看不见的力量”。正如赫伯特·麦克凯比所解释的:对于阿奎那而言,上帝并不干涉被造的自由存在者,也不会以一种剥夺其自由的形式强迫其行动,他并不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使他们获得自由[23]。在这里,阿奎那和基督教分道扬镳了,他认为,上帝并不想强迫人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也不想干涉其自由。这显然与基督教所大力倡导的禁欲主义和自我救赎截然相反,他其实在宣称:是你们而不是上帝,认为我们犯了错,这就为人类寻求自由打开了一个通道,同时也为身体的解放提供了依据。
阿奎那为身体解开了沉重的十字架,那么,他又是怎样看待身体和灵魂的关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和柏拉图是有区别的。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认为,灵魂并非像形式与质料一样和身体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像驾驭者和其被驾驭物一样,他认为灵魂之于身体中“犹如水手之于船上”。而阿奎那则认为,如果灵魂推动我们的身体犹如水手操动船只的话,那么,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并没有合为一体,如果我们的本质是灵魂,那我们就是非物质的,然而,这显然不合事实。阿奎那认为,我们是感性和自然的实在[23]。他同样也承认灵魂的存在,并认为灵魂是我们成为我们的关键,也就是说,单纯的肉体不能成为人,必须是拥有灵魂的肉体才是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奎那承认了灵魂和肉体的统一,这是对柏拉图所倡导的灵肉分离的一种修正,这使得身体从灵魂的对立面上走了下来,成为灵魂必须的战友。但是,他也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可以永存的思想,认为灵魂一定可以免于和肉体一起死亡的灾难,而获得永存。在阿奎那的哲学体系中的灵魂和肉体是一体的,二者是统一的,灵魂是身体的统帅,是身体的支配者。可以说,在那黑暗的中世纪,阿奎那的哲学无疑像一道曙光,划破了黑暗,带来了光明。
1.2.2 皮特拉克的复兴
对于中世纪的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天宇低垂,暗示着天国和人世的密切结合,也就是哲学与神学的集合。在这个时期,哲学实际上只是神学的婢女,它仅仅是为神学的各种教条提供一种由推理得出的说明。但是,这种哲学与神学的结合是不牢靠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上存在多个神,而在基督教眼里,上帝是惟一的神。阿奎那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基督化,来调和这种矛盾。而哲学却在为宗教提供一种理智的依据时使其自身受到了压制。在中世纪末期,奥卡姆的“剃刀”把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这种尴尬的结合戳了个洞,而皮特拉克却试图结束这种尴尬,使哲学独立出来[15]。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如阿奎那,司格脱等)关注的是神学,关注的是教义的合理性。而皮特拉克则将这种关注转移到了哲学与艺术上来。他认为,古希腊的哲学并不仅仅是对神的崇拜,更多的是对生命的思考,对自然的追问。他认为,教会利用了哲学,把哲学当其宣传的机器,而这种利用是对哲学使命的歪曲。因此,皮特拉克要求人们重新品读古希腊的哲学,并恢复哲学独立思考的本质特性,摆脱教会的束缚。就这样,他开始了对欧洲的再教育,这种教育不是从宣扬禁欲主义的教义出发,而是从人自身出发,寻找古希腊的文明。在这种教育的号召下,大批的学者开始搜寻和阅读古代的原稿,一场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开始了。
从但丁的诗歌到塞万提斯的小说,从达芬奇的绘画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塑,我们随处可见具有古希腊风格的艺术作品。这场文艺的复兴同时也是身体的复兴,在达芬奇的画里,人们脱掉了丑陋的道袍,把美丽的身体再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欣赏着维纳斯美丽的身体,推崇着大卫强健的肌肉,甚至连上帝和天使也是那么的富有力量。灵魂与肉体获得了平衡,而这种平衡也使人摆脱了教会的压抑。
1.2.3 马丁·路德的改革
只有当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进入神学领域,就个人而言,就是进入修道士马丁·路德的思想的时候,欧洲才爆发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反抗罗马教会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将古典文化和基督教融为一体,文化上自由的包容主义表现在教会接受了希腊的异教文化。马丁·路德正是在这种相对的自由中,把自己改革的利剑指向了已经腐朽的宗教。
马丁·路德认为,教皇和教会并不是神灵,也没有权利规定基督教的教义,他认为,宗教的权威最终而且也只能建立在基督教教徒身上,认为基督教教徒可以通过自己的良心,通过自己对上帝的忠诚来阅读和解释《圣经》,而教会和教皇无权干涉教徒的这种自由[10]。马丁·路德的这一主张其实就把教会和教皇推到了可有可无的位置。因为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良心和忠诚理解上帝,那么教会的那些教义就失去了价值,而作为对教徒进行教育的教会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其实促进了宗教的世俗化,人们纷纷离开教会,过上了世俗化的生活,只要他皈依于上帝即可获得上帝的爱。在这方面,马丁·路德更是身先士卒,娶了个修女为妻,并与其组建了家庭。宗教的世俗化把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也从古板的教义解放出来,同时也把身体从禁欲主义的监狱中解放了出来。人们获得了理解上帝的自由,获得了独立思考的自由,获得了关注身体的自由。人们开始摆脱禁欲主义,摆脱对身体的仇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1.2.4 弗朗西斯·培根的力量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人重新把目光放在了人和自然身上。哲学也渐渐地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开始为科学提供理念的支持,这种转变是从弗朗西斯·培根开始的。
在意大利的伽利略进行新的科学实践的时候,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里,自然哲学将承担起与精神进步相伴随的肉体的拯救。在培根看来,新大陆的发现相应地也要求新的精神世界的发现。在这个新的精神世界里,陈旧的思维,传统的偏见以及普遍存在的理智的蒙蔽将通过获取知识的新方法来克服。人们可以借助此方法得出控制自然所需的知识,这种知识可以帮助人类重新确立由于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对于自然的统治。在苏格拉底眼中,知识是一种美德,而在培根这里,知识是一种力量。他认为科学担当了与上帝的精神救赎相对应的角色——对肉体的救赎[10]。弗朗西斯·培根将哲学的关注从宗教转向了科学。而我们的身体也不再羞答答地躲在宗教和哲学的身后,它进入了科学家的视野。其实在培根宣布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比利时伟大的医生安德烈·维萨里已经开始对身体进行研究,并创立了解剖学。与培根同时代的威廉·哈维则创建了生理学。这些都为对身体的研究打下了基石,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的健康,对身体进行了拯救。而我们的体育科学也正是沿着这条线索而不断展开的。
1.3 理性的崇拜
弗朗西斯·培根把哲学的目光由宗教转向了科学,并赋予科学以哲学的使命:帮助人类确立了由于亚当的堕落而失去的对自然的统治。这种转向深深影响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思想,他们对理性的崇拜使得整个17世纪充满了数学的味道,而身体再一次被丢在了一边。
1.3.1 笛卡尔的怀疑
以蒙田为代表的法国怀疑派哲学家们对世界的怀疑,影响了同在法国的笛卡尔。这种影响使笛卡尔至死都在怀疑是否真的认识了自己。他在自己死前便选好了一句箴言:死对人来说并无伤害,除非此人虽名震寰宇,却尚未开始认识自己[2]。
笛卡尔的怀疑是从对一切的怀疑开始的,他认为,只有这种纯粹的怀疑才可以保证自己哲学的真实。正如阿基米德只要求拥有一个不动点,以推动地球离开其轨道一样,笛卡尔也在寻求他的支点。笛卡尔从怀疑自己的身体出发,到怀疑上帝的存在,甚至最后怀疑自己是否还醒着,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怀疑,思考了一个纯粹的问题:什么能让我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呢?笛卡尔认为,只有他的思维能说明他的存在,也只因为他在思考,所以他才存在。笛卡尔正是从这个他认为惟一能证明其存在的思维出发,建构了他的哲学体系。
笛卡尔认为,人的身体的许多活动就像动物的活动一样是机械的,他认为,人的身体的运动不可能来自灵魂,而灵魂也只能影响或改变身体的某些因素的运动方向。因此,他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而且,确信灵魂可以离开身体而独立地进行思想,并通过思想获得永生。我们可以看出,在笛卡尔这里,灵魂与身体再次分离了,再次回归到了柏拉图的二元论。只是有一点是令人稍感欣慰的:柏拉图认为,身体干扰了灵魂,并要求敌视身体,以保证灵魂的纯洁,而笛卡尔则认为身体无法干扰灵魂,身体只是一台机器,也无所谓敌视了。然而,我们的这位忽视身体存在的天才的身体太糟糕了,他只在这世界上存在了54年。而那个敌视身体的柏拉图则活了80多岁。如果笛卡尔能活到柏拉图那个年纪,他又会迸发出多少伟大的思想,而人类的文明又会获得怎么样的进步呢?然而,历史无法回到过去,我们只能从中汲取教训: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何谈灵魂?而体育的价值就在于保持身体的健康,从而保证人拥有思考的能力和时间。无须赘言了,还是看看另一个更为短命的理性主义者吧。
1.3.2 斯宾诺莎的透镜
笛卡尔对理性的崇拜使远在荷兰的斯宾诺莎开始了其被当时社会视为异教思想的哲学远征,而这位具有伟大的哲学德行的思想家也开始了他短暂而又孤独的命运。由于他不愿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而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堂驱逐出境,他的一生都在过着简朴的生活,他通过磨透镜来维持生计,而这个磨透镜的职业也使其患上了肺结核,并在1667年走完了他45年的短暂人生。在纪念斯宾诺莎诞辰200周年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捐助使其纪念碑屹立在了欧洲的大地上,杜兰特说:“从来没有哪个哲学家的纪念碑建立在如此广泛的爱的底座上”[18]。
斯宾诺莎并不仅仅是单纯地继承了笛卡尔的思想,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不可能被世人奉为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灵魂和身体是分离的,而且,灵魂能够影响身体的某些行为,但是,身体却无法影响灵魂的思考。而斯宾诺莎则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没有脱离身体的灵魂,也没有抛弃灵魂的身体,二者是同一的,在对待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上,斯宾诺莎回归到了阿奎那的一元论上。斯宾诺莎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从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灵魂与身体的关系。他将激情理解为同生理状态相应的混乱的和不适当的观念,属于人的精神的被动方面,而理智则使人从这种混乱中摆脱出来,走向有序[7]。他同时认为,激情本身不是人类的错误,而是人类所必须的性质。其实,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激情来源于肉体,来源于人的感觉和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激情是身体的代表,而理智则是灵魂的信徒。也就是说,斯宾诺莎认为灵魂离不开身体,灵魂是身体的观念,是身体中升华出的一种使人从无序状态走向有序状态的力量,这就与笛卡尔划开了界限。但是,斯宾诺莎认为,身体是被动的,是无序的,它需要理性的力量来驯服它。而这其实是对理性的崇拜,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并没有走出笛卡尔的怪圈。
1.4 理性的批判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上,这种理性的崇拜也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对自身感觉的忽略。人们沉浸在复杂的科学研究中,忘记了对生命的思考,甚至忘记了哲学。很多哲学家成了数学家,比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首先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崇拜所带来的人的地位的下降,而卢梭更是沿着伏尔泰的这种忧虑进行了呐喊,试图使人们重新回归自我,康德则将这种呐喊转化成一种更有力的批判。
1.4.1 卢梭的呐喊
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期间,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开始重新反思笛卡尔所主导的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他认识到这种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科学的崇拜,使人忘却了人自身的存在。然而,伏尔泰却过多地陷入政治的漩涡,而没有将这种认识上升为一种体系。卢梭接过了伏尔泰的衣钵,对这种理性的崇拜进行了讥讽并主张人们从对理性的关注转向对心灵与感情的熏陶[22]。
康德在其《论种类的特性》中这样写道:卢梭的3篇论缺陷的文章,第一篇是谈由于人的力量的软弱而使人类摆脱了自然走进了文化,第二篇是谈由于不平等和相互压迫而让人文明化,第三篇是谈因为反自然的教育和思维方式的畸形形成了所谓的道德化[21]。从康德对卢梭思想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的哲学脉络。卢梭认为,由于人的力量相对软弱,为了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生存下来,人必须要相互之间进行合作。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固定下来呢?答案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形成一个团体,这种团体必然要拥有约束其成员的道德上或形式上的条例,这种条例的建立使人摆脱了自然,走向了文化。然而,任何一个团体要想保持其持久性和凝聚力必然需要一个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产生其实就伴随着不平等和相互压迫而产生,正如狼群的首领是通过其强壮的身体和勇猛的撕咬而成为狼王的。领导者的意愿是团体成员所要遵循的,领导者要想维护其在团体中的权威,需要什么呢?很简单,需要自己的军队,用这种暴力的形式去镇压其他成员的反抗,而伴随着团体的扩大,活动范围的增加,国家便产生了,国家的产生意味着人走进了文明化。而国家要想维护其统治仅仅靠暴力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思想上的统治工具对人的野蛮性和自由性进行弱化。教育和哲学显然是最为理想的工具,它们可以帮助统治者对其国民进行思想上的麻醉,这种麻醉使人失去了反抗性,失去了自由,走进了道德化的社会。卢梭其实是追溯了人类一步步走向奴役,背离自然的历史。因此,他说:“思考与哲学使人类远离了自然,使人类退化了,我们同胞的那些著作欺骗了我们,而大自然却永远不会欺骗我们,我们应回到大自然里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14]。
卢梭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指向笛卡尔,更指向了柏拉图。他认为,在柏拉图那里,哲学便把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打破了,从此,人的感性便一直被遗弃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这种遗弃使人类远离了自然,远离了人类原始的存在状态,从而走进了受理性和制度压抑的文明时代。因此,卢梭主张人类应关注自身的感性,关注自己的身体,回归自然。他在《爱弥儿》中抱怨:“虚弱的身体使精神也跟着虚弱,而体育是对抗这种虚弱的一剂良药”。在卢梭这里,身体与灵魂站在了同一个位置上,他们共同构成了人。可以说,卢梭的这种呐喊不仅影响了康德还影响了尼采。
1.4.2 康德的拯救
1762年夏末,对于康德而言是十分有意义的,他阅读了卢梭的《爱弥儿》,并沉浸于其中,甚至因此暂停了每天到菩提树下散步的习惯。康德发现,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一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想走出无神论的黑暗。他在卢梭的启示下就感觉论问题进行了大胆断言,认为感情优于纯粹的理性。康德将休谟的观点与卢梭的感情联结在一起,从理性中拯救宗教,同时又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这就是康德的使命[18]。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理性张开它的双翼,单凭思辨的力量来超出于感官世界之上,是徒然的,理性无论是按照经验性的途径还是按照先验性的途径,都不会有什么建树[15]。在康德眼中,理性并非是万能,也不可能脱离感官而认识世界。他认为,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然后,通过心灵的感知而获得知觉,并以此认知事物。而且康德还认为,这种由感觉出发,经过加工后的知觉组成的对事物的认识是不真实的。正如我们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事物时,会受到这个眼镜的干扰一样,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也带着一副有色眼镜,这个有色眼镜就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先验。也就是说,在康德这里,世界是无法被人准确理解的,但是,他又承认世界是存在的。康德承认了身体的重要性,甚至把感觉看做认识世界的第一步,而且,他也反对过度地崇拜理性,他试图使身体与灵魂达到某种平衡,这也是他在卢梭那里继承的思想。但是,康德没有像卢梭那样把身体至于同理性相平等的位置上,他认为,人最终还是要通过灵魂来完成对世界的判断。康德本人是个极其重视身体健康的人,他有着很严谨的作息时间,终生坚持着散步的习惯,这也使他活到了近80岁的高龄,这在哲学家中已经算是很稀少的寿星了。他的长寿和健康也使他终生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从而创造了很多名震寰宇的巨著。
1.5 唯心与唯物之间
康德影响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者,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但是都始终未摆脱掉在康德那里所浸染的浓厚的唯心主义气息。而同样受康德影响的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则从康德的唯心主义中走了出来。
1.5.1 黑格尔的精神
黑格尔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以出色的、体系化的彻底性完成了康德宣称的不可能被完成的东西。康德认为,人的心理是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认识的,而黑格尔则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实在的,凡是实在的都是合理的”,并由此得出,一切都是可知的。在这里,黑格尔其实背离了康德的哲学,因为在康德看来,心灵仅仅使认识成为可能,仍需要身体感官的介入。在黑格尔眼里,认识本身就是精神的,它无需身体的介入[15]。
黑格尔并没有把身体至于精神的对立面,但也未像康德那样承认身体在认识中的必需性,他更愿把身体看成一种理念,这种理念是实在的,但又是如此单调,以至于黑格尔很少关注它的存在,这一点与笛卡尔相似,身体再一次被推向了毫不相干的位置。
1.5.2 马克思的调和
黑格尔把特定时代的思想和行为看作是精神在所有人中的作用,而与其同时代的费尔巴哈则认为,形成人的思想的影响力来自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的总和,一切关于上帝的所谓知识只不过是关于人的知识而已,也就是说,上帝就是人性[15]。
费尔巴哈把哲学的焦点由上帝转移到人身上,在费尔巴哈的的哲学体系中,物质是第一位的,身体是精神的基础,是第一位的存在。我们写道这里应该感到激动,毕竟这是从毕达哥拉斯以来,身体在西方哲学的关注上第一次超越灵魂,占据了第一的位置。但是,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否定了灵魂的作用,否定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他把人看成了一种被动存在的动物。
当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时,他从对黑格尔的迷恋中醒来。他巧妙地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中,这就克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机械性,使其充满了活力。马克思认为,人不应该被看作抽象的东西,而应该被看作有思想的能动的生物来看,但它首先是个生物[9]。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将感性与理性较好地柔和在一起,首先是个生物即承认身体的第一性,把人看成是有思想的能动的生物其实是承认了理性在人认识世界时的能动作用。这就把身体与灵魂放在了合理的位置上,在这点上,马克思走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前面。
1.6 身体的正名
马克思虽然把身体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但他并没有把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来研究,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社会学领域。与他同时代的尼采则用其疯狂的权力意志将身体推向了哲学的高峰。在尼采之后,德勒兹、梅洛·庞蒂以及福柯都将身体作为了其哲学的研究中心。身体也从哲学的幕布后面走向了前台,开始了其被人遗忘的美丽表演。
1.6.1 尼采的权力意志
什么是权力意志?尼采的解释是: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13]。尼采有时也用生命意志来代替权力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把生命的本能理解为权力意志。那么,权力意志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尼采说:“我已将权力意志的假说从生命扩展到整个存在,用以解释存在的总体特征,我认为权力意志是一切变化的终极原因和特征。我必须将权力意志这个出发点作为行动的本原”[12]。从尼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权力意志的本质就是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又寄附于人的身体内,也就是说,权力意志首先是一种身体的本能。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一切价值的评估标准,他甚至用宣布上帝的死亡来确立权力意志作为立法者和立法标准的地位,这样,尼采就建立了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我们的疑问在于:权力意志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尼采的回答是:“首先,感觉——各种各样的感觉都应当被认为是意志的组成部分;其次,还应当承认思想,思想和感觉是不能分开的;最后,意志不仅是感觉和思想的复合体,最重要的是一种激情”[16]。而这种最重要的激情又是什么呢?它是身体,用德勒兹的话讲就是:权力意志就是身体,是激情,是饱满的肌肉感,是运动生成和作用的根源。
身体在尼采这里得到了正名,身体再次超越了理性。而这种超越不是费尔巴哈那样的把理性排除在外,而是把理性柔和进来的对身体的崇拜。在尼采的哲学体系中,身体成为了价值评估的标准,而这也是哲学史上的第一次,身体在尼采这里得到了最高的礼赞。
1.6.2 德勒兹的欲望
德勒兹曾自夸是尼采的信徒,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德勒兹把权力意志抽象成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是积极的,精神饱满的。正像尼采的权力意志一样,德勒兹的欲望也总是不断地流动着,驱动着人前进[6]。德勒兹的这种欲望来源自身体,但他没有把意识纳入自己的视野中,他之所以这样,是为了让身体获得彻底的自由,让欲望能自由地流动,在德勒兹这里,身体与理性完全翻转过来。正像笛卡尔认为理性完全可以脱离身体而自由思考一样,德勒兹认为身体完全可以忘记理性而自由地运动。德勒兹其实是把尼采的哲学简化了,如果尼采的哲学是反抗身体奴役的哲学,那么,德勒兹的哲学则是一种享受身体自由与美感的哲学。
德勒兹的这种享受哲学其实正是我们体育所追求的。当我们在进行体育活动时,我们追求的是享受身体自由的舒展所带来的快乐。当由身体所创造出的各种美丽的姿势在我们面前展现时,我们能在内心的深处为这种自然之美所震撼,这种震撼便是身体的艺术所带来的。这也是体育在带给我们健康的同时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更高级的生命的享受。
1.6.3 福柯的惩罚
尼采将理性的主宰地位赋予了身体,这一点使福柯意识到:历史只能是身体的历史。但福柯与尼采又有一些不同,尼采把身体看成生产性的身体,他认为身体生产了历史,并坚信身体的不可摧毁。福柯则对此产生了怀疑,他不认为身体具有无坚不摧的生产性,他认为历史摧毁了身体。因为今天社会的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身体以及其力量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使人们总是对身体进行安排和征服,身体总是陷入被奴役的境地[8]。这样的身体其实是被蹂躏的身体,它失去了自由,不再洋溢着动物精神,不再流动着权力意志。因此,福柯认为,我们的身体被用于从事劳动和服务,使身体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
福柯的观点显然与尼采拉开了距离,福柯更为现实,他进一步走进了社会,发现了身体被奴役这一事实。而尼采把其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哲学的构建和破坏中,忘记了观察社会的事实。福柯的观点也让我们怀疑起竞技体育的本质是否合理?在当今的社会,竞技体育被金钱充斥着,运动员们用自己的身体来满足人们的消费,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健康服用兴奋剂或进行身体难以接受的训练,从而来赚取金钱和荣誉。这种行为是不是身体的奴役呢?这种行为又怎么体验德勒兹的身体的享受呢?这种变质的竞赛又怎能不让福柯痛心呢?而这也是竞技体育的存在是否合理的一种质疑。
20世纪有3个伟大的传统将身体拖出了意识哲学的深渊。追随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梅洛·庞蒂将身体毅然地插入到知识的起源中,取消了理性在这一领域的特权,并开始了其身体美学的研究;以莫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对身体的实践与训练来克服理性对身体的压抑;尼采和德勒兹则完全抛开了身体与理性的对立,沉浸于身体崇拜中;福柯则在现实中发现,身体正在遭受社会的惩罚,正在被人自身所奴役,身体的烦恼再一次展现在历史的画卷中。
2 身体谱系的启示
从荷马对身体的崇拜,经过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灵肉分离,再到奥古斯丁将身体至于灵魂的对立位置,这个过程是身体逐渐被轻视的过程。从阿奎那的反抗,经过皮特拉克的复兴,马丁路德的改革,到培根的科学倡议,这其实是身体逐渐从被轻视走向被重视的过程。然而,在笛卡尔理性的崇拜和斯宾诺莎对身体的轻描淡写中,身体再一次被置于了被忽略的位置,直至经过卢梭的反抗和康德的批判,身体才又一次被哲学家们所重视。此后,身体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中再次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直到费尔巴哈的反抗和马克思的调和,身体才真正获得承认,并取代灵魂成为人类第一位的存在。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把身体作为其哲学的研究中心,与其同时代的尼采则把身体置于其哲学体系的中心,并将身体作为评判一切价值的标准,使身体的崇拜达到了顶峰。尼采以后的德勒兹和福柯也追随了尼采的身体观,只不过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开始了身体哲学的构建。
我们可以从身体的谱系中看出,身体在哲学中的定位并不是一个从被轻视到被重视的简单的过程,在对身体的定位中,哲学的认识更像是一种曲折式的认识进程。从荷马对身体的崇拜到尼采对身体的正名,感觉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点。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从快乐单纯的童年出发,经过多愁善感的少年,再到年少轻狂的青年,然后是疲惫不堪的中年,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了单纯而又快乐的老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了生命,认识什么在生命中最重要,在我们看清生命的本质时,我们才发现,其实快乐是最重要的,小孩子那样的生活才是最令人怀念的。其实人类对身体的定位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最后还是回到了对身体的崇拜,只不过我们比荷马那个时候的人对身体的认识更为深刻了。
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何谈思考?看看那些短命的天才们,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卡夫卡、普鲁斯特,如果这些天才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他们能再多活上几年,我们人类的文明进程又会获得怎样的加速呢?但是历史无法更改,只能从中吸取经验。人首先是个生物,其次才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身体是灵魂的载体,没有身体也无从谈论灵魂。当然,我们也需要理性,需要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更诗意般地栖居在这个蓝色的星球上。
3 体育的价值定位
我国已故的学者李力研先生曾在其《体育的哲学宣言——“人的自然化”》中说:“体育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讲,就是体育是一种防止人种退化和机能衰竭的活动。因为它是关于人类感性如何从他自身理性的重压下获得解放的努力实践。这是发掘体育价值的历史尺度,也是展开体育哲学讨论的根本立足点”[11]。如果说思考是灵魂的一种实践,那么,体育就是身体的一种实践。正如思考可以使灵魂变得更加睿智和伟大一样,体育可以使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和长寿。此外,体育可以使身体获得德勒兹和梅洛·庞蒂所追求的美和自由,在体育活动中人们可以享受身体的自由舒展,可以感觉身体的力量与柔韧,可以体会身体与灵魂的完美结合,而这也正是体育在促进健康之外,最为重要的价值所在。
然而,正如福柯所担心的,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的身体正在承受着各种惩罚,这使它失去了自由,陷入了理性的奴役之中。试想一下,有哪个职业会对面试者的身体条件作硬性的规定?又有几个企业会把员工的身体健康放在利润之上?再看看我们的学校,有几个校长会把体育作为一门主干课程来发展?又有几个体育教师受到了和其他科目老师一样的重视?疯狂的楼房侵占着原本是老百姓们运动的场地,国家大把的资金又有多少投在了体育的基础教育上?当代人的体质越来越差,人们蜗居在楼房里,沉迷于网络中,我们的身体被放置在了可有可无的角落。这是现代人对身体的奴役,是现代生活对身体的奴役,而体育的价值就在于对抗这种奴役。
4 结语
从荷马的吟唱到奥古斯丁的神学,从阿奎那的反抗到弗朗西斯·培根的科学崇拜,从笛卡尔的怀疑到尼采的权力意志,最后以福柯的发现为短暂的结点。我用很粗略的笔触勾勒了从古希腊到现在的身体谱系。这个谱系其实是一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谱系,没有起点是因为在古希腊先哲们以前必然存在着许多关于身体的哲学认识,而这些哲学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识到的,所以,那是个盲区,也就是说,谱系的起点在何处是我们现在的知识所不能确定的。没有终点是因为我只能将身体的谱系记叙到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至于以后的哲学怎样对身体进行定位,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是无从得知的。所以,我所构建的这个身体的谱系仅仅是一个片段,但是从这个片断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启示:身体与灵魂共同形成了人,身体是灵魂的载体,是人类第一位的存在,而灵魂是身体的动力,是人成为人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我们应将身体与灵魂协调起来,达到一种平衡,而体育则是促进这种平衡的有效实践。
[1]艾尔弗雷德·韦伯.西洋哲学史[M].詹文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2]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M].韩东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7.
[3]柏拉图.斐多篇[M].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28, 15-17,65-68.
[4]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2.
[5]陈钦庄.基督教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4.
[6]德勒兹.反俄狄普斯[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50.
[7]弗兰克·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340.
[8]福柯.规则与惩罚[M].刘北成,阳远婴译.北京:三联书社, 1999:27.
[9]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哲学史[M].吕叙君译.济南:山东出版集团,2006:355.
[10]理查德·塔纳斯.西方思想史[M].吴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232,268,301.
[11]李力研.体育的哲学宣言——“人的自然化”[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4,9(1):28-35.
[12]尼采.权力意志[M].贺骥译.云南:漓江出版社,2000:327, 329.
[13]尼采.权力意志[M].孙国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89.
[14]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吕卓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45.
[15]撒穆尔·伊拉克·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M].邓晓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175,299,341.
[16]王安忆.尼采与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2.
[17]王晓朝.希腊哲学简史——从荷马到奥古斯丁[M].上海:上海三联书社,2007:128,386.
[18]威尔·杜兰特.西方哲学故事[M].梁春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6,186.
[19]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52.
[20]吴晓群.希腊思想与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39.
[21]伊曼诺尔·康德.论种类的特性[M].李瑜青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92.
[22]伊曼诺尔·康德.康德的三批判书[M].武雨南川,李光荣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9,90.
[23]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M].孙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76,279,284,286.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502.
Genealogy of the Body—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MA De-hao
The body is the carrier of sports and the basi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enealogy of the body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positioning the value of sports.This paper,through access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traces th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to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the body position changes,and in this change for the clues to construct the body’s genealogy.Derived from the genealogy of the body,the body and soul together to form a human,the body is the carrier of the soul,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first,while the soul is the body’s power,and essential factor for people to become human.Therefore,we should coordinate body and soul together to achieve a balance.Sport is an effective practice to promote such a balance.
body;genealogy;sport;philosophy
G80-05 文献标识码:A
1000-677X(2010)03-0083-08
2010-01-02;
2010-02-28
马德浩(1985-),男,山东聊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与适应,体育哲学,E-mail:madehao4519 @yahoo.cn。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20024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