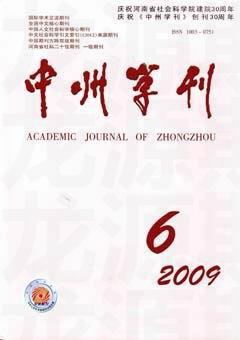郁达夫新论
许凤才
摘 要:自身复杂的性格、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悲欢交织的爱情行旅和良莠相间的交游活动是构成诗人郁达夫生前和死后蒙受不白之冤的主要因素。我们可以从他的婚姻爱情观、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文坛上的“和事佬”等方面来解读他那“光辉的特异的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郁达夫。
关键词:郁达夫;爱情;性格;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6—0210—05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小说,抑或是诗歌、散文,都达到了同时代其他作家所难以攀登和逾越的高峰,有许多名篇佳章至今还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尤其是他那坦荡的胸襟,高尚的人格及瑰丽多姿、带有浪漫和传奇色彩的生活世界,则更是每每为人们所称道。郭沫若就曾著文赞扬他的“卑己自牧”是和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一样为文坛之绝。但遗憾的是,由于诸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像郁达夫这样的有着“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著名作家、爱国主义战士,几十年来却没有得到公允评价,更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甚至还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造成人们对郁达夫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却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之外,恐怕其自身复杂的性格、放荡不羁的私生活、悲欢交织的爱情行旅和良莠相间的交游活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赤者嫌其白,白者嫌其赤。
婚姻爱情观
以炽热的情感,虔诚的心灵,博大的胸怀,努力不懈地去追求新时代具有科学文化知识和青春气息的浪漫女性,并希望从她们那里得到纯洁的拥抱,温柔的慰贴,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和空虚寂寞的心灵,是构成郁达夫绚丽多姿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此作为生命历程的启航点,便导演出了他一生中三次结婚两次离异及多次婚前婚后恋的悲壮剧。
爱,就爱它个热烈真诚,畅快淋漓;决裂,就来它个干净利索,清澈见底。这就是郁达夫的婚姻爱情观。他一生都遵循着这个原则行事,从没有违背过。
郁达夫对女性的追逐和爱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灵的需求,而非肉欲的满足。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视女性为圣洁美和崇高美的象征,一直是在幻梦中生活,清醒之日,便是爱情进入坟墓之时。
综观郁达夫一生的婚姻爱情纠葛,始终都是受这种指导思想支配的,即从倾慕到热恋再至失望到最终分手,冬去春来,夏过秋至,周而复始,从未超越过这个“爱情”的怪圈。
他和第二位夫人王映霞的“热恋”及后来的“婚变”遵循的就是这个“原则”。
郁达夫与王映霞是一见钟情,整个心都沉醉了。初出茅庐的王映霞在他的眼里,既像一株出水的芙蓉,是那样的清纯,那样的苍翠欲滴,给人以精神,给人以力量。而同时,她又像一朵春雨后盛开的牡丹,是那样的美艳绝伦,国姿天香,令人陶醉,使人无限遐想。
为了这株芙蓉,为了这朵牡丹,郁达夫开始发“狂”了,什么家庭、地位、金钱、名誉、权利,一切的一切,他全可以抛弃。此时此刻,他对王映霞的爱,是发自心里深处的,是真挚、纯洁、高尚的,上苍的日月星辰,大地的山川海洋都可为其作证。他认为,只有像王映霞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有地位,既年轻美貌,又时尚新潮的女性,才能够享受他那“猛如电光”似的爱,否则,那就是对爱的亵渎和践踏,而王映霞,只有接受他的爱,以后的人生道路才会越来越光明宽阔,精神世界才会更加丰富多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郁达夫和王映霞终于幸福结合了,成了人人所羡慕的“富春江上神仙侣”。
然而,他们的婚姻一旦出现“裂痕”,彼此不再那么热烈相爱时,郁达夫又回归到了原来的“自我”,毫不痛惜费尽万般辛苦所建立起来的“爱巢”,弃之如履。
无可讳言,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和爱情的纠葛中,既给郁达夫带来了充满甜蜜的欢乐,同时也给他留下了许多难以启齿的苦痛和悲伤。但这二者的混合交织却不期然地成就了他那光辉灿烂的文学大业。少年时代和赵莲仙、倩儿等少女“初恋”时,感情激越奔腾,笔走龙蛇,写下了数百篇天真烂漫、辞藻华美的诗词歌赋,描摹出了那个时代少男少女追求自由追求幸福追求爱情的心灵轨迹。在东洋岛国留学时有所爱,而始终得不到爱的痛苦磨难,成就了他那曾震撼过一代青年读者心灵的光辉名篇《沉沦》。与第一任妻子孙荃的感情波折,生活炼狱,使他产生了《茫茫夜》、《茑萝行》等扛鼎之作,在“五四”新文坛上风靡一时。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杭州四大美女之首王映霞的幸福结合,使他再度焕发青春,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像风光旖旎、引人入胜的山水游记《屐痕处处》,清新美丽的小品文《闲书》,抒情诗般的《东梓关》、《迟桂花》、《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说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而与王映霞的婚变,则使他写出了轰动海内外的千古绝唱《毁家诗纪》。
总之,无论是表现“五四”青年性苦闷的《沉沦》,还是抒发作者愤世嫉俗情感的《毁家诗纪》,或是赞美大革命时代追求进步女性的《她是一个弱女子》等,都是长期蕴藏在他心中的爱和恨相互撞击时所迸射出的耀眼火花。
郁达夫一生中曾三次结婚,两次离异,多次婚前婚后恋,而且每到一处都对那里的女性产生异样的感觉,创作上也随之会出现新的起色和亮点。之所以在他身上会出现这样的奇迹,这除受他独特的婚姻爱情观支配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他的泛爱女性心理有关。
在郁达夫的眼睛里,所有的女性都是可亲可敬的,个个都值得男人们去追求,去怜悯,去爱恋。促使郁达夫产生泛爱女性心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他幼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所致。
由于父亲的英年早逝,和两位哥哥长期在外求学的原因,造成了郁达夫从三岁至十五岁这个黄金时代的生活环境,始终是以女性为核心的世界。祖母、母亲、使婢翠花和邻居家的少女赵莲仙等,即是他这个核心世界里的主要精神支柱。她们的言论、行动、情感及生活方式都“润物细无声”地在潜移默化着年幼的郁达夫。从两代寡妇——祖母和母亲那里,他懂得了什么叫刚毅坚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道理;从使婢翠花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善良、纯朴、高尚和人间真情;从小学时代的女友莲仙、倩儿等人那里,他品尝了爱情的琼浆玉液,并且还领悟了“爱”的真谛。这几点交织融合在一起,便使郁达夫产生了一种对女性的泛爱心理。以后每当在人生的征途上遇到坎坷和曲折的时候,他都自觉不自觉地到女人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
“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
年轻时代的郁达夫,特别推崇英国19世纪初叶“交游最广,和同时代的作家都处得很好”的浪漫主义诗人莱汉特,并且希望自己“将来在中国文坛上也能作个莱汉特那样的人。”综其一生,他也的确实践了自己年轻时代立下的诺言,在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五四新文坛上他是朋友最多的一个,也是大家所公认的“稳健平和,不至于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在新文学团体内部,除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帮凶之外,他与其中任何一位都能友好相处,善始善终。革命阵营内,他的朋友有象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等忠诚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进步势力和中间力量方面,他的朋友更是不计其数——像郑振铎、叶圣陶、蒋光慈、阿英、许钦文、沈从文等成绩卓著的小资产阶级左翼作家,都和他保持着亲密的来往;即使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闲”文人,只要他们不投敌卖国,并能够坚持用白话进行创作,反对文言复古这个大方向,郁达夫也仍以“朋友”待之,如他与胡适、徐志摩、林语堂、陈源等人的关系就是范例。
郁达夫在“五四”新文坛上之所以能够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这是由他“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所决定的。
“圆”——系指郁达夫的交游广,朋友多,不管是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的作家,只要能够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大方向,热爱祖国,追求进步,人格光明磊落,他都能够友好相处;而一旦失去这个前提,“方”的一面也就露峥嵘了,不管你是何人,彼此的关系多么密切,他都会毫不客气地与之决裂,并以敌人视之。
周作人是郁达夫当时最敬重的朋友之一,俩人的关系一向很密切,周作人曾多次对人讲,他不佩服鲁迅的小说,而对郁达夫的小说却情有独钟,并多次为其唱赞歌。是他的《自己的园地•沉沦》的出现,方使骂郁达夫“诲淫”和“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
20世纪30年代前后,郁达夫因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组织,反对封建军阀专制,提倡革命文学,几度上了执政当局的“黑名单”,屡遭迫害,险些遇难,身心都很疲惫。
远在故都北平的周作人,得知郁达夫的真实处境后,不顾受牵连的危险,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多次邀请和敦促他北上任教,以解困厄。
对周作人的深情厚意和古道热肠,郁达夫是很感激的,也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永志难忘。1931年7月6日,他写给周作人的信就是其诸般感恩、钦佩心情的最好体现。
启明先生:
来信早已接读,终因杂事沉繁,迄未作覆。溯自两三年来,因无业而累及先生者,不知几多次。心里头的感激,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这一回的北来,恐也终不能成为事实,所以幼渔先生处,并不发信去问,怕又要踏去年之迹,再失一次信,负一次约也。
自广东回沪之后,迄今五年,因为一时的昏迷,就铸下了大错。遇人不淑,绝似法国Verlaine的晚年。(以此自比,原知僭越得很,然而事实却很相像,并不说个人的天才相像也。)欲谋解脱,原非不可能,但是责任之感,又不能使我断然下此决心,不得已只能归之前定的运命而已。五年来的无心创作,无心做事情,原因都在于此。妇人难养,古今中外似乎是一例的。
近来消沉更甚,苦痛更深,不知者还以为我恋爱成功,不想做事也,真真是千古未有的irony。
南方霉雨未晴,郁闷难堪,北国天气,想较好一点,若有闲暇,请时时赐书,好使我在无可奈何之中略能得着一时半刻的解放,余事后叙,就此请你们全家的安。
达夫敬上七月六日
这封信表明,周作人和郁达夫确实是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好朋友。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挚友”,一旦沦为汉奸,郁达夫也毫不客气地撰文挞伐。在《“文人”》一文中,他怒斥周作人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文化界永远洗不掉的耻辱。
……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时穷节而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
大义凛然,怒斥为私欲而出卖“灵魂”的昔日好友——佐藤春夫,愤然与之割袍断交,是郁达夫“外圆内方”处世哲学的又一具体体现。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私小说”的代表人物,作品素以表现现代人的孤独、忧郁、厌世等苦闷情绪而著称,这一点正吻合郁达夫的文艺思想,所以,俩人自1920年订交后,十数年来关系一直很密切,来往也很频繁。
殊不料,郁达夫的这位私交甚笃,十数年如一日的挚交,中日战争打响后,竟一反常态,肆意污蔑攻击郭沫若等文艺界的抗日先锋,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推波助澜。《亚细亚之子》为其代表作。该文的大意是:一位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北伐之后流亡日本十余年,一天晚秋的薄暮,他的一个姓郑的朋友衔中国最高领袖的密谕,忽而到他的寓居去访问。煽动他回国去作抗日宣传。芦沟桥事件后,汪一个人悄然留下遗书逃回了中国。在各地作了许多热烈的抗日的宣传。最后他发现了自己是被人利用了,作了人家的傀儡,更使他失望的,是他在北伐时代的一位情人,却被姓郑的骗去作了妾,藏置在杭州的金屋之中。于是他就幡然醒悟,重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凡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姓汪的革命文学家”影射的是郭沫若,“姓郑的中国朋友”暗指的是郁达夫。整个故事梗概是以郁达夫秘密动员郭沫若回国作蓝本的。在这篇恶劣之作中,佐藤“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和日本女人爱国爱家的高尚人格,而对中国人民则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进行攻击和诋毁,在他的笔下,中国的男人都是些“出卖朋友的劣种”,女人则“比日本的娼妇还不如”。
《亚细亚之子》虽是文学作品,但影响极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郁达夫看到后气愤异常,除与作者割袍断交外,还接二连三地撰文进行反驳,以正视听。在《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中他怒斥佐藤春夫道:
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平常只在说中国人是如何如何的好,中国艺术是如何如何的进步等最大的颂词,而对于我们私人的交谊哩,也总算是并不十分大坏。但是毛色一变,现在的这一种阿附军阀的态度,和他平时所说所行,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对比!
平时变化莫测的日本文人,如林房雄之类的行动,却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一个时候,即便一变而做了军阀的卵袋,原也应该,倒还可以原谅。至于佐藤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命的。他的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妓了。
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流于笔端,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佐藤自命“清高”、“友善”的画皮,沉重地打击了其反华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
北伐战争时期,郁达夫因误解创造社同仁与蒋介石军阀政府的合作,便毅然和他们断绝往来,视同陌生人,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彼此间的误会消除后,政治观点又趋同一致时,马上又是兄弟,和好如初。
郁达夫和郭沫若既是留日同学,创造社的发起人,又是十几年相濡以沫的挚交好友。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方面发生了严重分歧,以至反目为仇。在《日记九种》中他不但给郭沫若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而且还骂他是新军阀新官僚阶级的代言人。
对郁达夫的嘲讽谩骂,郭沫若也因忍耐不住,遂在《英雄树》、《桌子的跳舞》、《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章里进行反驳和批评,甚至还说出了许多超越理智和伤感情的话,以致彼此十年未再发生任何联系。
对与郁达夫的“反目”,郭沫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里曾有过很深刻的检讨:
我们那时还年青,感情彼此都不容易控制,是值得遗憾的事,但我始终对达夫是怀着尊重和惋惜的意思的。我尊重他的天才,尊重他的学殖,尊重他的创作成绩,更尊重他的坦白直率,富于情谊,为了朋友每每不顾一切,把自己置诸度外;但我可惋惜他有时候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而且他往往过分自贱自卑,这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自暴自弃或不自爱不自重的程度的。可是今天我得承认,这些都正是达夫的美德。他那样容易忘我,实在是他的品格崇高的地方。我自己比起他来,实在是庸俗得非常。我虽然也是一位冲动性的人,但比起他来,我更要矜持得多,更有打算得多了。我做一件事情,每每有点过分的思前想后,而采取保守。在表面看来,我好像是位急进分子而达夫倾向于消极,而在我们的气质上,认真说,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但他的积极进取没有得到充分的适当的展开,那是应该归罪于时代和环境的。
这一段话既有对于郁达夫高贵品德的赞美,又有作者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即谴责自己不应该轻信达夫的情感冲动之言,而与其“反目”。
经过十年的风雨沧桑,郁达夫和郭沫若彼此都认识到了当年“反目”时的轻率和鲁莽。1936年郁达夫访日,又重新沟通了他们的友谊。
1936年的11月底,郁达夫应日本友人的邀请,前往东京讲了一个月的学,他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就驱车郊外的千叶县看望郭沫若及其家人。
反目十年,初次相见,他们早已把过去的那些龉龃丢得一干二净,仍同少年同学时代一样,天真地谈吐,愉快地欢笑。一天的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了,直到日本朋友再三催促他们赴宴时,方才结束了这不同寻常的谈话。
在日本友人举行的欢迎郁达夫的宴会上,郭沫若心潮激荡,思绪万千,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他们在上海一块过“笼城生活”的时代,特别是四马路醉酒时的情形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他按捺不住奔涌的情思,挥笔写道: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家又亡。
接到郭沫若的赠诗,郁达夫也同样激情满怀,泼墨如云:
却望云山似蒋山,澄波如梦有明湾。
逢人怕问前程驿,一水东航是马关。
新文坛上的“和事佬”
五四新文坛上不同的流派、不同风格的社团多、杂志多,人与人之间也因文学主张不同而分成一群群,一团团,这样也就造成了社团与社团之间,杂志与杂志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经常发生相互攻讦,摩擦不断。这样也就需要一个德高望重、学识渊博、通情达理,无论是哪一方哪一派都能够接受的“和事佬”来调解彼此间的争执。无疑,这个角色在当时非郁达夫莫属。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双方激烈争论正酣的时候,是郁达夫借郭沫若《女神》出版一周年之际,把双方在上海的会员召集到一块开了个纪念会,以求“把微细的感情问题,偏于一党一派的私见,融合融合,立个将来的百年大计”①。
围绕女师大风潮,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为首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西滢等人为主的“现代评论”派争斗得如火如荼,郁达夫站在中间立场上,以客观的态度,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指东道西,调解矛盾,缓和气氛,以求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对郁达夫的调解,双方都颇以为然。陈西滢等人向鲁迅“求和”休战时,还是郁达夫从中传的话。
鲁迅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新旧朋友都既敬之又惧之,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定居上海后,时常与朋友发生矛盾,而一旦矛盾出现,双方都不能自行解决时,无一例外地都请郁达夫出面调解。如1927年,北新书局长期拖欠鲁迅版税,累积达一万四千元之巨,多次索要不得时,鲁迅只好请律师准备诉诸法律,以求公正解决。北新老板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一天就向暂居杭州的郁达夫发了两封电报请他回上海调解,而鲁迅也在同一天既去信又发电报,敦请郁达夫出面解决这件事。而这时的郁达夫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接到双方的电报,只好牺牲计划中的创作,不辞辛劳地奔波于沪杭之间。经郁达夫的调解,双方重新握手言好。
虽然因奔波于沪杭耽搁了计划中的长篇小说《蜃楼》的创作,但郁达夫并没有感到遗憾,相反的他还常常引以为自豪。10年后,他在《回忆鲁迅》中特重彩浓笔地描述了这件事的起因和经过: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糊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楚。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当时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写了的《蜃楼》,写它完来。但住不上几天,北新就有电报来了,催我速回上海,为这事尽一点力。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从宏观——整个社会的角度上来看,是矛盾重叠,关系错综;若从微观——个人生活的角度上来看,那则是年年岁岁都可称得上是多事之秋。表现在一代文豪巨匠鲁迅和郁达夫的身上更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就在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得以和平解决的当天晚上,却又发生了鲁迅和林语堂因误解而引起的矛盾冲突。
鲁迅和林语堂,也与他和郁达夫、李小峰等人一样,彼此间是早就有来往了,并存在着一定的友情。说起来此友情还可追溯到1923年他们一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②当时的林语堂曾态度很鲜明地表示,他是属于后一派的。据许广平讲,她在《两地书》中称鲁迅为“小白象”就是从林语堂的一篇文章中借用过来的。“象”多是灰颜色的,偶尔遇到一只白颜色的,就为一些国家所宝贵珍视了。林语堂认为,鲁迅在中国的难能可贵,就如同自然界的白象一样应该为人们所稀罕所珍贵。由此也说明了林语堂对鲁迅精神及其著作的认识和理解程度。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不顾个人受牵连的危险,接二连三地发函邀请身处逆境的鲁迅到自己任职的厦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辗转来到上海时,他也接踵而至,其交往也比以前更加频繁。1929年的8月28日,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纷得以和平解决的当天晚上,李小峰为答谢这次矛盾的调解人,缓和书局与鲁迅之间的矛盾,特在南云楼举行宴会。作为北新书局及鲁迅和郁达夫的共同朋友林语堂,也应邀前往作陪。在酒酣耳热之际,林语堂不知是有意地或是无意地竟突然对春野书店的创始人张友松大发了一通议论,而且言语中还多含批评和谴责的成分。
张友松原与李小峰一样,系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他在筹办和经营春野书店的过程中曾得到鲁迅不少帮助。鲁迅这次为版税问题计划向北新书局提出法律诉讼,外间及北新书局方面的人多误认为是由他从中挑唆作梗而引起的。在这样的一种背景和场合下,林语堂突然对他进行评头论足,很自然地要引起鲁迅的反感。刹那间,鲁迅的“脸色变青,从座位里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③
在鲁迅与林语堂这场面对面的冲突中,郁达夫又一次起了和事佬的作用。他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就又“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这一按一拉,便平息了这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的冲突。
但据郁达夫的观察,造成这次鲁迅与林语堂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鲁迅的疑心和误解所致。他的论据是:依林语堂与鲁迅多年的交情,及他对鲁迅的崇拜程度进行推猜,他是不会在众目睽睽的场合上讥讽鲁迅,替北新书局鸣不平的,这是其一;其二,憨厚正直有余的林语堂在宴会上说出了一些令鲁迅疑心和不快的话,那也只是偶尔的疏乎所致,根本不存在着什么对鲁迅不敬和讽刺的意思。
由于郁达夫认为,林语堂对鲁迅并没有怀什么恶意,彼此间是因误解而发生冲突的,所以在这之后,他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疏通他们之间因误解而形成的隔阂,使他们重新言和语好。后来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自传附记》中谈起这件事时说到,当时鲁迅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象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
经郁达夫的斡旋,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很快又重新融洽起来。如1932年林语堂创刊《论语》,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时,鲁迅虽不太赞成他这种做法,但还是给予了有力支持。
1931年,《文学》杂志的主编傅东华在杂感《休士在中国》里发表了对鲁迅不敬的言辞,鲁迅看后非常反感,一方面写文章声明傅东华文中所言非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则写信责怪《文学》杂志编委会,扬言要退出编委会。
傅东华原没有想到问题这么严重,只是兴致所至,随手拈来而已,一看事情闹大了,急忙请茅盾召集编委会商量解决办法。编委会的意见,一方面委托茅盾出面代表编委会向鲁迅道歉,请其原谅,另一方面则公开发表编委会向鲁迅道歉的书面函。尽管如此,鲁迅的怨气仍未消除,决意要退出《文学》杂志编委会。茅盾等人无计可施,最后还是请郁达夫出面,才算把这事摆平。
注释
①郁达夫:《〈女神〉之生日》,《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③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