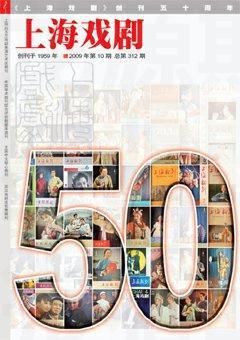话说“梅党”



梅兰芳后来的成功,也同他善于同知识分子交朋友有关。梅兰芳“从善如流”,学习的对象还包括票友。他与票友同台演出时,往往戏码排在后面,他经常会早早来到戏园子,到侧幕边仔细观摩票友的演出。
这里插一句,什么叫票友?
票友的来历,出自满清入主北京的初期。刚建立的清政府,派八旗子弟中有表演能力的青年,走到全国去,以文艺形式,宣传以清朝来代替明朝的好处,这些业余演员,都拿着一张皇帝颁发给他们的“龙票”,作为“钦差宣传员”身份的凭据,因此被称作“票友”。后来,这“票友”二字,就社会上用来泛指那些能够登台表演的非专业演员。
梅兰芳的《玉堂春》,是一位名叫林季鸿的外行人士编的。这位林季鸿是福建人,酷爱京剧,可是他连票友都称不上,因为他从来没有登过台。他设计出来的《玉堂春》唱腔非常好听,是梅雨田推荐给梅兰芳的。既然唱腔搞得好,管他设计者是什么身份呢?梅兰芳就采取“拿来主义”,大量采用,这就使得《玉堂春》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梅派新腔的一个标志,天下仿效,流传到今天。
梅兰芳家里的书房叫做“缀玉轩”,“缀玉轩”里的常客,被称作“梅党”。“梅党”中有剧作家、评论家、金融家、学者、记者、画家等。梅兰芳就像梨园行里的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家聚在一起,审时度势,不时地讨论,梅兰芳应该拿出什么戏。他们研究剧本创作,编新戏。在这个编剧的圈子里,有齐如山、罗瘿公、吴震修、黄秋岳、李释戡、许姬传等人。
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世家,曾经在北京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学习德语和法语,后来旅居欧洲。回国后,齐如山对比了中外戏剧,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他看了一些梅兰芳的戏,写信去为梅兰芳提建议,梅兰芳就回信,希望能够约谈。《齐如山回忆录》这么写道:
“我给他写了两年多的信,我还没有跟他常谈过……一因自己本来就有旧的观念,不大愿意与旦角交往。二则也怕物议……三则彼时相公堂子被禁不久,兰芳离开这种营业,为自己名誉起见,决定不见生朋友,就是从前认识的人也一概不见,这也是我们应该同情的地方……及至我到他家,留神仔细一看,门庭很肃穆,本人固然是谦恭和蔼,确也磊落光明,实在是不容易。本界的朋友,来往的已经不多,外界的朋友更少,倒是有几位比我认识他早几年或者一二年,也多是正人君子……或者有人会说,目下还谈到相公堂子,未免有伤厚道。其实不然,它原也是一种事业,数百年来好角都在相公堂子中,这也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实事。”
齐如山后来成为梅兰芳的重要幕僚,帮梅兰芳写了不少新戏,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牢狱鸳鸯》《黛玉葬花》《俊袭人》《廉锦枫》《西施》《洛神》等等。
新戏排练时,“梅党”坐在下面评头论足,提出意见,梅兰芳会非常认真诚恳地听取。当然,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意见,往往也有一个如何“化”的问题,在“化”的过程中,大主意是梅兰芳自己拿,身边还有姚玉芙、朱桂芳等行内人士,帮他具体出主意,排戏。因此凡是老戏,经梅兰芳的改动,搬上舞台后,往往就有了新意。加上“梅党”为梅兰芳搞的一批新戏,包括新编的古装戏、歌舞戏和时装新戏等,梅兰芳给当时的北京舞台,带来一片清新,于是“梅派”二字,呼之欲出。
“梅党”除了写戏、编唱腔以外,还干什么呢?
今天,许多演艺界的大腕都有经纪人和做宣传的撰稿人。我这里介绍一位梅兰芳身边的剧评家兼记者,名叫张豂子。他是我们江南人士,原籍上海青浦县,又名张厚载,本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一些学者以西方文化为坐标,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除了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外,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京剧,称之为“旧剧”。当时批判得比较积极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名鼎鼎的学者,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豂子,一个人跳出来同他们辩论,坚定站在捍卫京剧的立场。双方的论文都发表在当时很出名的《新青年》杂志上。
大家想想,一个学生,敢于独自反对和顶撞大师,其中有的还是他北大的师长,结果会怎样呢?——他被校方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为理由,开除了。此时张豂子四年级,正准备毕业呢。此时遭到开除,实在是可惜。
梅兰芳了解张豂子的上述情况后,十分同情,便把他罗致到缀玉轩里。张豂子本是“梅迷”,后来他在记者生涯中,发表了许多关于梅剧的评论,成为梅派艺术的极力鼓吹者。
天时,地利,人和。不言而喻,梅兰芳此时,已经从一个一般的演员,成为角儿了。
可是,在北京成了角儿,还未必能够得到整个梨园行的真正认可。大家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上海已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有外国人的租界,文化上比较开放。南下的名角所赚的包银,比在京城多几倍甚至几十倍。上海对角儿很注意商业化的包装。比如一个名老生出台,在北京的宣传往往就是戏园子门口挂一个水牌,水牌上写你的名字和戏码。然而在上海就没这么简单了,完全可能是霓虹灯高悬于市中心,亮着你的名字,而且冠以“全国老生冠军”“全球第一老生”这样的头衔。上海的报纸多,舆论比较开放,可以把你捧到天上,溢美之辞不绝,然而如果你演不好,那么剧场里马上给你叫倒好,第二天报纸上也会开骂,又把你贬到地下。这个舆论监督是无情的。因此梨园行认同了一个评判标准,叫做“不到上海不成名。”
1913年底,梅兰芳第一次在上海演出,是跟随老生演员王凤卿挂二牌去的,由于上海观众不知道梅兰芳是何许人,因此剧院老板给梅兰芳的包银,起先比王凤卿少得多。王凤卿是王瑶卿的弟弟,他当时在上海的包银,每月3200元,而梅兰芳起先只有1400元。王凤卿认为老板对梅兰芳估价太低,要求增加,老板觉得梅兰芳不值。于是王凤卿就要求,从自己的包银中扣400元,加给梅兰芳。老板觉得过意不去了,这才把梅兰芳包银,勉强加到1800元。
前三天的演出,叫做“打炮戏”,由王凤卿唱大轴,就是压台戏。在压台戏的前面,末了第二出,叫做“压轴”或者“倒第二”,这是梅兰芳单独主演时的戏码。三天演下来,观众对王凤卿和梅兰芳的反映都非常好,天天客满,老板喜出望外。于是王凤卿向老板提出,要为梅兰芳单唱的戏,排一次大轴。这一次,老板态度同以前不一样了,他对王凤卿说道:“只要您肯把大轴让出来,完全可以呀。”
在上海演大轴戏,当然是一种荣誉和资历,可是如果弄得不好,也可能是危机。因为当时王凤卿正红在风头上,如果把王凤卿的戏码移到前面,观众看完他的戏以后,“抽签”,也就是提前离场了,那么对于后面演大轴的演员来说,名誉就会受到损失。这时,从北京专程来捧梅兰芳的梅党“智囊团”,想出了好办法。
“智囊团”里有一位底蕴深厚的长者叫冯耿光,字幼伟,行六,因此又叫冯幼伟,冯六爷。冯六爷早年是同盟会员,在袁世凯独裁时期,很受江苏总督冯国璋的信任。冯国璋在是否“倒袁”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冯耿光向他分析形势,促成了冯国璋倒戈,使得当时冯国璋“站队”就站对了。袁世凯称帝,在万众的唾骂之下死去,于是冯国璋便当上代理大总统。冯国璋感激冯耿光啊,想封他一个官作为答谢。给他什么官呢?财政总长吧。冯国璋想,财政总长钱多,想必冯耿光能够接受吧?谁知冯耿光对冯国璋说:政府的官员我不能当,你想啊,如今政局动荡,一旦你总统下台了,树倒猢狲散,我这个财政总长还保得住吗?冯国璋问:那么你想要什么职位呢?冯耿光说:你让我到中国银行去当头头吧。他心里想,如果这样的话,不管谁当总统,谁当财政总长,都会有求于我。果然他就当了中国银行总理。冯耿光特别爱听戏,在梅兰芳十四岁时,发现他是个人才,就主动去帮助他,扶植他,后来在芦草园为梅兰芳安排了房子。冯耿光对梅兰芳的一生,起了很大作用,堪称是梅兰芳的导师、幕僚和经济后盾。穆辰公在《伶史》里这样援引梅兰芳对冯耿光的评价:
“他人爱我,而不知我,知我者,其冯侯乎?”
当时冯耿光的意见是:这次在上海演大轴戏,虽然有风险,但机遇一定要抓住。冯耿光和几位上海的朋友一起,分析了前几场戏的观众反映,发现一般上海观众,爱看唱做并重的戏,如果梅兰芳继续演老腔老调的唱工戏,那么大轴肯定压不住,应该搞一个新颖生动的,表演性比较强的戏。演哪出为好呢?梅兰芳接受了冯耿光等人的意见,临时学了一出《穆柯寨》。《穆柯寨》表现的是穆桂英在战场上,萌发情愫,与杨宗保“假打真爱”的故事。在这出戏里,观众可以看刀马旦的“枪架子”——一种舞蹈程式,同时,还可领略穆桂英复杂的心理活动,确实是既漂亮而又生动有趣。梅兰芳由于学过钱金福所教的身段法则,因此对这类做功戏掌握得很快。
第一次演完《穆柯寨》后,效果不错,不过还有问题。冯耿光指出:由于穆桂英的装扮,背上有四面旗子,就是扎上了靠旗,梅兰芳没练过,不习惯,在台上经常低头,不好看。于是下一次演这出戏时,冯耿光就坐在二楼的包厢,一见梅兰芳在台上低头,就鼓几下掌。这种掌声出现的时间,并不在表演的精彩和“节骨眼”处,此时梅兰芳在舞台上,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掌声的来源:是从哪个包厢里传出来的.根据这个“暗号”,他就知道自己老毛病又犯了,于是赶快改正,把头抬起来,形象又好看起来了。就这样,《穆柯寨》越演越好,大轴,终于压住了。
(选自翁思再著《非常梅兰芳》,中华书局2009年1月第一版,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