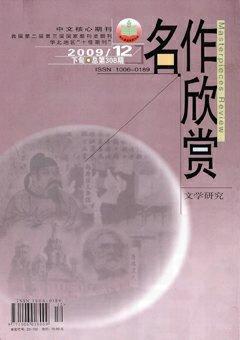浅析波德莱尔的应和之美
关键词:波德莱尔 应和论 审美 恶之花
摘 要:波德莱尔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其才华令世人所倾倒,探寻其诗作可以发现,除了他孤独的诗品于众不同之外,他独树一帜的诗学理论——“应和论”也是使其大放异彩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波德莱尔作品的阅读,结合他的身世,全面的看待并分析他诗歌中的应和因素,最终证实正是“应和”这一诗学理念才使得波德莱尔的诗歌贯穿着永恒的美感。
作为一位顶级的诗人,波德莱尔不仅为法兰西人所知,更在世界范围享有盛名。他的一生充满曲折历程,六岁丧父,七岁母亲改嫁,这些童年的阴影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忧郁的阴影。然而,他的诗让世人所倾倒。波德莱尔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派诗歌先驱,称他为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也不为过。读过他的诗的人们都能够体会到这个茕茕孑立的才子深邃的沧桑。难以想象生活中充斥着忧郁、颓废的波德莱尔一方面饱受惶惑,同时又能够沉浸在不幸的快乐之中。他的诗作里随处可见其复杂情感的错综交错:对社会的怨恨(“我迷失在这世界里,被众人推揉着,像一个厌倦了的人”);对亲情的失望(“如果有个人年纪轻轻就识得忧郁和消沉的滋味,那肯定是我”);幻想的破灭(“我的青春是一场晦暗的风暴,雷击雨打造成了如此的残凋”);对理想的追寻(“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在深邃浩瀚中快乐地耕耘”)等等。这些令他歇斯底里的思绪往往使得他不能自控,想抛开所有的一切升入无忧的天堂,却又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向往,所有的拼命挣扎均为徒劳。备受煎熬的波德莱尔万念俱灰,却又不甘放弃。于是在这进退两难的尴尬中诞生了他的惊世杰作《恶之花》。这丛花并未带来应有的馨香,相反却招致世人的惊骇与诋毁。透过人们的谩骂与攻击,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波德莱尔之所以可以如此勾勒周围的世界,那他必然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与人格。
其实,波德莱尔并非是什么邪门歪道的异类,他只不过是个不愿意走寻常之路的孤独旅者,当然这会让许多自诩为循规蹈矩的人对他的行为看不顺眼。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会公允地归还每个人应得的认可。在他短暂的生命中,波德莱尔创造了令人胆战心惊、满是绝望气息的诗篇。虽然他生前未能获得认可,但在离世后却大放异彩,博得了无尽美誉,就仿佛是一瓶陈年老酒突然拔去瓶塞,散发出无法抵挡的诱人芳香。重新审视他的诗歌,人们不难发现,他的诗歌理念使浪漫主义重新散发青春的魅力,他的应和论让象征主义找到了源泉,他纤毫毕见的真实描写与自然主义交相呼应。众多流派的文人大家,都视波德莱尔为自己理论的体现者、实践者,都以波德莱尔归属自己阵营而荣。说实话,可能在时代的变迁大潮中,在创作生涯的沉浮起落当中,波德莱尔未必真正地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真实的创作情感与异常的文风魔力却将他再次成为大众的焦点。
要想实实在在地理解波德莱尔唯一的途径就是尝试解析他的应和论。有了应和的存在,文学就出现了无数的可能性;有了应和,象征主义在文学中初见端倪;有了应和,诗人改变使命成为“通灵者”;也因为有了应和,人们内心中精致细微的情感才得到了完整的展示。
波德莱尔的应和这一理念最初是在他的一首被称作“象征派宪章”的同名十四行诗《应和》中提出的。该诗缩小了无限,容纳了无限,包含了波德莱尔诗艺的全部要诣。当然,要说应和论的诞生完全归功于波德莱尔一人也是不准确的。在西方传统理论中,许多官能感觉是被排斥在美学领域之外的。人们只承认眼睛能看见对称,耳朵能听见和谐,而否认其他审美快感。但是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于是乎许多哲人学士便在其著作中留下点点应和之痕迹。上溯到柏拉图,他认为“可感的、物质的现实不过是思想的反映,亦即精神的反映”。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不过是瞬间一些知觉触觉的感应而已。昔日的积淀与时下的所感所知交相呼应,各种不可名状的激情与思绪在大脑中膨胀、碰撞,从而泉涌般衍生出别具一格的灵感。对于这种似乎超自然的头脑、心灵现象,柏拉图认为不可名状,只好将其解释为神灵附体。真正对波德莱尔产生本质影响的是瑞典哲学家史威登堡和德国作家霍夫曼。史威登堡从神学的角度阐述了颇为相似的“对应论”:“上帝如同精神的太阳,它的温暖是爱,它的光明是智慧。这同自然界中的太阳是对应的。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间,在可见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都存在这种彼此契合互相对立的关系。”这给了波德莱尔无限的激励与力量,于是他在《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中说:“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这些理念最终都在他的那首十四行诗中得到了体现。而霍夫曼的《金瓶》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去表现一种神秘的融洽,例如苹果篮子可以发出声音,接骨木的叶子和花朵可以唱歌,钟绳可以变成一条蛇;卖苹果的女人既是算命者的夫人,又是户籍官家里漂亮的铜门环,原来她的爸爸是一条破羽毛扫帚,她的妈妈是个烂甜菜根。这一切看似荒谬至极的描绘令人匪夷所思,仿佛是后现代式的无厘头。然而恰恰是这种对美的永生不死的赞叹让人类认识自然自身的存在,认识何为真实。波德莱尔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窥视前人无暇顾及的激情与感受,从而超越了象征。
中国的古人前辈中也不乏与波德莱尔产生思想相撞火花之人。比如李商隐,读他的诗就像读波德莱尔一样需要我们学会在隐晦中去沟通、交流。再比如像曹雪芹,读他的《红楼梦》百遍千遍都会有新的体会与收获。波德莱尔的《应和》一诗正是如此。它以神秘的笔调描述了自然与人类的休戚关系,即万事万物彼此联系,互为象征,传递出模糊的信息,激起人类内心不可解的感应。只有经过“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有着异与常人的感知力”的“诗人”,才有资格作为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纽带,用“熟识的目光”去洞察这些光怪陆离的契合,深入到“混沌而深邃的统一体中”。此外,该诗还通过“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应和”,提出了各种感官是彼此相通的理论。香味同触觉的相似(“嫩如孩子肌肤”),香味在声音上的理解(“柔和如双簧管”),香味在视觉中的消融(“碧绿好似草原”),从各种香气弥漫到颜色、视觉和听觉,再激发出彼此应和的回忆和思想,最后在转换中又落在心灵上产生感情。这个过程教人懂得色彩、轮廓、声音的道德含义,懂得事物与人类间存在着绝对的平衡关系。由此,诗人的使命发生了本质的更改。诗人不再以引导人类为己任,而是努力去表现万物间最细小的关系,完成记录世界的使命。用波德莱尔自己的话说:“诗人如果不是一个翻译者,辨认者,又是什么呢?”应和贯穿了波德莱尔的整个诗学理论体系,例如“丑中之美”这一重要的美学理念就体现在其中。传统的诗人和作家往往坚持真善美与丑恶的绝对对立,而《恶之花》中的波德莱尔始终对恶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态度,他对这朵病态之花的描述令人窒息。他虽然强烈希望摆脱腐朽与死亡的国度,但同时认为这个王国在美学上是光明和令人神往的,要从痛苦中发掘出善和美来。恶与善始终呼应,麻醉着诗人的感官,让他挣扎在爱恨之欲的煎熬之中。想象力也是波德莱尔诗中的另一重要命题。他认为想象力是应和现象的引路人和催化剂,正是这种珍贵的禀赋告诉我们颜色、轮廓、香味所具有的精神含义。由于推崇想象,波德莱尔在作品中大量使用比喻。例如“回忆有一只号角;遗忘有一只口袋;爱情是个孩子,坐在一个巨大的头颅上,吹肥皂泡;而悔恨则从水底冒出来,脸上现出了微笑”。这些奇异的话语中应和的身影清晰可见。
在应和之力的支撑下,波德莱尔于自己的诗歌中大肆激发和谐的情感。运用朦胧的意象,清晰饱满的韵律,无尽的想象空间,独具匠心的表达理念,光怪陆离的言语,以及多重感官的完美融合,波德莱尔为我们塑造了一幅超越时空,跨越疆界的组合图案。当我们全神贯注、若有所思地欣赏波德莱尔的诗歌时,也正是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之时。因为在波德莱尔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会迷失,可能会彷徨,但在体会诗人那份感伤及忧郁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可以体味到某种别样幸福的时刻。带着那丝丝熟悉感,去领悟沉重地懊悔犯下原罪的迷茫诗人,与他一起在诗的世界中声嘶力竭地呼喊,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波德莱尔那呼之欲出的应和之美。
作者简介:付江涛,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1]Baudelaire, Charles-Pierre. Baudelaire in English[M]. Edited by Carol Clark and Robert Sy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8.
[2]Aggeler, William. The Flowers of Evil[M].Fresno: Academy Library Guild, 1954.
[3]Wagner, Geoffrey. Selected Poems of Charles Baudelaire.[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4.
[4]刘波. 波德莱尔“应和”思想的来源[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04).
[5]刘波.《应和》与“应和论”——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基础[J].外国文学评论,2004,(03).
[6] 尹小玲,赵彩花.试析波德莱尔的应和论[J].韶关学院学报,2001,(07).
[7] 让-保尔·萨特.波德莱尔[M].施康强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8] 皮舒瓦,齐格勒.波德莱尔传[M].董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郭弘安.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水 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