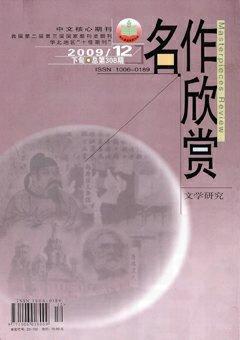刚柔间的游走
关键词:生存 意义 当代 小说
摘 要:当代小说常以历史或现实为媒介,以文学形象为符号,传达对人性和生存意义的探讨,做出关于生存意义的文学阐释。本文选取四部有代表性的当代小说作为观测点,尝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有关人性和生存意义的阐释做一粗略描述,并对阐释间的关联,以及与当代社会形态变迁的联系略做探究。
生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文学家始终关注的大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代小说常以历史或现实为媒介,以文学形象为符号,传达对人性和生存意义的探讨,做出关于生存意义的文学阐释。本文选取四部有代表性的当代小说作为观测点,尝试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有关人性和生存意义的阐释做一粗略描述。
一、寻觅家园的青春歌谣
家园是生存的根,有关寻觅家园的故事是探讨生存意义的永久话题,《黑骏马》是这类小说的杰作。
《黑骏马》有表里两层结构:表层是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里层隐含着寻觅家园的主题,而寻觅家园的主题则是通过“归来——离开——再归来”的结构模式体现的。离开草原的“我”,成为一个不良少年,于是被父亲送回草原。由于在草原之外生活过,“我”的思想中便有了一些不同于草原的准则,特别是有关婚俗的法则,最终又离开草原,走入城市。但是城市的生活法则,又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在《黑骏马》中,草原与城市成为截然对立的两个世界。草原是民间世界的象征,城市是主流社会的缩影。“我”漂泊寻觅的过程,正体现了人物回到民间世界、离开民间世界、最终回归民间世界的历程。
《黑骏马》所描绘的民间世界的美好,在于它拥有爱和宽容。而这爱和宽容在《黑骏马》的民间世界中,主要是通过女性形象去表现的。“我”想:“女孩总该比男孩纯洁些,就像索米娅比我要纯洁一样。” “女孩总该比男孩纯洁些”,是《红楼梦》“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这“女尊男卑”观念的当代翻版。《红楼梦》的理想世界是大观园,那是一个女儿国,是一个逃离男权压迫的避难所,在这里大观园表现了对男权世界的反抗。人类数千年来的社会形态主要是男权社会,文学中对主流社会的反抗常常是以反抗男权的面目出现,《黑骏马》所展现的草原理想世界带有浓厚的女性色彩,其本质也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反抗。《黑骏马》似乎在说明着疏离主流社会的民间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最好家园。
二、至刚至烈的生命欢歌
《红高粱》被文学史家誉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其实是用抗日历史外衣包裹着的人性传奇,是在战争与爱情、死亡与新生的交响里讲述的人性故事,是至刚至烈的生命欢歌。
《红高粱》所歌颂的是蔑视人间法规的爱情。奶奶和爷爷的相爱,既违反法律又违背道德,但他们的爱情却又是合乎人性的自由的男欢女爱,他们的爱情追求是对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姻的反叛,这就使这一违法而不道德的恋情变得合情合理,而这对敢爱敢恨敢哭敢笑敢作敢为的男女更得到作者的热烈赞颂。《红高粱》在战争的背景下、在死亡的阴影里,书写爱情,书写情欲,书写爱的渴求与生的欢狂,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极点。
作者对爷爷、奶奶们充满敬意与热爱,他崇敬的是这些人所构成的充满野性的民间世界——一个极端矛盾的统一体:“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爷爷、奶奶等人似乎是《水浒》中草莽英雄在当代小说里的复活与再生。作者以现代人的“种的退化”与之对照,更凸显了民间世界的强悍有力与勃勃生机。
如果说,当初《黑骏马》对民间世界的认同还有些迟疑,到了《红高粱》则是斩钉截铁、义无返顾地讴歌民间世界,并对民间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给予充分的肯定。如果说,当初《黑骏马》对生命和人性的描写还有些刚中带柔,而到了《红高粱》,则是在战争与爱情的交响中,表现死的庄严与生的欢狂,并将至刚至烈的人性张扬到了极点。
三、磨蚀生命的凡俗哀叹
《一地鸡毛》被文学史家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它在对现实做出另类的描述和解说中,阐释了作者对生存本质的认识。
比起“一地鸡毛”,“豆腐”的意象在小说中更为突出,它贯穿始终,意蕴丰富。小说由“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开始,到“老婆醒来,见他在那里发傻,便催他去买豆腐。这时小林头脑清醒过来,不再管梦,赶忙爬起来去排队买豆腐”结束。“豆腐”成为凡俗生活里最为重要的东西,它代表了凡俗生活的全部内容、全部追求和全部目的;而它也象征着被生活所磨蚀的生命,渐渐变得如豆腐般软弱稀松而不堪一击。豆腐即人生,人生如豆腐。作品活生生地勾画出人对现实无可抗争的处境,揭示出这处境的荒谬。这种讽刺精神来自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原则的绝望,从根本讲是社会人生的一大悲哀。①
由《一地鸡毛》可以看出,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从《红高粱》至刚至烈的人性张扬,走向了以阴柔取胜的生存策略,这折射了文学由社会中心逐渐向边缘的隐退,表现出作家由个性张扬走向情感内敛的时代特征。
四、至阴至柔的生存寓言
与《红高粱》所张扬的至刚至烈的人性相比,《活着》刚好表现的是生存的另一极——至阴至柔一极。
“这是一个寓言,是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遍生存意义的寓言。”②作者如此阐释这寓言的内涵:“《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③显然,《活着》试图阐述的,是一种以苦难命运为友的生存策略。
《活着》的主人公在经历了富贵、别离、战争、饥馑以后,在父母妻女及所有的亲人都相继离世以后,仍然坚持生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乐。“‘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不仅显示了一种达观的生活态度,同时也意味了对自我身体的珍惜。注重自我的肉身、自我的感觉,注重生活的当下感,把活着作为生活的全部理由,用以对抗所有迎面而来的幸与不幸。此时“人身对自身的在世短暂性和有限性的恐惧和忧伤被一劳永逸地克服了,有限人身与无限恒在的亘古裂伤被彻底解决了”④。
《红高粱》与《活着》,从至刚至烈到至阴至柔,在刚柔的两极间完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关生存意义的文学阐释。
五、在刚柔两极之间
20世纪80年代前期,多元经济形态的试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拓宽了国人生存的思想文化空间,而这一切折射到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主流文学中民间社会与民间世界的耀眼登场。非主流的民间价值观、世界观在文学作品中一再得到作者们的肯定与认同,从《黑骏马》到《红高粱》可以粗略地看到民间世界在文学中的从崭露头角到如火如荼。伴随着民间世界崛起的是人的觉醒。80年代“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使启蒙主义的人文理念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之中,人的自信、历史的自信使80年代的中国文学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气息,而以《黑骏马》、《红高粱》为代表的8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则更是挥洒出人的创造历史的激情。电影《红高粱》让我爷爷跪向红袄红裤、仰卧如大写“人”字的我奶奶,正是用影像对80年代人性觉醒的最好描写与概括。
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的挫折和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同时也挫败了国人的自信,“大写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萎缩成一个如当时的流行歌曲所唱的“小小的我”。而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新写实小说”中,更可以感受出现代人的逐渐萎缩。“80年代后期改革的挫折不仅激荡起社会普遍的贫困之感,同时更深刻地引发了人对自身的怀疑,对自身的能力、信仰、道德观念、伦理准则等方面的自信心逐渐丧失。在当下时势的起伏变幻中,人发现自己不能改变什么,也不能把握什么,人对历史无能为力;同时,人对自身也失去了把握,变幻的时势冲击了曾经的信念,人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危机。”在《一地鸡毛》、《活着》中,创造历史的激情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人无法掌握命运的无力感,是历史的无从知晓、未来亦无从把握的颓废与伤感。”⑤
在《黑骏马》、《红高粱》诞生的时代,社会需要文学充当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急先锋,文学的启蒙话语始终居于意识形态体系的中心地位,此刻小说中的自我主体便自信强大,勇于反叛,充满激情,富有生命张力。然而,到了《一地鸡毛》、《活着》出现的时期,一体化意识形态体系伴随一体化经济形态体系的瓦解而云散风流,文学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方面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家需要更多地直面普通人生存的艰辛,并开始趋向认同妥协的合理。于是,小林在现实生活的凡庸中抛却了当日的理想激情,专注于买豆腐带孩子收拾大白菜等日常生活琐事,对比《黑骏马》、《红高粱》等以理想主义对抗庸俗生活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自我丧失背后的是文学家话语权力的失落。《一地鸡毛》、《活着》等“新写实小说”所呈现出的主体失落表明,在90年代由于社会的转型与话语权力的易位,文学的启蒙话语的中心地位已经动摇,社会酝酿着新的价值选择。⑥
从《黑骏马》浪漫理想的青春激情,到《红高粱》至刚至烈的生命张力,代表了80年代生命阐释的刚性基本特征。从《一地鸡毛》对荒诞生存困境的无奈与绝望,到《活着》以苦难命运为友的生存策略,代表了90年代生命阐释的柔性基本特征。生存意义的文学阐释在刚柔两极之间的游走,折射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
作者简介:田卫平,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16页。
② 比利时《南方挑战》杂志对《许三观卖血记》的评价也适用于《活着》。载《许三观卖血记》,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封底。
③ 余华:《活着自序》(韩文版),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3页。
④⑤⑥ 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551页,第524页,第525页,第531页,第542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