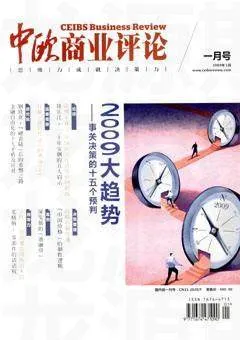生活中的宗教
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契约等,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私人关系。一种文化,如果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或者先讲关系、再讲原则,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种文化的未来是不足乐观的。
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中的宗教其实就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用则信,没用就不信,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什么东西最有用呢?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朋友”最有用。按照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秘密就是,中国人真正崇拜的从来就不是“文圣”,而是“武圣”——关公。为什么崇拜关公呢?其实就是崇拜关系,崇拜义气,小圈子里朋友之间的义气。但这种世俗的义气其实并不值得这么崇拜。道理很简单,小圈子里的义气的代价或者反面就是剥削圈外的人、掠夺圈外的人、虐待圈外的人。
好莱坞电影《完美陌生人》里的一句台词,把这点说得很清楚,主人公说,她的原则是personalloyalty(个人忠诚),因为这是law of universe(宇宙法则),对方不同意:是law of jungle(丛林法则)吧。把个人之间的忠诚当作一切的准则,最高的标准,这其实是人类最原始的做事方式,是丛林原则,但可惜,很多中国人崇拜的就是私人关系。
一个文明社会崇拜的应该是原则,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契约等,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私人关系。一种文化,如果只讲关系、不讲原则,或者先讲关系、再讲原则,老实说,就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种文化的未来是不足乐观的。
黄仁宇说:“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挟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很多人也都感慨中国人就像走兽,什么时候才能脱胎换骨、变成飞禽,好像一时看不到希望,包括一些最有见识的学者,比如钱颖一说,以中国现在的制度框架(广义的制度包括信仰和价值观),大概只能支持6000~7000美元的人均GDP,而现在沿海地区已经是七八千美元了(全国平均数低一些)。所以他这个话其实很沉痛,只是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出来。
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儒家、道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学术界一直在辩论。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儒教、道家的道理本身都不错,根本的问题在于一应用的时候用错了地方。秦晖沿用严复当年在《群己权界论》中对公域、私域的划分,强调公域要讲民主,私域要讲自由。
我们却全反过来了。应该用在公共领域、用来治理国家的清静无为(让民做主,让老百姓自己做主)的道家,反倒用到私人领域去了。汉初的黄老之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从此就成了千古绝唱。相反,应该用在私人领域的儒家的自我修养、自我实现、内向超越(积极自由),反倒用到公共领域去了。所以儒家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了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系统地洗脑和奴役被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们天天讲“修己安人”、“克己复札”,矛头对准的都是弱势群体,目的都是控制这ASIcJINBTDJg+0wFrJ/edWj4SODfH5Wg7GTsh5GQPYM=些被统治者,也就是所谓的“阳儒阴法”。
相反,道家却变成了疗养手段。做奴隶主,做奴隶都做累了——做奴隶连自由都没有,当然累;做奴隶主的、每天都要看着,别让这帮奴隶造反,也累;最累的是奴隶头子,又怕下面造反,又怕上面不高兴。大家都很累,累了怎么办?就要靠道家来做私下的疗养手段。什么吸纳术、炼丹术、性命双修、采阴补阳之类,都属于道家的疗养手段。尤其是那些靠科举制度上去的奴隶头子,所谓“阳儒阴道”,表面上讲文死谏、武死战,精忠报国,最在乎的,其实还是自己那身臭皮囊。这其实也就是南怀瑾所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的意思。但南怀瑾这样说是夸赞,他觉得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是好事咧。
相比而言,佛教是最博大精深的,但以管窥豹,挂一漏万地说,其精髓还在于一个“空”字,梁漱溟认为,印度文化的核心是取消,是一种向后看的、强调放弃的文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佛教中最中国化的禅宗的最大秘密之一在于“对时间的某种顿时的神秘的领悟”(李泽厚语)。总之,不要去试图把握世界,不要把握人生,而是把握瞬间,通过一刹那来勘破生死,超越因果,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放弃的哲学。
熊十力比较佛儒得失说,与孔子看见“生”相比,佛学只见到“灭”。梁启超说,佛说法50年,一言以蔽之,曰“无我”。虽然“无我”也可以解读为爱自然、爱他人、慈悲为怀,但我估计大多中国人还是把“无”当作了弃绝。当然也有入世的人间佛教,强调儒释互补,通过力行来改变周遭的世界,但总体而言,强调放弃的比例还是更大一些。
归根到底,宗教要解决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向问题和动力问题。解决了方向问题,才能保证大多数人走大道、中道和正道;解决了动力问题,才能让大多数人长亭接短亭,一手一手走下去,让整个社会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的儒家和道家,应该来讲,首先是没有把方向问题解决好。聪明、才智都不缺,可惜都用错了地方,把儒家用到公域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权谋和权力游戏,把道家用到私域的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种种得道成仙的幻想。方向问题没解决好,动力问题,更是提不上日程了。
个人以为,在动力问题上做得最好的应该还是宋明理学,不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主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气魄,也有“我心光明,亦复何言”的自信,更有“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然而,儒家这种所谓的“内向超越”是否能够普遍化为日复一日的庸常行为,化为包括贩夫走卒之类的昔罗大众“苟日新,日日新”,“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践行精神,实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龚鹏程老师在这里讲的儒家的社会与生活实践,从大的范围来讲,其实也属于这个问题。这里我们不可能展开讨论,但仅就儒释贯通的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的那一代大师的最终选择看来,最终的出路,应该还是在宋明理学基础上的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