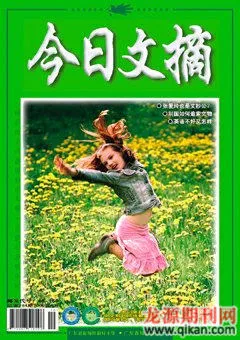当大师遭遇“诺贝尔奖”
对于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国人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特别是对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牵肠挂肚,爱恨交加。说起来也是,想我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从古到今,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漫长而辉煌;源远流长的文化艺术,丰富而深邃,却在这个满打满算仅仅只有107年的年轻奖项面前,颜面尽失。不但没有获得一亲芳泽的待遇,甚至连一次正式提名的机会也没有。也就是说,诺贝尔奖就像一个风骚却骄傲的公主,对一个充满激情和期待的老人,从来就没正眼瞧过。所以,每年一到诺贝尔奖揭晓之际,大家免不了就要热烈地议论一番,各种各样的声音就会甚嚣尘上,不绝于耳。诺贝尔奖,成了国人永远无法释怀的梦与痛。
其实,国人所期待的,也就是一种结果,一种能与国际接轨,并能得到青睐和认可的结果。事实上,与这种功利的期待相比较,我倒觉得,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最为重要,特别是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态度。
根据民间或者半官方的一些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相传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沈从文、老舍、巴金、林语堂、艾青、李敖、王蒙、北岛等人,坊间甚至还传出有王小波、余华、郭敬明等说辞,权当笑话吧。但在此之前,在中国文学诉求诺贝尔奖的路途中,最早被提及的当是鲁迅先生。他的经历着实让国人虚荣了一把,成为国人在诺贝尔奖前的一服强心剂。
1927年,瑞典一个叫斯文·赫定的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觉得这是件好事,于是托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的意见。这年9月25日,鲁迅便郑重地给台静农回了一封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这封信,写得极好。这封信里,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以及上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初二三十年的文学现状,他都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应该说,他的这种认知和态度,是中国作家对待诺贝尔奖的一种最理性、最正确的态度。他既没有着意轻蔑诺贝尔奖的矫情,也没有刻意抬高诺贝尔奖的心思。当时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却清醒地觉得自己还“不配”、“还欠努力”。
这段史实,有段时期曾被人演绎成另外一个版本,说瑞典文学院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奖,鲁迅则表示不接受。这一说法,如果是出于无知,倒也罢了,倘若是因为自大心理作祟,自编自导出这么出滑稽戏,除了用以自慰外,只能让外人笑掉大牙了。因为谁都知道,提名和获奖,根本就不是一档子事儿,何况还是个“拟提名”。
无独有偶。与鲁迅先生处在同一时期的大学者胡适先生,也曾被拟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巧的是,热心操办这事的,仍是那位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据《胡适日记全集》中记载,那是1929年2月26到28日,胡适当时乘火车从外地返回上海,事情就发生在火车上。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火车上熟人最多,有美国公使,有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有陈万里、杨宪武等。斯文·赫定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金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
这话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当时诺贝尔奖的提名,还须具备相当的身份。例如斯文·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其次,中国文艺的对外传播还不够。尽管有了具备一定条件的作家,但翻译不行。所以斯文·赫定提出要胡适把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
胡适当时是如何口头回答这个热心的瑞典人的,这不得而知,也无从考证,但他的意思从日记里看,还是表达得很清楚的:
“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这段话表达了几层意思。首先他认为自己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是“有功”之臣,甚至因此而提名选举也“不推辞”;再,为了获个什么奖,而自己来翻译自己的东西,不干。那实在不符合当时中国文人的自尊和体面。所以胡适用了“没那厚脸皮”这样俗而重的字眼。第三、胡适自认“不配称文学家”。在他看来,“文学奖”主要是授给那些文学创作者,而他自己,主要功绩是在“提倡文学革命”方面。适之先生不愧是做学问的大家,理性、克制且自重,在诺贝尔文学奖面前,他所表现出的热情,远比其对政治所表现出的热情来得理智,因而并没有头脑一热,干出赤膊上阵一搏诺贝尔文学奖的傻事来。
瑞典人斯文·赫定一再提名中国人去争诺贝尔文学奖,其真正的动机何在,我们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人的态度还是友善的,对中国文学还是有感觉的。这点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两位中国先贤在诺贝尔奖面前的态度。面对世界性荣誉的诱惑,他们分别用了“不配”,“不配称”这样的字眼,除了表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敬重外,还表现出了一种文人的自省、自知和自重,其谦抑、恭敬、理智的态度实在令人起敬。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被外界称为“大师”、“大家”的业界权威或者名流人士,当有人明里或暗里在你耳边唠叨,怂恿你接受什么诺贝尔奖提名时,在表态之前,不妨先想想鲁迅和胡适这两位大师当年说过的话。■
(张金山荐自《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