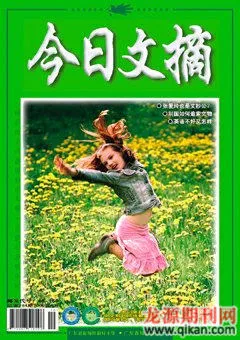知青过节
生活过八年的黑龙江给我留下寒冷的记忆,那是没有办法的,气候已经浸润心灵深处。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梦见自己回到积雪的深山老林,风声、飞雪与苍茫大地都成了真实,惊醒过来后,好半天都以为眼下的现实却是虚幻。
知青生活还有一个强烈的记忆就是过节,漂泊在外,对节日特别敏感。
刚去的第一年,过春节像小孩过家家似的热闹,大年三十,伙房里做了熘肉段,炒粉条,山蘑炖鸡。大家把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东西全集中在一起,上海知青有鱼松,炒米粉,牛肉干,温州知青有腌带鱼,米粉,虾干,再搭配着各地的吃法,变出了18道菜。可是壮观的宴席一过,就听见齐齐的哭声,都是17岁,初次在外过年,心里空空的,倍加想念亲人。
后来,大都选择在过年的时候回家探亲,几乎都是年关从深山里出来,在哈尔滨换车。很怀念哈尔滨的霁虹桥,它离火车站不远,在积雪的冬天,我眼里的它有雪国的美与矜持。我喜欢看刚买了新皮靴的人,手里拎着年货从桥上走过。我向往有足够的钱买一双新皮靴,把家人接过来,逗留在此过一次北国的春节,不必风雪兼程了。
今年我陪着母亲到了哈尔滨,可是已经没有了父亲。我们穿过霁虹桥,在不远处有法院的那条街上晚餐,老百姓把那条街俗称为杀人街,没有恶意,只是直白。用餐的地方叫农家大院,是怀旧的主题。可是我的怀旧无法深邃,因为事过境迁,努力去够也不能够到,即使想体验当年的落魄,也已成奢侈。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把探亲假用掉了,春节得在林场度过,当时我已是学校的老师,从一年级能教到六年级。学校里没有心理老师,学生叛逆,也分不清是心理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还是道德问题,混合在一起了。在那春节的闲暇时段,我和学生们在一起,倾听他们的诉说,教他们学风琴,他们手指灵活,兴高采烈。我们一起捉迷藏,朗读,扮演课文里的角色,那个春节过得淳朴与可爱。
已婚的老知青比我们过得好些,所以什么正月十五,什么三月三龙抬头都招呼我们去打牙祭,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常常是做一摞油饼,炒上土豆丝,炖小鸡,当场去院子里活杀做菜。我也会亮一手,做上一道用茶叶烧烤的熏鸡腿。那是我们共同体悯着,在异思乡酿成的病。
知青生活的物质是匮乏的,每人一个月只有一斤大米,九斤白面,其余都是杂粮。可是也想为家里置办些什么,有一年年底,我跟着同事去齐齐哈尔,它最有名的叫法是卜奎驿站,我在那里买到了黄豆和葵花籽,飞一般跑邮局,想在元旦前夕寄到。牙齿黄黄的邮寄员说:“往家寄呢?真不易呀。”
当时那忧伤的思乡其实也是活下去的支柱。佳节将至,我想象着母亲在包裹领取单上敲上蘸了鲜红的印泥的图章,心里充满暖意,对亲人好总有最愉悦的感觉。
母亲也想念我,家里吃饭桌的玻璃板下面就放着我的照片,母亲做了好吃的就难过我不在场。得到我快回家过年的讯息后,她用悄悄攒起的肉票买回一整条的猪腿,规划着,最好的部位作成香肠、酱油肉,节后让我带走,还留一些全家过节的佳肴。父亲调侃母亲的节省,给我写信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都成为面条大王了。”
父亲来知青点看过我一次,我说我们很好,不提饥饿和疾病和孤寂。父亲安心地走了,什么也没有说。直到他去世了,老干部处的女士才告诉我一个秘密,父亲说他当时难过了好几年,心里一直堵着。
有个漂亮的女知青在年根的时候嫁给一个满洲里的小伙子。那地方后来我去过,夜里很晚了,灯光还是亮如白昼。拍来的照片,视觉上很飘渺,天空穹庐似的,似乎云前还有薄纱,照出来是冰川一般。起初是好好的,她比别的知青都过得幸福,后来我们都可以返回故乡,才发现她被遗忘在那里。听说当年美丽的小姐姐,现在已是老妈妈了,有了孙子。
近三十年过去了,过节时候的孤寂已不再,过去的快乐情景会突然历历在目,心被缠得很柔软。岁月呀,过去了那么久。千万个走过来的知青,也许更能体会孤寂的滋味,领悟快乐的可贵?■
(王沛荐自《散文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