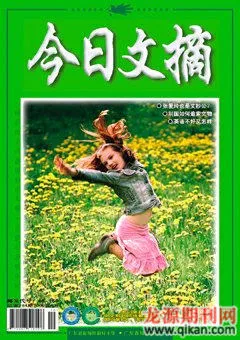张悦然:让走失的葵花重新盛开
1982年,张悦然出生于山东济南。和那个年代所有的独生子女一样,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有着一份天然的善感。对身边的人和物,她都有自己的表达意境和话语系统,而对于表达,她给自己造了一个词:嚣厌。喜欢沉默不语、低头走路的张悦然,在高中以前,给人的印象都是含蓄而内敛的。没有人能真正明白她心里在想什么,也没有人会知道,她心里的真实世界是怎样的。
一直蜷缩在个人世界里的张悦然是不太自信的,虽然皮肤白皙、个子高挑、家境富裕,但依然不能给她带来足够的自信和坦然。于是,张悦然一度将自己打扮得很出位,有时穿着红绿大花的裤子,有时穿上两只不同颜色的鞋,有时扎着无数条辫子,走在校园里,她永远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个。
2001年1月,正在念高三的张悦然获得了“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因此她成为全国很多重点大学争相力抢的保送生,反复考虑后,她选择了清华大学。有了这个保证,她就可以提前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了。然而,2001年4月,教委出台了一个新规定,除了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外,其他保送名额一律取消,这时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了。虽然她的学习底子很好,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却让她很受打击,平时就有点消极的她甚至在想,这是不是命运给自己的安排?几个月后,她考取了山东大学。
父母的关心和周围的议论,让张悦然意识到,自己每做一个选择,不仅决定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同时会影响到身边的人。作为一个80后,光有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担当的觉悟和勇气。正是有了这种思想上的飞跃,到山东大学报到后不久,张悦然就抓住机会,报考了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恶补各学科,她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系的录取通知书。
独自一人在新加坡求学,并没有想象中浪漫。很长一段时间,她内心强烈感觉到的是与环境的对峙。此时,写作对她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构想着一个个似真似幻的意境,认真地剖析着一个个属于自己的需要。几年间,她在年轻读者中形成了自己众多的拥趸。
2003年,张悦然在新加坡获第五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第二名。随后,她的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年,她的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图文书《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红鞋》及小说集《十爱》等相继出版。
2006年回国后,张悦然选择了定居北京。她继续写作,但是始终低调,不喜欢介入纷争。正因为远离了这个把80后作家炒作得热火朝天的环境,她一直保持着谦虚、真诚的本色。
在她看来,写作是一种天生的特质,而不是所谓天赋或才能的东西。个人性格里的特质,也许天生就容易忧伤的情绪特质,注定了她的写作风格,文字锋利、忧郁、奇妙、简洁、时尚而且到位。
担 当
2005年3月,印尼发生特大海啸。张悦然马上出发,去看望那里的灾民。就在她到达当天,正赶上印尼大地震。在安达曼海上,她和两个当地人蜷缩在一艘小船上漂流了整整一夜。在那漆黑且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突然生出这样一个念头: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人可以不在了,但属于这个人的记忆应该留下来。尽管她知道这样的故事很俗套,但因为她有那不同寻常的一夜,有迫切地要把记忆留下来的心愿,所以她还是选择了这个主题。
这次生死边缘的经历让张悦然思考了很多,也成为她尝试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开始写作《誓鸟》的灵感来源。2006年11月,《誓鸟》出版了。
张悦然的作品很快在青少年中引起极大关注,很多读者对她的作品连续发表了热情的评论。认为她的小说从少年的成长入笔,洞悉力极强,丝丝入扣地把少年成长中的困惑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读者把她推为最擅长描写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思想感情变化的女作家。
她希望探讨一些与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和这个年龄段的读者们分享、交换。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除了读书,他们应当还需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比如知道周围的人怎么想,知道自己的处境,解开内心的困惑等。她希望这个主题书系可以在这方面起一点作用。
“孤独”是80后的顽疾。这一点,张悦然并不否认,她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但她同时相信,这只是一个过程,走过去后,80后就会成为勇于担当的一代人。
盛 开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张悦然通过电视报纸得知灾区的情况,止不住地泪流满面。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她带着药品和食物,独自赶赴灾区。
乘飞机抵达成都后,坐汽车辗转到北川。由于路面毁坏严重,去北川县城的路,有一半是徒步前进的。路途中,张悦然认识了两位1984年出生的男孩马东和韩小平,得知他们要去寻找失踪的家人,他们三人一路同行。
沿途是一片废墟,人间烟火的气息已经完全熄灭。目睹这满目疮痍,张悦然心碎万分。她远远地看见官兵抬着担架从山上下来,担架上女人的脚是黑紫色的,已经局部腐烂,但尚有气息,女人的嘴唇张着,还保持着呼喊的口形。身上的红雪纺裙子原来应该很好看,染黄烫卷的头发那样长,也许曾令她骄傲。只是三天,却像过去了半生那样久,她的泪水顿时汩汩而出。
在搜救现场,官兵们疲倦地坐在尸体旁边,吃着饼干。韩小平跳到塌陷的废墟里寻找姐夫。他每天来一次,都没有收获。看到他垂头走回来时,张悦然总是默默走上前,递给他一瓶水。夜幕降临,天变得很冷,可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不再有黑夜和白天之分。
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痛彻心扉的痛苦,让张悦然的灵魂一次次受到冲击。回来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这场参与救援的经历,之于志愿者自己的意义,也许远远大于对外界的。这更像是一段自我洗涤、洁净灵魂的路途。当他们怀着奉献和担当的虔诚,在这条路途中忙碌着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正在抖落厚厚的尘埃,渐渐露出剔透晶莹的本质。某种善良的东西,宛如血小板,在灾难造成的伤口上,迅速聚集。善良本身,就是一种纯然、强大的力量。若它可以持久,可以累积,未尝不是灾难带来的一种馈赠。”
行走在灾区的每一分每一秒,她都握紧了自己的拳头。在一所小学的废墟前,面对满地的尸体,她泣不成声,表示愿意出资捐献一所希望小学……也许,她力量有限。可是,她告诉我们,只要你想,就可以做到。
从灾区回来后,有很多人采访她,问她是否会根据地震的题材进行创作。她断然回绝:“这种经历是一种积累,并不是以索取为目的的,更不是用以作为所谓的‘灵感’的。”
回来后的一天夜里,她突然想到了“孤独”这一主题,想想那些被压在废墟下的人,他们在等待救援的日子,是如何在孤独中坚持着,又是怀着怎样的信念等待着!为此,她决定推出以孤独为主题的主题书,当然,读者仍然是定位于80后的年轻读者,直面他们内心的孤独灵魂。
慢一些,快乐写作,是作家张悦然的理性思考。她的第一部书《葵花走失在1890》,描写的是走失,而渐渐成长的她,却开始让走失的葵花归来,重新盛开。■
(刘杰锋荐自《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