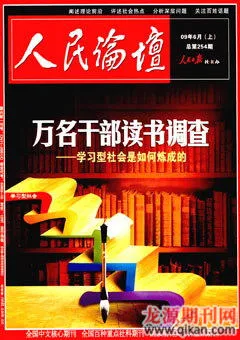“公共管理模式”的中国变革
编者的话
我国公共管理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哪些不同?如何针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模式?为此,本期“中国模式与新理论”栏目,人民论坛杂志社邀请国家行政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3位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特邀嘉宾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刘熙瑞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 任进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刘金程
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
刘熙瑞
群众不但参加选举,还要参加管理;不但有间接民主,还要有直接民主:不但有政治民主,还要有经济民主。这样的公共管理体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体制。
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关注中国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尤其有重要意义。这个理论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起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它的人性假设,其次是它对人民群众作用的看法,再次则是如何处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把握这些,无从了解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真谛。
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组织作用的根源,是我们政府保持对社会较大调控力的依据
从人性假设上说,我们并不赞成简单的“经济人假设”。我们知道,西方很多学者,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派的学者,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和基础的。他们认为,人都是自私的“理性”人,知道怎样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制度就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利益奋斗,“只要每个人都为自己了,客观上就是为社会了”。这实际上信奉的仍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这里也有尊重个人权利、最大限度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好处,但这种建立在绝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基础上的“动IA8SSe8cwOokz6ouTM44gg==物”法则,搬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它显然会有很大的弊病。由撒切尔主义发展来的所谓“新公共管理”思潮,无疑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很深的踪迹。而“华盛顿共识”就是其集中表现。
在人性假设上,我们则强调“后天环境决定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如果硬要表述现实中的所谓“人性”的话,那么我们则认为它除了有动物性中自私的一面以外,同时也还有人的社会性一面,而社会性可能更是人的基本存在。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无论如何是社会的动物”可为此做注脚。这一点,达尔文本人也是一直强调的。他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曾反复讨论,人除了在自然选择中有个体的进化外,更主要的还有物种间竞争导致的“种”的进化。他曾讨论,人在与许多动物相比中有明显的弱点,但这些弱点也许正是他的最大财产,因为正是这些弱点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合作关系”,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形成——这是使人能适应和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他在研究人类的社会道德时也强调,正是这种“合作关系”构成了人类的“社会本能”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道德观念”。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特别强调的。因为正是这一点,否定了西方某些人的理论基础,从而也否定了由这理论导致的某些社会制度。有人漠视达尔文的上述思想,不仅是对达尔文的否定,也是对历史事实的背叛。对于我们,则决定了我们对人类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的肯定,对社会和社会各个系统总体效益的追求,以及对人的组织观念和社会组织力的倍加重视。这正是我们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府组织作用的根源,是我们政府保持对社会较大调控力的依据,也构成了我们中国公共管理有别于西方某些国家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与此有关的是如何评价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和社会的主人。这是因为,首先,他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构成了一切社会的现实基础;其次,凡是社会的每次变革,都是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原来的秩序而实现的;再次,任何新的生产方式,也都是因为他们以最大实践者身份提供了素材和生产力基础,才推动和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一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战争年代如此,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我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其内涵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七大确立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同样基于这样的考虑。
我们信奉的是人民权利的彻底实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与政府想的,就是群众想的,群众的要求和目的,就是党和政府的要求和目的
西方许多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以人民作根本”的概念,也不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当然他们讲民主,但在给人民政治权力的同时,也特别强调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讲以“资”为本。所以他们推崇代议制,“代”人民来“议”,而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的“代表制”。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生产考虑到了分配,其中也包含了所有制因素。这样从根本上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与西方某些国家的公共管理自然有不同。
最后则是如何处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认识。某些西方理论家出于“政府是必要的恶”的判断,在不信任政府的同时,强调公民自治,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公民社会各组织间通过利益博弈而达成共赢。所以在他们眼里,最理想的状态是共同治理,是“善治”,是政府能最大限度地“回应”并促成与社会的“合作”。这实际上是“两元”或“多元”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我们国家的代表制理论,讲一元、和谐、融和不同。
当然他们要造成的回应与合作局面,比起我们过去的高度集权体制、有政府无社会状态,肯定要好得多,应该说也是前进了的。但作为理想状态,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信奉的是人民权利的彻底实现,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与政府想的,就是群众想的,群众的要求和目的,就是党和政府的要求和目的。两者达到高度的统一,这就叫“融和主义”。因此,群众不但参加选举,还要参加管理,包括决策、执行、监督、救济;不但有间接民主,还要有直接民主;不但有政治民主,还要有经济民主。这样的公共管理体制,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