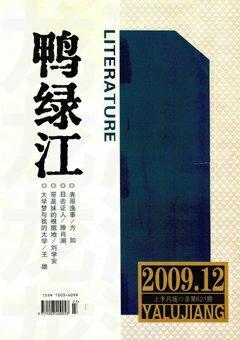诗歌本
王 往
王往,江苏淮安人,1969年9月生。江苏省作协会员。曾做编辑工作十年。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余篇。中篇小说《岁月刻刀》获《作品》杂志“金小说”全国征文二等奖,《雨花狐》获江苏省首届吴承恩文学艺术奖二等奖,《底层是一车煤》获 《扬子江诗刊》全国“民生之歌”诗歌大赛二等奖。现为江苏省淮安市文学艺术院专职作家。
父亲的一生是一本辛酸的诗集。
那天下午,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病倒了,催我们兄弟马上回去。
我和大哥赶到家里时,父亲躺在床上,闭着眼,呼吸时轻时重。他的颧骨凸起得很高,顶着苍黄的皮肤,腮帮陷了下去,灰白的胡须了无生机,让人难过而又慌张。上个月我回家时,他还精神十足的呀。
母亲说,昨天傍晚,他去学校后面的河坡上闲逛,遭了一场雨,回家后饭也没吃,就上床睡觉了。夜里,开始发抖,又咳又喘,我说快上医院,他说不去不去没什么,今天早上和中午都没吃下饭,咳也加重了喘也加重了,我害怕了……
大哥问母亲,前些日子有没有什么反常?
母亲说,也咳也喘,不过没这么厉害,饭也没少吃。
那时候就应该叫我们回来嘛。大哥说。
唉——母亲叹气,着急地说,我是说叫你们回来的呀,他死活不让,说孩子都忙,回来做什么,该叫他们回来时你再叫也不迟。
父亲醒来以后,先是咳嗽,拼命地吐痰却吐不出来,挣扎出两行泪水,然后又大口大口喘气。
我们兄弟当即决定送他去医院。
父亲一手扶着床沿一手揩着泪说,柏园,竹园,我不去医院了,去了也没用,我和你们说实话,十几天前我自己去查了,是肺癌晚期。
我们兄弟都惊呆了,对视一下,眼里都冒出泪水。
大哥说,爸,不管是什么病,一定要去住院。
父亲捂着胸口,低下头,轻轻摇摇。
爸,一定要去医院。我说,不能再拖下去了。
父亲还是摇头,接着又咳嗽起来。
母亲赶紧去给他捶背。母亲说,他爸,就是为了孩子一片心,你也要去医院啊。
父亲住进了医院,我们这才知道,父亲确实来查过。给他复查一下,也确实是肺癌晚期。所谓治疗,只能是用些药物缓解痛苦,延长生命了。
父亲才六十岁啊。
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就……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抽时间多陪他老人家了。
那天下班后,我去了父亲的病房,父亲正拥被坐着,半眯着眼,嘴唇无声地动着,像在默念着什么。
我看他精神还不错,就问他,爸,想什么呢?
父亲笑笑,摇摇头说没想什么。
邻床的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接过话说,你爸吟诗呢。
老先生说着递给我一张横格纸,说,看看,你爸写的。
父亲赶忙摆手,我瞎画两句,弄着玩的,别让孩子笑话,我家竹园是作家呢。
老先生说,那就更应该给他看了,自己孩子,你还怕他笑话呀。
我一边伸手接纸,一边说,我爸年轻时就喜欢写诗呢。
父亲咳嗽着,脸上带着笑,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父亲的字很大,结构也松散,歪歪扭扭的。那纸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黄昏时分归学童,你追我赶闹哄哄。
谁知老人心中事,独对斜阳听晚钟。
我不懂古体诗,说不出好坏来,但不管写得好不好,只要他愿意写,写了心情好,我就要支持他。我说,爸,你想写就写,开心就好,等会儿我去给你买个笔记本。
父亲嘿嘿一笑,我哪会写,瞎画的。
老先生接过话说,你瞎画谁又不是瞎画?老先生又对我说,我也爱瞎画,我们是文友呢。
父亲对老先生说,你是教师,我哪能和你比。
父亲年轻时是个文学爱好者。在大集体时,他就常给广播电台写新闻稿,写朗诵诗。只要有空闲,他的笔就不停,就像他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白天挥着牛鞭子,晚上摸起笔杆子。为了歌唱新生活,决心写诗一辈子。他只有小学文化,却是全大队公认的有文化的人。过年时,请他写对联的人从我们家屋里排到屋外。平时,乡亲们的书信几乎是他一个人代笔。有个叫三妹的姑娘谈了一个当兵的对象,当兵的对象当了军官后,不想再和三妹好了,父亲以三妹的口气连写了三封信,到底打动了他的心。三妹结婚时,送了父亲一篮子礼物。母亲读书比父亲多,初中毕业,而且很漂亮,但是母亲偏偏爱上了父亲。农村分田到户以后,不用天天忙田里的事,父亲写作的劲头更足了。他在诗中写道:分田到户家家忙,自种自收意气扬。更有诗人得闲情,大槐树下做文章。
父亲写好诗,喜欢念给母亲听。念完了长长舒口气,然后,仰起头,一手卡腰,很深沉很有理想的样子,好像在构思下一首诗。其实,他是在等母亲夸奖。他不时地侧脸瞄一眼母亲,脸上带着得意,眼里带着期盼。我记得,母亲是夸奖过父亲的。母亲夸父亲的诗,总是两个字:押韵。母亲说,星南,押韵呢。母亲对诗的好坏的评价就是押韵不押韵。但这两个字的评价也让父亲眉飞色舞,有时他重重地点点头,鼻子里响出一声“哼”,我的诗会不押韵?有时拖长声音,模仿戏剧里的腔调说,谢谢夫人夸奖。母亲鼓励他:你不是要投到报社去的吗,快投去呀。父亲说,当然要投,一定要上《楚阳报》。楚阳报是我们县的报纸。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时父亲的视野是多么狭窄,《楚阳报》在他眼里是最重要的报纸,他知道的报纸也只有《人民日报》和《楚阳报》,至于杂志,他一本没看过。《人民日报》对他是高不可攀,《楚阳报》对他来说就是文学的惟一阵地。父亲给《楚阳报》投过几次稿,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母亲对父亲的支持,让父亲的诗情燃烧不止。看着父亲好学上进,母亲眼里流露出幸福。她常常在夸奖父亲以后,趁我们小孩不注意,噘起嘴,使个好看的眼色,拍他一下屁股,或者揪他一下腮帮子,说一声“看你得意的”,就去田里干活了。
我们没想到父母后来会变得水火不相融。他们争吵的原因竟然是母亲反对父亲写诗。母亲说,分田到户几年了,村里人的生活一年一个样,一年比一年好,我们家呢,也就能填饱肚子罢了,有时零花钱还像大集体时一样,从鸡屁股里抠。母亲说的不错,那时村里已经有了很多“第一”:谷老四家兄弟俩去东北做瓦匠活儿,买了全村第一台电视机,杨钱生家贩木材买了全村第一辆拖拉机,陈贵龙家炸馓子卖盖起了全村第一座楼房,杨大拿家更不得了,育鱼苗赚了钱又办起了全村第一个饲料厂……别的人家虽然没发大财,但过得也有滋有味的。母亲说,人家都把空闲时间用起来苦钱,你爸倒好,在家写诗。
开始,母亲也是好好劝父亲的。母亲端个小凳子,坐到伏案而作的父亲身边,吹吹他落在桌上的烟灰,说,他爸,三个孩子都读书,全靠地里的收入不行啊,粮食不值钱的,你想办法苦点钱。我在家多吃点苦头,等到日子好过了,你再写东西吧。父亲皱着眉,两眼闭起来,好一会儿才说话,我晓得呢,你先去做事吧。过了十多天,母亲发现父亲还是老样子,就发火了,母亲说,你要是再写,我就把你的本子烧了。父亲一拍桌子:你敢!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母亲不怕他。母亲说,我懂,你那不是诗,是死尸!你写了多少年呢,报上见过一个字吗?父亲踢飞了小凳子,冲出门去,扭头丢下一句话:我就不信上不了《楚阳报》!
那一次争吵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在《楚阳报》上发了一首诗,他先把信封在母亲面前晃晃,指着信封上自己的名字说,汪——星——南——同——志——收!然后又指着信封右下角念道,楚阳报!母亲很不在乎地说,什么宝贝东西!父亲抽出报纸,小心地打开后,铺在桌子上,叫母亲,你来看!母亲走过去,父亲指着第三版的名字说,这叫副刊,这个副刊叫桃花岛,呶,我的诗,《春到人间》,汪星南,看到没?谁知母亲一点没感兴趣,一把扯坏了报纸。父亲伸手去夺,母亲扔在了地上。父亲赶忙拾起。母亲说,我晓得怎么回事,你是不是送给人家编辑一篮子鸡蛋还有几斤黄豆?父亲的脸涨红了,两眼睁得大大的,泪水任性地住下淌。母亲“哼”了一声,看你那样子,还委屈了你?我告诉你,汪星南,你赶忙想办法苦钱,写什么我都不稀罕。母亲走开了,父亲把报纸拼了起来,看着看着,伏在桌上哭了:这是我的处女作啊,我的处女作啊……
父亲不顾母亲反对,继续写。他很固执。不过,用父亲的话说,叫坚韧不拔。有时,他实在孤独了就对我们小孩子诉苦。父亲说,诗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知道么?我们不知道,摇头。父亲说,我现在没钱,没人看得起,我不怕,你们要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诗人。
大姐菊园问他,爸,为什么要成为诗人呀?
父亲想了想,手一挥又往下一压说,这个嘛,因为诗人是高贵的,很高贵很了不起……大姐菊园说,那我们为什么没有钱呢?妈老是和你吵架。父亲说,你妈什么也不懂,写诗不是为了钱。大姐又问,那为了什么呀?父亲又想了想说,为了……为了一种追求,诗,就是我的追求,你们长大就明白了。大姐还是一脸疑问。父亲的眼里好像也有疑问,手在胡茬子上磨来磨去,好久不说话。
长大以后,大哥柏园曾经和我谈过父亲的诗。大哥说,我爸的诗嘛,说难听一点,就是顺口溜,打油诗,幸亏他后来不写了,要是写一辈子那样的诗,才叫笑话呢。我说,那也不一定,后来他不是接触了外界一些诗人吗,如果有名家指点一下,或许会写好呢。大哥说,恐怕难哪,他基础太差了。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住父亲对诗歌的热情,就像他和母亲吵架时说的那样:我不会放下手中的笔。
我们本乡有一个农民,叫徐烈,在《诗刊》上发过一首短诗。他拿着这首诗找到县文教局领导,请求领导给他一个民办教师的位置。县文教局领导爱才,还真同意了,让他到黑鱼湖农场去教语文。父亲很是佩服徐烈,带上作品去请教。黑鱼湖农场离我们乡有六十里,每到周六下午,父亲就骑上自行车去了。父亲说他和徐烈彻夜长谈,徐烈对他悉心指点,大有启发。
从徐烈处回来时,父亲走路都和平时不一样了,腰挺得直直的,目不斜视,见了村里人爱理不理的。父亲说,他们懂什么,他们知道北岛、顾城吗?
父亲见了徐烈后,自己也跟着有了名气,本乡的文友都爱来找他谈文学,除了写诗的,还有写散文的写小说的。那时候像我父亲这样爱好文学的人太多了。据说,有一回市里的诗人曹不语来我们乡讲课,周围几个乡的文学青年都赶来了,县城的文学青年也来了不少。曹不语先是打算在文化站里讲,看人太多了,就改去电影院,但是电影院也没容得下,蜂拥而至的文学青年把电影院的大门都挤坏了。父亲和文友们常常聊到深夜才回家。母亲不给他开门,任他怎么拍都不开。一般是我大姐菊园被吵醒了去开门。天亮了,我们都起来了,母亲开始骂他,催他起来做农活,父亲一声不吭。母亲骂道,难道你死了吗?父亲说,没死,诗人的心不死!到了晚年,母亲和我们讲起当时的情景,笑个不停。母亲说,那时他就像疯子,你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父亲和外界接触后,知道了更多的文学报刊,他开始大量投稿。那时候,邮票是二角钱一枚,就这二角钱父亲往往拿不出来。母亲说话很刻薄。母亲说,你那些诗稿给人家擦屁股人家都嫌硬,你不要投了,你快给我想办法苦钱。父亲说,你不要瞧不起我,总有一天我叫你刮目相看。母亲说,你就是上了天我也不稀罕。母亲开始控制家里的经济,卖粮卖鸡卖鸭都是自己上集市。父亲买一盒烟也要向母亲伸手。有一段时间,父亲不吸烟了,把烟钱换成了邮票。父亲不吸烟是很难受的,烟瘾来时,眼泪直往下掉。母亲心软了,叫我去给他买了一盒烟。父亲猛吸了一口,烟就只剩下半截了。母亲趁机开导他,你都三十一二岁的人了,日子过成这样,你好意思吗?我都说了,日子好起来了,你再写诗,偏不听。哪知父亲吸了几口烟,诗情一下子涌上来了,摸过纸笔就写。
有一天,母亲说我舅舅生了小孩,要去喝喜酒,打算买一双新凉鞋。母亲一摸钱,准备好的几块钱没有了。母亲找钱的时候,发现了几本新杂志。她晓得是怎么回事了,先是拿起杂志砸在父亲头上,然后脱下旧凉鞋又朝父亲砸去。我跟着你过什么日子呀。母亲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我们家围了好多人。母亲边哭边说,你偷我的钱呀,我一双鞋子都买不起,你叫我怎么见人呀。父亲躲在屋里不出来。母亲说,你出来呀,出来让人家看看你那张脸,看你丢不丢人……母亲回娘家后,几天都没回家。大姐菊园叫父亲劝母亲回来,父亲说,她不在,我清静。菊园说,都怪你,你是个疯子。父亲冷笑道,我是疯子。菊园便自己去叫母亲了。
父亲站在门前,两眼空空地看着远处,自言自语道,我贫穷,孤独,没有爱情……父亲的表情让看到他的人发笑,人们把他当作一个怪物。
母亲从娘家回来后,看到父亲还在写诗,母亲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扛起锄头下地了。父亲对我笑笑说,她想扑灭我心中诗的火焰,没那么容易。我不明白诗为什么有火焰,只是觉得父亲的话听起来很有趣,和常人不一样。
我们谁也没想到父亲会突然不写诗了。
说起来很叫人伤心,父亲不写诗是在我大姐菊园死后。
那年夏天,一个晚上,吃晚饭了,大姐菊园还没回来,父母亲从学校找到她几个要好的同学家,都没有影子。最后,是一个用手电照鱼的人在学校后的河坡上发现了她。她死了。开始大家以为是被人害了。父亲赶来后,扑在菊园身上大哭,是我害死了她,是我害死了她呀!父亲说,中午时候,菊园跟他要学费,他说没有,菊园说人家都交了,自己没脸上学了,不想活了。父亲没理她。菊园就说,你不给我学费,死给你看。父亲说,你死去吧……他说我哪知道她真的会寻死呀,父亲狠命地捶着胸口,又揪着头发把头往地上撞。
大姐菊园死的时候不满十三岁,读初一,下学期刚开学。她死后大约半个月,父亲和母亲说,我出去打工了,两个孩子交给你了。母亲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冷冷地说,你早该出去了……
父亲打工后,我们家的日子逐渐好了,两间草屋翻成了四间大瓦房,装了电灯电话,买了电视机。当然,他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兄弟完成了学业。大哥柏园和我先后考上了大学。
大哥工作以后,劝父亲不要打工了,父亲说不打工做什么,我身子骨很好呢。大哥开玩笑说,在家陪陪我妈,没事写点小诗嘛。父亲连连摆手,写什么诗呀,哪能和你们比?
大哥柏园从高中时就爱写诗了,发表了不少。母亲劝他不要为了写诗误了功课,父亲却很赞成。父亲看着柏园的诗,一脸羡慕,问,真是你写的?大哥说,不是我写的还会是抄的?父亲就“啧啧”咂嘴,那样子简直有点妒忌了。背地里,父亲却又对我说,你大哥那诗不好,东一句西一句,我看不懂,而且不押韵。我说现代诗不讲究押韵呢。父亲就挠着头说,不押韵还叫什么诗,见鬼,就他那诗也有人登出来。
大哥柏园毕业后在报社工作,一开始在副刊部他还写一些诗的,后来进了广告部,几年都没写一个字。我进了企业,业余时间倒喜欢写小说。我们兄弟接父母来城里住,父亲在大哥家住了两天就要到我家,父亲说,你大哥也不写东西了,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其实,父亲和我也没什么话,我的作品好在哪差在哪他也看不出来,一句不评价。他只是喜欢翻我写的那些文章。父亲看文章很有意思,他看几句,就摊开手掌在上面抚摸一下。我问父亲写得怎么样,父亲总是先说好啊,然后又说还没看完呢。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他要看一两天。看完了,我再问他好不好,他先说好啊,然后又说,要是诗就更好了。我说,诗,我写不好。父亲说,我随便说的,你只要写就好,写什么都比闲着好。
父母更多的时间是在老家,他们习惯村里的生活。母亲说,父亲不看电视,也不看书,也不打牌,就爱蹲着晒太阳,要么就是在村子外走一走,学生放学了,他就回来了。
我再次去医院看父亲的时候,发现他在笔记本上已经写了五十多首诗。邻床的老先生说,你爸一醒来就写,我不知道他哪有那么多诗,真是佩服。
有一天,大哥去看了父亲,见到我之后说,爸把一个笔记本都写满了诗,有三百多首,问他还要写吗,他说还要写三百多首呢,我就给他买了两个笔记本。
我说,爸在病中写诗这么快,真奇怪。
大哥说,我也奇怪,后来我看到其中一首诗才知道怎么回事。那首诗写的是:
年轻梦多爱写诗,写到鸡鸣晓星稀。
生活艰辛去奔忙,一首一首埋心底。
原来这么多年,父亲一直在心底写诗!我几乎哭了。
大哥的眼圈红红的。大哥说,我有个想法,给父亲这些诗出一本诗集,我们买书号。
我说,对,帮爸出一本诗集。爸的诗除了错别字以外,我们一句都不要改。
大哥说,一句不改。
父亲昏迷了。他的诗集就放在他的床头。六百三十首,三百多页,厚厚一本。装帧很精美。邻床的老先生对我们兄弟说,你父亲不简单啊,他的诗全是他艰辛受苦的经历啊。老先生说着就背了一首:远离家园一千里,风雨赠我两行泪。打工苦打工累,好在有诗伴我睡。
现在,伴着他睡的是他自己的诗集。
父亲昏迷了二十多个小时才醒来,一醒来就问,菊园呢?我大女儿呢?
母亲说,你做梦了吧,菊园走了二十八年了。
父亲说,哦,是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了我看她还是十三岁。
爸,我们把您的诗出版了。大哥提醒他。
父亲看着诗集,没有打开,也没有触摸封面。他说,过两天你们带我去学校后的河坡上看看。
两天后的下午,父亲的精神好了一些,比平时多喝了半碗粥。父亲说,带我去看看菊园。
我们都感到了不祥之兆。
母亲说,他要去就带他去吧,这是了他心愿啊。
临走时,父亲看着诗集说,把它带上。
到了村小学后边的小河边,我们扶着他下了车,不知往哪走。父亲说,跟我走。
走着走着,父亲停下来了,指着土里露出的一小块石头说,菊园,我来看你了。
在我们老家,未成年人死后是不留坟不立碑的。这块小石头是父亲埋下的。
看着那小石块,我的心一阵痛,啊,姐姐,你要是活着,会是什么样子?这么些年,我几乎将你忘记了,我已经记不清你十三岁时的模样了。
父亲蹲下身去,叫我把诗集给他,又跟我要打火机。
父亲对着摇动的火光说,菊园,爸害了你啊,爸向你谢罪来了,爸再也不写诗了,爸把诗都烧了,你看看啊,都烧了。
母亲蹲在地上,抱着那块小石头哭。我和大哥也是双泪直流。
纸灰飘散着。父亲用小木棒拨着书,火焰就突然地蹿高了,几乎要烧着父亲的眉毛了,可是他像没有感觉似的,只顾不停重复着说,菊园,爸害了你啊,爸向你谢罪来了,爸再也不写诗了,爸把诗都烧了,你看看啊,都烧了。
我和大哥再也忍不住了,哭出声来。
母亲抬起头说,都别哭了,扶你爸起来。
我们扶起父亲,父亲的身子直抖。
大哥说,回医院吧。
父亲说,我不去医院了,我就住家里。
母亲说,住家里哪行呢?听孩子话。
父亲说,好,听你们的,回医院。但是你们再陪我一会儿,等学生放学了再走。
我们点点头,扶他坐下,围在他身边,静静地等那放晚学的钟声响起。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