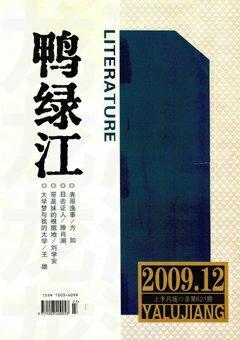逝去
毕 亮
毕亮,男,1981年生,湖南安乡县人,毕业于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现居深圳。已发表中、短篇小说五十余万字,散见于《天涯》《长城》《小说界》《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期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小说选本。为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级研讨班青年作家班学员,深圳市文联签约作家。曾获2008年度“长江文艺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我从麻城的学校回断崖岭当天,落了好几场雷阵雨。父亲的病愈加重了。整个寒假我窝在屋里,照顾父亲。
天气晴好的日子,擦黑时,岭上桃树林会传来唱山歌的声音:
阿妹山中来放牛,
唱首山歌逗一逗。
牛不抬头为吃草,
妹不抬头是害羞。
……
我就晓得是黄莺找我了。这是我俩约会的暗号。
脚踏暮色走出家门,我来到黄莺倚靠的那棵桃树下。约会时我俩总是手牵手,不讲太多话,在暮色洇散的桃树林散步。不久夜空里月亮升起来,月光下的黄莺,比我大学里的女同学显得羞涩。
高考落榜后黄莺就没再上学,她老觉得没上大学,矮我一等。但我不这么想,她善良、单纯……身上许多品质是旁人读再多的书也没法比的。念到大三了,每次暑假、寒假回屋,我就对黄莺说,等我大学毕业,咱俩就结婚!黄莺不作声。我就继续说,黄莺,你说行不行?黄莺盯着我看,埋下脑壳,冲我点两三下头。
春节大伯二伯三叔来到我屋里,从他们的闲聊中能听出来,断崖岭马上要搞旅游开发了。正月二十学校开学,我返回麻城学校不久,深圳的考察团就来到了断崖岭。
财神爷要来,村长乐坏了,不单村长,乡里乡亲也都乐透了。迎接贵客的腰鼓队练好了,十万响的鞭炮备齐了……可找谁接待考察团,这事让村长犯难,就他一个男人撑场面肯定不行。
村长抱紧臂膀站门口踅步,像场院里抱窝的母鸡。
太阳落山了,远处近处升起缕缕炊烟。村长踮起脚,视线跃过矮墙,目睹黄老汉拎个镢头迎面走来。他心里有了主意,赶紧跑步迎上前去。
先是递烟,再是点火。待黄老汉抽上了香烟,村长说,老黄,考察团要来了,借你屋闺女黄莺陪陪客人,就两三天!
黄老汉囔道,你家闺女才去陪客!
村长察觉话讲得不妥,补充说,是当导游!
黄老汉默声不答腔。
村长说,成不成,老黄你给句准话!
黄老汉瞥了眼暮色四合的天空,仍不答腔。
做着黄老汉的思想工作,他们并肩走到了黄老汉瓦屋门前的场院里。三四个挑箩筐、背篾篓看热闹的乡亲,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见黄老汉不回话,村长有些恼火,却又不能耍脾气。
思来想去村长只好利诱,他说,这事若成了,往后黄莺就是咱断崖岭的旅游形象代言人,月月给她发工资!
黄老汉眉角扬起来,笑了。他说,那好,村长你今天讲的话可要算数,在场的各位都是证人。黄老汉掏出裤兜里的香烟,给在场挑箩筐、背篾篓的乡亲各递了一支。边递烟他边说,大家伙可要为我作证!
黄莺眉目清秀,是断崖岭公认的美人。最了不得的是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唱起山歌比夜莺的声音还好听。接下来三天,黄莺陪考察团环绕着岭上的桃树林走了无数圈,又在青山绿水间穿梭,一路上山歌不断:
梧桐树上凤凰窝,
源浅河深龙降落。
凤凰想和龙王配,
一心展翅为阿哥。
……
带考察团参观时,黄莺察觉团里那个戴玳瑁眼镜的南方人对她抱有好感,时不时拿眼睛瞄她。到最后一天,南方人干脆直来直去,那双镜片下的眼睛摆在黄莺身上,不挪步子。
后来黄莺告诉我,南方人临行前夜,约她去岭上桃树林。她拒绝了。我晓得,黄莺的心在我身上,不会喜欢别人。
考察团走了,隔不久又来了。
这一次来,只有南方人一个人,他带来了配套开发方案,计划将断崖岭漫山遍野的桃树林改造成旅游景区,美其名曰——桃花源。
断崖岭的男人女人想着好日子就要到来时,黄莺站在三月黄昏的桃树下,远远地冲我挥手。一阵风吹过,粉色的花瓣顺风而落,落在她头上、肩上。一路紧跑,我双手叉腰站黄莺身旁呵粗气。
黄莺说,刘力,你才开学,咋又回了!
我说,我爸癌病恶化,怕是扛不过去了!
黄莺“哦”一声,我俩就沉默了,手牵手走在夕阳下。碰到路上有熟人,黄莺赶紧把手抽回去,羞红了脸。
断崖岭的乡亲,还没人晓得我和黄莺谈恋爱。我把黄莺送到屋门口,正转身要走,黄莺喊住我说,刘力,那个南方人来我家了,拎了一堆洋烟洋酒!天黑了,黄莺不安的眼神湮没在黑暗里。我的心思在生病的父亲身上,没察觉到黄莺话语里的不安。
熬了三天,父亲到底没能挺过去。
给父亲送葬时,路过桃树林,桃花花瓣在萧瑟的唢呐声中飘落。我发现黄莺站在人堆里,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那样子像是她的亲人过世了。看她那样,我心里挺难受也挺感动。父亲下葬后,单剩下我和母亲,一下屋里冷清了许多。母亲怕耽搁我学业,催我赶紧回麻城的学校。我在家又多呆了两天。临走前,我去父亲的坟头那里,站了老久,眼泪也流了老久。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情景出现在我眼前,躺在床上他吃力地挪动枯枝般的手,耷着眼皮,交代我往后照顾好母亲,别让母亲再受累……暖风把我的眼泪吹干了。
回学校时母亲送我,黄莺也来了。这时,母亲知道了我和黄莺处对象。母亲没多说话,独自走在前面,我和黄莺走在后面,隔二三十米远。黄莺交代我莫多想,人都有生老病死,家里母亲她会帮我照顾。后来我当着母亲的面牵黄莺的手,黄莺依了我,没把手抽开。我俩的关系算是在母亲那里公开了。
之后黄莺常打电话到我宿舍来,讲断崖岭旅游开发的事,讲考察团的南方人。后来她讲电话的语气变了,不再是一副局外人的口气。南方人想跟她结婚,她不同意,倒是独身拉扯她长大的父亲黄老汉希望她嫁给南方人,有个好归宿。偶尔母亲也打电话告诉我,黄莺经常去我家,帮忙挑水,干些力气活。她见我母亲眼睛不好,隔些日子就上卫生院买一盒眼药水,给我母亲点眼药。
断崖岭旅游开发紧锣密鼓地进行,南方人却变成了霜打的茄子,成天锁紧眉头,他没想到黄莺会拒绝他。求婚遭拒后,南方人多次表示,想离开断崖岭回深圳。
村长急坏了,一天临近吃夜饭时,他拎了两瓶陈年老酒“浏阳河”去黄莺屋里,去给黄莺做思想工作。
村长和黄老汉喝着酒,聊着天。
村长说,老黄,南方人要是真走,咱们这块风水宝地就开发不成了,断崖岭致富的门路就紧闭了。
这话村长不是讲给黄老汉听的,他是讲给旁边端瓷碗吃夜饭的黄莺听的。黄莺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当成耳旁风。
村长又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嫁这么好个人家,你闺女还不乐意?
黄老汉说,她是个猪脑壳!
村长说,老黄,你也莫骂她,黄莺是不是搞对象了?
黄老汉说,哪里有,没有!
抓起酒瓶,村长倒满了杯,端起酒杯说,没对象那就好办了,黄莺,我代表断崖岭的乡里乡亲敬你一杯酒,就算是给集体做贡献造福子孙后代,也是为你今后的幸福,嫁给南方人吧你!
黄莺说,我不嫁,您别喝。
村长不理黄莺,把一满杯白酒喝得干干净净。
黄莺说,喝了我也不嫁。瓷碗里的饭没吃完,哐当一声她撂下碗筷,躲进卧房,栓紧了房门。房外黄老汉挥拳不停地擂门,房内黄莺像只小兽缩在床头,嘤嘤地哭,就是不开门。后来黄老汉意识到快把自家的木门擂坏了,赶紧停了手,和村长一起站门口劝黄莺。天底下的好话讲尽,黄莺就是不顺从,不松口。
村长嘴巴讲干了,见黄莺吃秤砣铁了心,不再劝她,气呼呼地走了。半路上,村长觉得应该发动集体的力量,村里搞旅游开发不是他个人的事。走家串户,很快他把断崖岭上的乡亲发动起来了。
他们一群人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朝黄莺屋里走。黄老汉见到以村长为首的一群人堵在他家门口,慌了神,结巴着说,村……村长,你们想干啥子!
不晓得谁带来了鞭炮,点了一挂就放,劈啪响。待鞭炮声止了,村长说,大家伙是来给黄莺做工作,是来替南方人求婚!
黄老汉说,莫搞这大场面,不晓得实情的人,还以为我屋里哪个死了,你们赶紧散!
希冀往后的好日子,乡亲们不愿走。他们当中谁说,黄莺,嫁给南方人吧!声音传开了,形成和声,逐渐大起来。前面那人说的话变成了口号,震天响:黄莺,嫁给南方人吧!
黄莺坐卧房里,心里乱成一团麻。她还是不管不顾那些人,也不想跟南方人过好日子。
门口声音越来越大,屋顶上的瓦片都快震动了。黄老汉急了,他大着声音嚷,你们莫吼,我屋脊上的瓦片都快给你们狗日的吼碎了!黄老汉的声音就像一滴水落进大海,给更大的声音淹没了。他只好回堂屋,附在门边说,丫头,你就从了他们,嫁给南方人吧你!
打开门,黄莺走到屋檐下,门口震天响的声音瞬间消失。她望着门前黑压压一群人说,你们回家吧,我不会嫁给南方人!
黑压压的人群说,你不答应嫁给南方人,我们就不走!
黄莺说,不走,那你们就永远在门口站着吧!
然后她转身回了屋。
那些人真不走,站在门口,时间长站累了,有些人就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黄莺以为他们站累了就会走,可拖到半夜,他们还是没走。霜和露水打湿了他们的头发。黄莺心里不忍,只好打开窗户,冲着窗外喊,你们走吧,我答应你们,嫁给南方人 !
那些被霜和露水打湿了头发的乡亲,立马精神起来,他们说,你是说真的?
黄莺说,真的!
他们说,早些答应,我们早就回屋了!他们打着哈欠一个接一个摸黑走了。村长最后一个走,他朝黄莺的窗户说,黄莺,以后你会有好日子过,我们也托你的富,过好日子!
天麻麻亮,黄莺偷偷离开断崖岭,搭车来了麻城。
这一天落雷暴雨。黄莺联系上我时已是黄昏,她站在夜幕低垂的校门口,全身湿透,身子瑟瑟发抖。一见我,她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在学校旁边旅社开了房间,黄莺换了身干净衣服。我俩一起到小酒馆吃夜饭。
在小酒馆里,黄莺告诉了我断崖岭发生的一切。她望着面前桌上摆的西红柿蛋汤、茄子煲、红烧鳊鱼发愣。不久,她不安地望我,突然开口说,刘力,我们啥时结婚!
我说,再等一年多,等我把四年大学读完我们就结婚!
夜黑了,雨也停了,我牵起黄莺的手在校园遛了一圈。夜里我没回宿舍,我和黄莺呆在旅社的房里。熄了灯,我脱尽衣服,又把黄莺的衣服脱了。我和她紧抱一起。我那两只手直颤抖。黄莺也浑身打抖。
过去我只牵过黄莺的手,亲过她的嘴巴。现在抱着黄莺没穿衣服的身体,我就不是我了。我身体里闯进了一头兽。我也变成了一头兽,在黄莺身上撞来撞去……
恍惚间我眼前出现了断崖岭成片的桃树林。我闻到了桃花的芳香。
黑暗中我抱紧黄莺说,才刚我看到桃花了,你呢黄莺?
黄莺说,我啥也没看见,我下面疼!
黄莺又说,刘力,到时候你会娶我么?
我轻捏黄莺的手,说,这辈子我只娶你!
黄莺在我这里吃下定心丸,来天带着我的承诺回了断崖岭。
黄莺一回屋,乡亲们就嗅到了她的味,又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接成队伍来了。天上落起雾麻雨,他们顶着细雨,站在黄莺屋门口。黄老汉像赶苍蝇那样,挥手当扇子,他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接二连三堵我家门口,不晓得实情的人,还以为我屋里又有人死了,你们赶紧走!
有人说,你们家不是办丧事,是有喜事,南方人看上你家闺女,你屋里有福!
黄老汉说,你们谁有闺女谁去享这个福,我没这福分。
他们又开始喊口号了,黄莺,嫁给南方人吧你!
这次黄莺不把自己锁在房里了,很快她站在屋檐下,她说,你们莫劝我了,我已经是刘力的人了!
人堆里谁说,哪个是刘力?
黄莺说,就是刚放寿的刘国军的儿——刘力!
黄老汉在旁边急了,小声说,丫头,你给他了?
黄莺羞红了脸,默不作声。
黄老汉就晓得女儿吃了亏,铁青着脸,模样吓人。
那些人闻出了异样的味道,但还是说,没扯结婚证,就不算他的人!他们就开始嚷,走,我们就去找龙玉兰,让她劝劝她的儿,刘力他刚死了爸,我就不信他不听他妈妈的话!
他们吵嚷着走了,结伴去了龙玉兰那里,也就是我家。
后来我母亲在村长屋里打电话告诉我,那群人把她吓了一身汗。讲完母亲就开始哭,泪水把她那患了白内障的眼睛打湿了。
母亲从我小时候穿开裆裤一直讲到如何辛苦把我拉扯大上大学……听得我觉得不对劲。铺垫那么多话,终于母亲进入正题,她劝我,要我跟黄莺分手。
我不答应,我刚把黄莺身子拿来,就分手,那要遭天打雷劈的。我告诉了母亲这事,她就说,我也是没办法,你爸刚走,我也老了,一个人养不活这个家,村长答应还你爸生病时欠的账,以后村里还负担你的学费、我的养老费,只要旅游开发区建起来就好!
我还是没答应母亲。我说,妈,我不在屋里,黄莺又是给咱家挑水,又是给你买眼药,我不跟黄莺分手!
母亲在电话那边急了,喘起来,不停咳嗽。
想起父亲临终前交代的话,让我照顾好母亲,再别让母亲受累,我的心一下就软了。但我还是没答应母亲。
村长把我母亲带来了麻城,面对面给我做工作。
村长还带我母亲去麻城最好的医院检查眼睛,把母亲那只害了白内障的左眼睛治好了,付了三千多块手术费。
我的心又软了一次。
村长说,刘力,你爸不在了,你妈也老了,人老了病就来了,往后花钱的地方还多,到时我担保村里出医药费!
村长又说,就算你跟黄莺分手,又不是害她,以后她跟南方人一起回深圳,有吃有喝,指定比跟你在一起更好。你真心爱她的话,就该为她考虑!
我脑子一下空了。
等了半天,我说,我再想想!
村长说,这还用想!
我就崩溃了。
母亲从麻城回到断崖岭,黄莺再打电话来,我提出了分手。听到“分手”两个字,黄莺不再讲话,抱着话筒在那头哭。
黄莺又来了一次麻城,这次我躲了她。她在学校里转,我一直远远地跟在她身后。找我的那三天,她脸上的肉掉了好多,猛地人就瘦了,变小了一圈。我在心里不住地骂自己,骂自己猪狗不如。
黄莺在学校没找到我,就死了心回屋。她把魂丢在了麻城,回去她变了个人,不爱讲话,眼神里的光彩也像炊烟一样消失了。她爸黄老汉经常拎一把篾刀,站堂屋门口骂村长的娘、祖宗先人。这是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的。我猜黄莺他爸肯定连我也骂了,只是我母亲没直白地告诉我。
断崖岭的旅游开发区建成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桃花源”。
村长的努力没白费,断崖岭的经济真正好起来了。经乡亲们撮合,黄莺跟南方人谈起恋爱。他们隐瞒了我和黄莺的事,南方人不知情。
在黄莺和南方人处对象的日子里,黄莺成了断崖岭的“贵宾”。看到黄莺走在路上,隔得老远,乡亲们就打招呼,比对自己女儿还好还亲。
有天清早,黄老汉屋门口树杈上歇了两只乌鸦,看到后,他心里打起鼓。他想,屋里只怕要出事了。
晌午,南方人带着厚礼来到黄老汉屋里。燥热的天,知了聒噪地鸣叫,叫得黄老汉心里一团乱。南方人把厚礼搁在八仙桌上。黄老汉心里想,南方人来求亲了,他是不是在深圳有家室?
黄老汉说,你提这么重的礼,是不是想我把女儿嫁给你!
南方人矮下头,脸红了。
黄老汉见南方人的模样,觉得自己猜得八九不离十,就说,你是不是在深圳还有个家?
南方人说,没有。
黄老汉说,那你离婚了?
南方人说,没,我还没结婚。
于是黄老汉放心了,忘记了清早那两只歇在树杈上的乌鸦,忘记了屋外树上知了聒噪的叫声。他感觉到了穿堂风吹在身上的爽朗。黄老汉拍着南方人的肩膀说,那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你了!
南方人说,伯父,抱歉得很,我不是来求亲的,我对黄莺没感觉了,她像是变了个人,不是以前我认识的那个黄莺了!
黄老汉就急了,他说,我闺女都是你的人了,你今天说没感觉?
南方人又说了一声抱歉,从椅子上站起,扬起右手扶扶眼镜,急匆匆地走了。黄老汉急得直跺脚,在南方人身后喊,你回来,你把你这些东西给老子带走!
终究黄莺和南方人没走到一起。
黄莺跟南方人恋爱谈崩后,断崖岭的乡亲对黄莺的热情打了折。黄莺越来越沉默,经常坐在场院里发呆,昂起头目光空洞地望远方。偶尔,黄昏的时候,黄莺会唱一支山歌,调子变得凄楚,没有从前那般欢快了。
旅游搞活了经济,断崖岭卖给游客的假货却多起来。黄莺看不过眼,沉默多日的她找到村长,讲这样下去不行,迟早会出问题。她把读到的书现学现卖,讲了一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频繁出现的热词——“可持续发展”。
然后黄莺把卖假货的那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报给村长听。待她讲完,村长说,那你说咋办?
黄莺说,反正我们不能只顾眼前做一锤子买卖,不能卖假货坑人家游客!
村长说,那我去说说。
黄莺走后,村长挨家挨户去打招呼。利字当头,村长讲话并不起作用,他们完全把村长的话当成耳旁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卖假货坑游客成风了。任黄莺怎么讲卖假货的害处,村长都只是无奈地摆手、摇头,他也没办法。村长老婆开的铺子也照样卖假货。
那些开铺子的乡亲嫌黄莺多嘴管闲事,从前遇到还打声招呼,问个好,现在倒好,黄莺挡他们的财路,他们见到黄莺就像躲瘟神,不理不睬,当她是透明人。
不到一年时间,黄莺在断崖岭的待遇从天上掉到地下,甚至变成了后娘养的闺女。那些人联合起来,孤立黄莺。可黄莺仍要管闲事。有天夜里,黄莺父亲黄老汉走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人用蛇皮袋罩头,揍了一顿。伤得倒是不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为了警告黄老汉的女儿黄莺。黄莺趴在黄老汉的病床前,哭成了泪人。黄老汉也不讲话,默默地淌泪。后来,黄莺不管闲事了,整天郁郁寡欢。她山歌也不唱了,话也不多讲了,成了个忧心忡忡、眼神空茫的“哑巴”。
……
大学毕业前,我仅回过一趟断崖岭,听说了许多关于黄莺的事。那个星空灿烂的夜里,岭上桃树林传来唱山歌的声音。我仿佛又听到了黄莺的召唤。我出了家门,去找黄莺,半路上我打起退堂鼓,转身回了屋。一路上,我流了满脸泪水。我没有勇气面对桃树下的黄莺。
毕业后我留在麻城工作,娶妻生子,把母亲也接来麻城跟我一起生活。之后好些年我没再回断崖岭,不敢回,害怕见到黄莺。母亲知道我心里的结,她也小心翼翼地避开,不去触碰它。
又一年,清明节前,母亲说梦到我父亲了,想回去看看,给父亲扫墓。我在单位请了假,陪母亲一起返乡。
断崖岭变得面貌全非,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而惟一不变的,是风景,是漫山遍野的桃花。我和母亲来到一家小卖店前,购买纸钱、鞭炮、香火,老板是一位瘸腿中年男人,讲话带河南口音。我正付账时,店里头跑来一个嘴角边沾满米饭的邋遢的小女孩,身后跟着个端着饭碗的中年女人。
我抬头看时,她也看到了我。
是黄莺,我不敢认她。现在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去眉目清秀的她整张脸变得粗糙不堪,眼神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神采。那个曾经唱山歌比夜莺声音还好听的女孩就那么死了,彻底消失在世上。而我就是刽子手当中的一个。
黄莺好像有些惊喜,又好像羞涩、不好意思,腾出一只手去掖身上那件发皱的褂子。她矮下头,怯着眼神望我。她说,刘力,你回来了……
然后她把目光挪到别处,不再看我,蹲在小女孩面前,给孩子喂起米饭。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