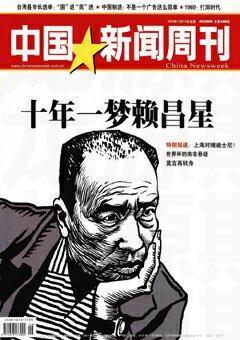“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杨 时 陈晓萍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工作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工资,享受福利医疗。这是中国现实。”
莫言现在开始忙碌起来,新长篇《蛙》出版之后,已有各媒体约访。他穿着旧毛衣坐在自家的客厅里,背后的墙上贴着女儿不久前结婚时的喜喜字。这个讲故事的高手面对媒体早已驾轻就熟,问题不用说完,他就会给出答案,细节丰富,观点清晰。
告别时,莫言对记者说,“不用动那些椅子,下午还有人来呢。”
“越是敏感题材,越要塑造独特形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经在讲座中说过,这部《蛙》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作家不敢面对敏感题材”的批评?
莫言:也不完全是,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主要还是我的一个姑姑是一个妇科医生,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退休,还有很多人找她,一辈子非常曲折。她是我生活中非常关注、让我非常感动的人物,最终要写出来。
小说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表现计划生育这个题材,还是要利用这个题材来塑造我姑姑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我想这可能是小说家最高的追求。越是这样的敏感的题材,越有可能让自己的人物处在风口浪尖上,处在这种极富冲突感里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小说里有很多隐喻,比如蛙是娃的谐音,养蛙厂和背后的代孕公司等等,这些是你有意设计的吗?
莫言:我没想得这么明白,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些之间有某种联系。其实“蛙”是我们先民的一种原始崇拜,一种图腾。先民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繁育后代和获得食物——食色性也。直到现在我的故乡里还有蛙崇拜的这种痕迹。像高密的泥塑里有胖娃娃,双腿之间要抱着一个青蛙。所以小说叫这个名字。
中国新闻周刊:小说中的写信者蝌蚪,一直在为姑姑做很拙劣的辩护,这是因为这个敏感题材所做的一种平衡吗?
莫言:也不是为了平衡,还是站在相对超然的立场上,来评价计划生育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一边倒,只展示一个个生命被毁灭的过程,那样,计划生育就是一个恶法,一个极不人道的政策,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计划生育应该有它的正面意义。大的角度来讲,和战争一样,有大人道和小人道。
辩护的拙劣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本身就产生一种反讽。
中国新闻周刊:《蛙》的语言不再有你之前作品的那种典型的狂欢化风格,这是你有意的吗?
莫言:最初废掉的15万字还是狂欢化的语言,我觉得不能总是那样,要改。有意压低调地去写,用正确的语言去写。
我也不是一拿起笔就像野骡子撒欢一样,也可以收敛着写。我当然喜欢那种狂欢化的语言,太过瘾了,可以一日万言。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中国作家过了50岁创作力就大不如前,你有这感觉吗?
莫言:写长没有问题,一天写三千字,一年一百万字了。写作时间长了,你的经验越来越多,匠气就会出来,包括你的记忆力衰退。写小说要有记忆力,要从你这个记忆库去寻找写作素材,找词汇、找比喻。记忆力衰退了,就慢慢地不行了。
我们承认毕竟一个人总是有限度的。
“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仍被贴上了“中国马尔克斯”的标签,马尔克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莫言:表面上看就觉得我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多,因为有超现实的情节,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这样的小说,跟我熟悉的生活很接近。土改、革命、中农、共产党,这样的小说才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我们解放以后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是虚假的,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写的,而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写的。这样的现实主义是狭隘的不真实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在写《檀香刑》的时候,用那种乡土的语言,民间戏曲的语言。你在后记里说,这是你大踏步的倒退。我个人觉得像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莫言:其实是想从文坛往后退。想和其他作家都拉开距离。不要大家都在一块,写的东西都差不多。
从热闹的地方往后退一点,作家就是应该像鲸鱼一样,稳重的,一个人在深海里呼吸。只有鲨鱼才成群结队,老虎也独来独往。其实文坛没有方向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那种狂欢式的语言方式和民间戏曲有关系吗,还是受到其他的影响?
莫言:那种语言和文革有关系,那会儿都在广场上演讲,文革期间红卫兵大辩论,口吐白沫的。口才好会被人敬佩不止,文革期间的语言就是一种气势,大排比、空洞。语言的一种狂欢,大量的形容词,语言的霸气。
我的语言风格是杂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语言对我肯定有影响,早期小说里边受到元曲的影响比较深。元曲一韵到底的气势是有点狂欢的味道,这种东西我觉得很过瘾。再一个是古典小说,另外就是民间戏曲。
民间口头语言,我想着这个是最重要的。农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极好,说话非常生动。我当时特别梦想长大了到集市上说书去。家里人骂我说我“热锅里炒屁”,闲我说话太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是对民间性的一个佐证,民间视角,新历史主义还有民间语言,但是你对“民间性”这个概念有所怀疑?
莫言:民间性,到底民间是指什么?过去我想多数人感觉是底层、农村,偏僻落后就是民间的;再有就是和官方对立的、在野的——非官方的就是民间的。尤其是诗人里,官方诗人能在主流的诗刊上发表的,在油印的发表的是民间的。这和出身没有关系。
后来慢慢我觉得民间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不要把底层农村简单的理解为民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间。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小说所涉及的都是农村的变革,你已经在城市居住这么长时间,对于城市和当下并没有涉及,是不屑去写还是无从下笔?
莫言:是无从下笔吧。生活在城市里处处感觉到城市的虚伪压抑和弊病,但还轮不到写这些,已经想得很成熟的题材在排着队呢。
事实上城市也已经渗透到我的小说了,每一部小说都有所体现。像《丰乳肥臀》的后半部分,《蛙》的第四部分以后。广义上来讲,8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向城市化转变的。
中国新闻周刊:说到《丰乳肥臀》,当初也引起很大争议?
莫言:如果你读我一本书,就读《丰乳肥臀》。新历史主义的,延续了红高粱家族很多的东西,比如家族、历史、乡土;也有后现代的,上官金童这种人物,恋乳症就是一种象征隐喻;历史跨度一直延伸到90年代,还涉及官场腐败;荒诞的也都有了。
出版社说这个名字出来肯定有麻烦,最起码有人说追求商业利益,用这样的书名勾引读者。我想还是没法改,这个小说的题目确实很难改,和内容太贴切了。大家都能感受到微弱的嘲讽的味道。
当时题目本身就让小说面临一种被枪毙的命运。要是换个题目叫《金童玉女》之类的,没准得茅盾文学奖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已经被故乡绑架了,是吧?比如,你这个年纪已经被故乡的人做了莫言文学馆、故居等等?
莫言:我这文学馆,也没有宣传的这么厉害,以前有个旧的,在那空着,有一帮退休的老同志,都是我大哥的同学们,他们没事干,就搜集一些资料。很多我扔掉了的东西,他们搜集。最开始成立莫言研究会,我就反对。他们说这跟你没有关系,我们要研究莫言你管得着吗。后来越做越大。只好认可了,只好支持他们。
我在开馆仪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后面这个楼里的莫言和站在这的莫言基本不是一个人,那里面用很多夸张的语言表扬的语言。我内心深处很清楚,永远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吃几碗米饭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你和其他一些中国作家集体离席,你为此受到很多批评?
莫言:没有办法。我看有的人说秦晖教授怎么没有离席,他是单独由德方邀请的。我是新闻出版署和作家协会他们让我去的,我属于代表团团员。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享受福利医疗。这是中国现实。国外无论在哪都有保险,在中国如果没有职业,生病我治不起啊。外国人骂还可以理解,中国同胞自己骂就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