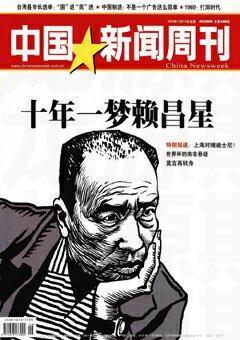莫言再转身
杨 时 陈晓萍
对于西方的批评——“不敢直面社会尖锐矛盾”,他嗤之以鼻。莫言认为自己的作品中“一向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管谟业从小的梦想是做一个集市上的说书人,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这是一个令同乡人侧目的梦想。
多年后,管谟业变成了莫言。梦想中的说书人变成了现实中的作家。而高密东北乡成为了他永远无法走出的故乡。所有小说都生长于那个充满荒诞、愁苦、乖张、朴实的山村,这部最新的长篇《蛙》同样如是。
一身居家打扮的莫言坐在北京的家中,他的公寓位于这个城市商住楼22层的高空。他从窗户望出去,把记忆抛到高密东北乡。“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的一个姑姑。”莫言这样说道。
《蛙》:荒诞派的收敛
在《蛙》里,姑姑是一位乡村妇科医生,曾经见证着生命的繁衍,后来却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计划生育”的战役之中。从此,姑姑的生活被夹在了新生婴儿的哭声和流产妇女的谩骂里。
年轻时的姑姑本有着似锦的前程,但她的飞行员未婚夫毫无征兆地叛逃台湾后,一切急转直下。经历了灰暗无比的特殊十年后,进入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重新激活了姑姑的热情。她再次被重用。
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生命的毁弃变成了天平两端无比沉重的砝码,姑姑努力保持着内心的指针不被某一端的重压崩断。步入晚年后,这个国策的忠诚执行者,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往,她对自己曾经的忠诚并不怀疑,但对死去的胎儿和孕妇们开始了忏悔。姑姑与一位泥塑艺人结婚,还魂般地与丈夫一起捏出无数泥娃娃,并且开始帮助不孕的妇女生育,内心如磐石的姑姑在这样的转变中慢慢老去。
现实中,莫言的姑姑确实是一位妇幼医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计划生育的时代,只是小说中加入了大量的虚构。
“写这个题材,也不完全是回应西方批评中国作家不敢直面社会敏感问题。主要还是想塑造姑姑这样一个人物。”莫言这样说道,“这个人物也是时代塑造的,要解释这个人物会颇费周折。”
小说以古老的书信体写成,夹杂着信件、故事叙述和剧本。写信者蝌蚪以文学爱好者的姿态向一位日本作家讲述姑姑的故事,最终以一部荒诞派的话剧剧本形成了与叙述的反衬。“有些不方便说的,用荒诞的方法写在最后的戏剧部分里了。”莫言承认转换形式的用意。
《蛙》最初写于2002年,初稿的15万字被莫言废弃。当时的小说有着复杂的叙事结构,穿插着回忆、联想和现实。“我觉得没必要用这么复杂的结构给读者接受造成很大障碍。”莫言说。于是在完成上一部长篇《生死疲劳》之后,他开始重新布局。改变结构的同时,莫言也放弃了他商标式的狂欢化语言,以收敛和“语文老师挑不出错”的文法述讲述故事。
现在的《蛙》充满了隐喻和象征,“蛙”本身就是先民生殖崇拜的图腾,小说中的泥娃娃与婴儿、养蛙厂与代孕医院都是掩体与实体的对比。在写信者蝌蚪为姑姑的辩护中,复杂和尖锐的国策成为了难以判断对错的存在。
《蛙》在结构形式上似乎是对于90年代另一部长篇《酒国》的呼应,但于文本层面,新作有着更为简洁的语法。从2003年出版的《四十一炮》开始,就可看出莫言改变语言的自觉的尝试,但刻意控制的文字力度远不及早期的绚烂肆意。
狂欢式语言的强转弱
1984年底,莫言写出了让他功成名就的《红高粱》,张艺谋的改编和电影的获奖,让莫言成为了一个明星般的作家。那是一次新历史主义写作的尝试,从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视角还原了一段民间叙述的历史。
“我爷爷”“我奶奶”和高密东北乡像魔咒般被不断提及,还有那个村庄中魔幻现实主义的闪影,莫言由此被贴上了“中国马尔克斯”的标签——即使当初这也是一个误读。彼时,莫言尚未读过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对我的影响远不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莫言坦陈。在彻底否定了颂歌式的伪现实主义写作之后,莫言开始向民间回归。《红高粱》只是一个开始。
1989年,莫言动笔写作《酒国》,这部小说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一个异数。《酒国》有与新作《蛙》相似的结构,书信和小说文体的交替,虚实合力建构叙述漩涡。小说虚构了一个灰暗的县城,里边有着诡异的侏儒和食婴儿的官员。“我把很多想说的狠话都藏在里面了。”莫言回忆。在一直关注莫言的评论家王尧看来,“《酒国》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小说,直到现在,这部小说也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
和敝帚自珍的《酒国》相比,莫言在90年代中期出版了引起巨大争议的《丰乳肥臀》。争议来自这个具有挑逗性的书名,实际上这部与身体写作毫无关系的作品,描写了一个民族受难的历程。小说前半部秉承了一贯的新历史主义,后半部对80年代后的社会充满反讽和讥诮,这应和着书名——对生命力的歌颂和对欲望泛滥的批判。这是一部壮年的作品,无论整体篇幅抑或细部描写。“前两天重新校对《丰乳肥臀》,看到里面大场面的战争描写,自己觉得叹为观止。”莫言笑着说。
在接着写作了一系列的中短篇之后,《檀香刑》出版。小说语言的狂欢达到极致,民间戏曲“猫腔”的一韵到底被莫言征用,小说的悲悯意识和受难情绪包裹在华丽的血腥描写中。莫言在后记中写到,“这是一次大踏步的倒退。”作者所说的倒退,是指语言再度深深扎入民间。这似乎是一次以退为进的策略,在一片“西方翻译调”的文坛,莫言用土腔上位。
自此,莫言将恣意妄为的叙述方式冻结在《檀香刑》内部,开始寻求文体狂欢以外的可能。
作品“一向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我希望每一部和上一部完全不像一个人写的。但那不可能。”莫言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新长篇《蛙》中,叙述语言收敛而正确,不再有排比和铺张,不再有信手拈来的比喻。其实,作家自觉改变语言方式的尝试始于几年前。
《檀香刑》实际上是莫言一个阶段的终结。在那之后,他曾说对于新长篇的写作“每一句都很艰涩”。至于未来的变化只有“天知道,鬼知道”。等到人们看到莫言的变化,是2003年《四十一炮》的出版。
在文学彻底式微和作家自我寻求语言转变的情境下,《四十一炮》这部叙说农村变革的小说虽然获得某个年度杰出奖,但与之前的作品的影响力相比下降很多。小说仍以孩童的视角展现90年代农村变革中的人性、观念冲突。语言方面部分残留着以前的汪洋恣肆,部分向平实靠拢,撕扯中让作品陷入平庸。
在《檀香刑》出版之后,莫言曾表示“有生之年再写一两部自己觉得很好的长篇就可以了。写那么多干吗?”但事实上,这更像一个成功作家的说笑之词。2007年,一部50万字的《生死疲劳》问世。一个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六道轮回为动物,以动物的口吻叙述五十年的乡村史。与先前作品趋同的主题和毫无控制的叙述,让小说显得絮叨而冗长。
莫言承认,作家的语言和生活经验不可能完全超越,“每一部作品能稍有不同已经不错了”。现在的莫言已然是中国一线作家的代言者,每部重要作品都被翻译为各国文字,应邀代表中国出席国外书展,与诺奖得主对话且往来频繁,不情愿但仍被故乡设立了莫言文学馆且保留了故居……
不可避免地,他也承受着西方的批评——“不敢直面社会尖锐矛盾”,但他对此嗤之以鼻。“我一直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我的作品中一向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莫言这样说道。莫言所言属实,他每一部作品都有对社会的批判,甚至写出过《天堂蒜薹之歌》这样的愤青之作,但只不过一切批判的锋芒都被他收纳到叙述的迷宫中,显得隐晦难寻,这是形势环境之下作家的表达方式,或许也是性格使然。
《蛙》是莫言的又一次尝试,用“去莫言化”的语言更直接地面对一个敏感题材。虽然有些地方仍显得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但是他在意的是“这样的敏感题材这不也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