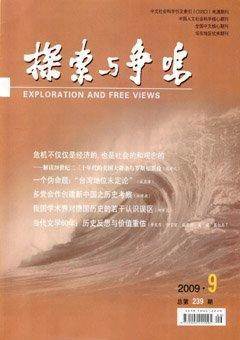论道德恐怖主义
内容摘要 道德恐怖主义是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将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置于道德恐怖中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网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这种做法会掩盖事实真相,损害民主的健康发展,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强势群体对既得地位和利益的维护,以及绝对化和简单化的道德思维。为了消除道德恐怖主义,需要人们养成倾听弱势群体声音的习惯,具备包容之心和复杂思维的品质。
关 键 词道德恐怖主义 网络 实质 危害 根源
作者 唐克军,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武汉:430079)
对人实施恐怖行为有多种手段,道德是其中之一。为了激起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怒,甚至仇恨,一些人就会拿起道德武器,让这些群体或个人处于道德恐惧之中。例如,为了攻击普通中小学教师,有人炮制出家长给教师送“出国游”的大礼,似乎在说如今的教师早已堕落;为了阻止农村人到城里务工,有人大肆渲染“农民工”进城会制造混乱、破坏城市的文明,甚至把犯罪行为都与“农民工”相联系,仿佛农民工是道德堕落的代名词。我们把这种以道德为武器而制造公众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愤恨,从而使这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人处于道德恐怖中的做法称为道德恐怖主义。这种道德恐怖主义现象在网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范跑跑”、“杨不管”等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在此,笔者无意否认道德谴责的正当性,而要质疑的是对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无根据的、不客观的道德攻击的正当性,并分析其实质和危害。
道德恐怖主义的实质
不论道德恐怖主义以何种形式出现,其实质是一种社会排斥,因为这种恐怖的道德攻击都依据某种道德标准,并利用这一道德标准将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从社会中排斥出去。只不过,网络时代的道德恐怖主义承接了历史上的传统做法。过去,我们批判封建礼教,痛斥礼教杀人,如鲁迅揭示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胡适也说:“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1]劝人做烈女,是让人合乎礼教,为贞节而死,当然这种死会获得褒扬。但如果不按某种道德标准行为,就是禽兽,就不配留在这个社会上,因而,只有死路一条。在这种意义上,道德成了杀人武器,成了对人施以恐怖的手段。孟子有言:“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君臣父子之伦,天经地义,杨氏却要为我而不忠君,墨氏却要兼爱而不孝亲,因而不配做人。如朱熹说:“若君亲与他人不分先后,则是待君亲犹他人也,便是无父。此二者之所以为禽兽也。”[2]是禽兽也罢,更恐怖的是导致率兽食人。孟子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在孟子看来,如果不排除杨墨之徒,就不会有仁义的社会。因此,必须把杨墨之徒排除在社会之外。从孟子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如何利用道德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
这种以人与禽兽之别的道德标准,将某些人或群体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做法一直运用到今天的网络中。2008年,在网络中被丑其名曰“范跑跑”和“杨不管”的范美忠和杨经贵,不是被这种道德恐怖主义从教师队伍中排斥出去了吗?在道德恐怖主义者看来,范美忠临危先跑,而不顾学生的生命危险,怎能称为教师?爱护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危难见真情。先学生而跑是不爱学生的明确表现,因而不配做教师。所以,有人异常激动地用“无耻”、“畜牲”、“杂种”之类的字眼辱骂范美忠。既然是畜牲,也就丧失做人的资格,当然不能继续做教师,于是教育部取消了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证,学校解除了与他的聘用关系。在这种道德压力之下,谁敢替范美忠说话,谁就会受到道德攻击。一位名叫鲁靖的“抗震美女”说了句“嫁人就要嫁范跑跑”,就遭到网民的道德炮轰,最后她不得不说:“我鄙视范跑跑。”杨经贵同样遭受了道德恐怖。网上就有人指责他是“任凭风浪起,稳站三尺讲台当‘看客,是极端不负责、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既然没有职业道德,当然得离开教师岗位。杨经贵不仅要承担10万元的赔偿,还被停职。
在西方,同样有通过道德恐怖的渲染而将某些人或群体排斥在社会之外的行径。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有灵与肉或精神与肉体的区分,“灵”或“精神”意味高贵、高尚和主宰,“肉体”意味低级、卑下和服从。依此标准,可以将某些人归为肉体的范畴,将某些人归为精神的范畴。占据精神的人有自己独占的空间,自然容不得“肉体”进入。依此理论,理性是参与政治最基本的道德品质,而妇女和穷人没有理性,因而应排斥在政治之外。“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到洛克、卢梭,政治理论家和哲学家认为男女生而有别,男性天生更理性,因而更适合政治和公共生活,女性因为非理性而更适合家庭的情感生活。”[3]尼采更是将精力充沛和有权力欲的男人颂扬为高贵,而将女人贬为弱者和反复无常的病态,从而鼓吹专制统治,鼓吹强者对弱者的利用和剥削。卢梭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妇女参与政治会引诱男人,使男人堕落。
劳苦大众的政治参与也被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所排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民必须是有产者、家长和战士。韦伯解释西方古代公民之所以必须是战士,是因为城市需要保卫,只有有产者才能武装自己,成为战士。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赋予了有产者以美德,即所谓“公民美德”,这就天经地义地宣告有产者参与政治的资格,从而划定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政治界限。西方的这种社会种类理论认为,平民百姓在行为上不成熟、不道德,无产者有暴乱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这种伪造出来的政治鸿沟做了精彩的分析。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中,可以看到群众是怎样被排斥的。他们说,在批判的批判看来,群众是肉体,或者是肉体的代表,布鲁诺及其伙伴是精神,或者是精神的代表。在批判的批判看来,精神的对头是精神空虚,“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4]。精神空虚就是“思想懒惰”、“表面性”、“自满”,这些是群众的品质或群众的代名词。“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5]这样群众就被精神规定,也就在文化上完成了对群众的规训,群众理所当然被排斥在精神世界之外。“群众将要被这种或那种方法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其结果,‘群众社会将留在‘社会的社会之外。”[6]因为群众精神空虚,所以他们不可能独立,需要统治者,从而达到某些人独立统治的目的。“同黑格尔的这种学说同时发展的,法国有空论派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的独立自主是和人民的独立自主对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也就是一群单个的人的活动,那么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反而应该仅仅在少数单个的人身上得到抽象的表现。每一个单个的人是否愿意去冒充这样的‘精神代表者,这要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象力。”[7]的确,某些人有了某种地位,同时也就有了想象力,以为自己可以主宰历史的方向,把自己视为神,让群众顶礼膜拜。然而历史不是某些人的精神的历史,相反是感性的、具体的人的历史,群众是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事实上,群众的消极品质是制造出来的。“批判的批判自己制造出自己的对立物即群众的愚蠢。”[8]那些企图做神的人往往把群众按在地上,跪在地上的群众以为他们很伟大。但人们意识到那些人其实不过是包装出来的普通人,当人民站起来与之并肩时,一切占据精神的人就难以统治人民。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引用了一段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9]
道德恐怖主义的危害
社会排斥的做法就是让你难以在其中生存下去。为了把某些人从某一领域或地区排斥出去,就把某些品质归于这些人,迫使这些人选择“自愿”离开。那些处于优势的人,以精神的化身自居,以精神的高度盛气凌人,对于那些心怀蝇头小利的人用高贵的道德加以训斥,斥责他们没有良心、没有做人的道德,行尸走肉,不是人,因而不配生活在世上。那些只有自己利益的人与占据精神的人相比,就会觉得无地自容,最后的办法就是逃离社会。在某些占据精神的官员看来,“草民”、“刁民”犯上作乱、不守法度,只有自己的私利,不懂大仁大义,所以应当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以还人间太平。作为“草民”、“刁民”的人不得不自绝于世,断不敢有参政之念。城里人以文明、现代、精明和独立等形象出现,而把短视、自私、愚钝和依赖等不良品质强加于乡下人,乡下人自然不敢对城市有所奢望。这种做法有以下危害:
第一,破坏人的道德平等。道德恐怖主义预设的道德前提是道德不平等,即将某些高尚品质归为自己或某一特定群体,而将不良道德品质归于自己的攻击对象,使自己处于道德优势,从而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平等。
第二,阻止对真相的探索。道德恐怖主义将某些不良品质强加于人,然后理直气壮地排斥这些人。所排斥的人实际怎样,并没有人关心,因为他们已不配被关心。当群众被斥为精神空虚时,群众的真实情况就被忽视。当范美忠与杨经贵被斥为“范跑跑”和“杨不管”时,他们真实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感受便被忽视,这就阻碍人们对真相的探索。
第三,妨碍制度的改进。我们知道,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改进。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了解真相,也就无法判断问题的实质,更无从改进制度。杨经贵为什么没有管理好课堂秩序?这个班、这所学校的状况是怎样的?学生的家庭状况又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问题没有弄清,我们就无从提出改进教育的任何策略。
第四,损害民主的健康发展。民主意味着给所有声音以同等的机会,而压制和排斥某种声音就会破坏民主。道德恐怖主义者往往以道德上的优势压制自己攻击的对象,迫使攻击对象选择沉默。杨经贵在事后即如此。实际上,在道德的恐怖压力下,沉默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被攻击者说出自己的心声,为自己辩护可能会遭到更为强烈的道德攻击。然而这种沉默是民主的悲哀。
道德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道德恐怖主义以道德为武器,对某些群体和个人制造道德恐怖,以便公众对这些群体和个人保持警惕。面对这种道德恐怖,我们不禁要问,谁在制造对某些群体或人的道德恐怖?他或他们代表谁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习惯于运用道德恐吓?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道德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回答前两个问题,我们会发现制造道德恐怖的人往往是处于社会结构的强势地位的人或为社会强势说话的人;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道德思维存在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第一,社会的强势群体出于对既得地位和利益的维护。虽然社会免不了要分层,但分层并不意味社会向上流动的停滞。然而当分层完成了结构化和制度化,就出现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之别。体制内的人即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强势群体,他们为了阻止体制外的人进入,就会利用道德盾牌阻挡体制外的人对其地位和利益的觊觎。体制内的人往往把自己装扮得更道德,把高尚品质绝对地固定在自己身上,而把体制外的人描绘为无耻、无知的道德腐败者,极力渲染被排斥群体的道德危险性,其目的就是证明自身特权和既得利益的合理性。
第二,绝对化和简单化的道德思维。如果我们反思自己的道德思维,便会发现:我们习惯于要求他人绝对地履行道德准则,不管个人的特性和具体的情境;习惯于简单地把不良的道德特征固定在某些群体的身上。前者是以圣人的标准评价人;后者就是道德偏见,即所谓“地域偏见”、“种族偏见”、“阶层偏见”和“性别偏见”。在前者看来,军人应该勇敢,最好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如果军人临阵怯弱,就是违背军人道德,就是不能接受的。教师应该保护学生,不管教师个人的特性,也不管所处的危险境地。如果教师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呆,或者先跑,都是不道德的,都是不能原谅的。作为父母,应对孩子慈爱,而不管父母的境况。如果父母因为贫穷卖儿卖女,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此道德评判,自然让被评判者陷入公众的道德恐怖之中。其实,人非圣人,何况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后者则是对某些地区、某些阶层、某些种族等进行道德攻击,以让公众对这些群体产生不信任感,以便使这些群体处于道德恐怖之中而自我孤立。面对这种道德攻击,只要我们了解这些群体,道德恐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
对道德探究的呼唤
消除道德恐怖主义,建立和谐、包容的社会,需要我们探究真相。网络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探究真相的平台。“周老虎”、“躲猫猫”等真相的还原,都是网民探究的结果。但同时,网民又极易陷入非理性情绪,从而滋生、助长道德恐怖主义。因此,为了探究道德真相,有必要重塑我们的心态。
第一,要有倾听弱势群体声音的开放心理。道德恐怖往往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发出的,他们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弱势群体的呻吟,即使在网络中也如此。要知道,弱势群体也有平等的道德要求,人们也需要尊重他们的需要。如果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会改善对他们的道德看法。如武汉市政府曾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的官员与街头擦鞋女对话,擦鞋女的生存要求让在场的专家潸然泪下。从此,她们获得了街头擦鞋的自由,而在此前,她们被视为城市文明的污点。因而,作为具有开放心理的网民,不仅要倾听弱者的声音,而且要增强这种声音,以便引起社会的关注。
第二,要有一颗包容的心。消除道德恐怖主义,需要我们树立平等的包容心态,包容不同的道德表现。包容并不是纵容,我们绝对不能纵容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对发生了的不道德行为,我们不能仅仅进行简单的谴责,而是要接受和面对这种事实,寻求更好的道德解决办法。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为保护学生而献身的教师体现了人类的高尚道德情操,可歌可泣!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接受在大灾难面前被吓倒的教师,因为人有软弱的一面。香港凤凰卫视曾播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节目,其中一对夫妻回忆他们的经历。当地震发生时,他们一家三口正在熟睡,丈夫一感觉震动就意识到是地震,他立马翻身下床,冲出房外,随后房子完全垮塌。这时他才意识到老婆孩子还在房里。于是他拼命地扒废墟,终于扒出老婆孩子,而老婆的身体正俯在孩子身上。事后,妻子并没有责备他只顾自己逃命,而是一如既往地共同生活到今天。如果从道德绝对主义立场出发,丈夫在危难之时抛下妻与子逃命,说明他既不爱妻,也不爱子,是十足的禽兽,也就理所当然地不能让他再进家门。如果这样,将是家庭的破裂、岁月的艰难。
第三,要有复杂性思维的倾向。并非所有道德问题都像给老人让座这样简单,很多道德问题发生在复杂的情境中,因而不可能凭借一种道德标准衡量人。如去年网上流传一则消息,郑州一位中年妇女偷肉被抓,面对记者的镜头要撞墙,怕儿子见了没法生活下去。她说,儿子上高中,两个月没有吃肉,又无力购买,才这样做。对这样一位母亲,我们怎样进行道德评价?我们怎样对待这位既是小偷又是慈母的女人?对此,我们应思考不同的道德主张和真实的道德情景,以免让我们陷入道德绝对主义。
参考文献:
[1]蔡尚思. 中国礼教思想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9.
[2]黎靖德. 朱子语类. 长沙:岳麓书社,1997:1180.
[3]简•弗里德曼. 女权主义.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33.
[4][5][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5、109、125、108、16、104.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