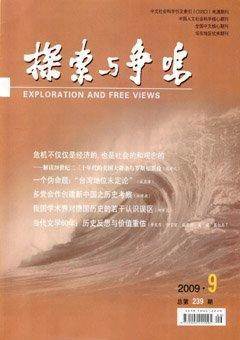本土文学资源的激活与重铸
黄发有
当西方文学的价值系统被视为优越于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性”,现代西方被等同于在时间维度上领先的“新”,古典中国被等同于在历史进程中滞后的“旧”, 片面的追新逐异隐藏着割裂汉语文学传统的危险,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就成了缺乏对西方话语进行辨析与批判的唯西方化。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深入传统内部清理并反思传统,而一些当代作家却因为对传统的无知而抛弃传统,以至于试图通过生硬的文化嫁接将西方传统当成自己的文化根基。让人纳闷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什么总是有人理所当然地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当成水火不容的东西,甚至心安理得地认为割裂传统是“现代化”的必要代价。
在“十七年”文学中,《林海雪原》、《红旗谱》、《山乡巨变》、《三里湾》等作品都留下了继承本土文学传统的审美烙印。但是,作家对本土文学资源的自觉认同与深入开掘,更为集中地体现在“文革”后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在文化自新意识的推动下,不断有当代作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探索本土文学传统重新铸造的可能性,其艺术成就也更具有文学史价值。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一边是盲目的反传统所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另一边是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所催生的文化自卑主义。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境中,为了避免使自己成为平均化的全球公民,一些作家以外来文化作为镜子,开掘沉睡于脚下的土地之中的民族文化记忆,抗拒遗忘,将厚重的传统资源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打破封闭的心理定势,激活曾经长期被正统文化所抑制的民间文化的创新能量,形成互动共生的良性循环格局。
“寻根文学”常常被视为新时期初期立足本土经验的文学探索的先驱与典范。确实,寻根作家笔下原汁原味的风情展示弥散出民族化的审美情调,尽管其中也不无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福克纳式意识流的痕迹,但恰恰是外来刺激强化了其文化认同,在其艺术借鉴中贯穿着一种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本土化情趣,在艺术上也显现出一种追求民族同一性的身份自觉。事实上,“寻根”文学承续了以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冯骥才、林斤澜为代表的地域风情小说的文化追求,那种冲淡平和的审美风格、宠辱不惊的出尘趣味与传统士大夫游移于进退之间的入世情怀,与当时呼啸而过的“伤痕”与“反思”文学大异其趣。虽然这些作品注定不会大红大紫,但这种疏离文学主流的选择,恰如汪曾祺在《受戒》中所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主流。”[2]但是他们对于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的审美表现,却具备了更加锐利的审美穿透力和更加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文化寻根的审美追求在诗歌创作中的觉悟要来得更早一些。1982 年杨炼就推出了《半坡》组诗, 1984 年又陆续写出模拟《周易》思维结构的繁复的《自在者说》。1984年7月以石光华、宋渠、宋炜、杨远宏为主将的四川“整体主义”诗群宣告成立,江河在1985年初发表了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的《诺日朗》和《半坡》、《敦煌》、《西藏》等组诗,从楚骚精神到文化遗址和经典文本,以朝圣者的虔诚从历史文化中追寻现代启示的精神源头。诗人及其后来者通过对远古神话的激活,寻求现代意识与原始精神展开对话的隐秘通道,在破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本原的基础上,建构 “现代史诗”,瞭望中华民族的来踪去影的高塔,追索向整体存在趋近的可能性。以廖亦武、欧阳江河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诗群”则对文化传统背后隐藏的巨大黑洞进行长驱直入的内在爆破。他们一方面以审父意识冲决正统文化培育奴性的牢笼,另一方面是对一种隐性的、被压抑的、被遮蔽的民间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从大地母亲蓬勃强健的野性活力中寻找孕育新希望的文化摇篮。在回归与批判的深入追问中,诗歌对于传统的多向撞击开启了与传统对话的新空间。
关于本土审美资源的现代转化,以孙犁、汪曾祺为前驱的新笔记小说的形式探索与文体建构的功绩常常被忽略。新笔记小说情节淡化,文字淡雅,意味深长,回归中国笔记小说传统并不意味着简单移植传统,而是通过主体意识的高扬来摆脱僵化的规范,在舒展性灵的自由选择中扩展文体的艺术容量和思想含量。这种文体在松散处有暗流涌动,在留白处韵味丛生,在散文化的体式中埋藏诗眼,一些作家对于心理描写、人性悲剧、象征效果、幽默色彩、寓言风格的探索,犹如在舒缓的田野上挖一口深井。
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的本土化探索可谓异彩纷呈,这最为典型地反映在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作家的价值选择和形式建构也更加多样化:
首先,在文本的历史形态中,创作主体的想象力呈现出自由发散的状态,从多个角度对民族历史进行阐释与重构。和再现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不同的是,“新历史小说”借历史的躯壳来复活作家心目中的文化精魂,从不同侧面拓展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1)民间野史对庙堂正史的反讽与解构,通过对那些被遮蔽的史料的重新发掘与叙述,通过官史文本的矛盾与裂缝揭露皇权政治的虚伪,批判权力意志对于民间疾苦的漠视及其反人性倾向,代表作品为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和《温故一九四二》、莫言的《檀香刑》、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等;另一方面,在主流规范的边缘处发掘冲决压抑和驯化的原始生命力,从野地的狂欢中寻觅点燃酒神精神的野性火种,突破腐朽的禁忌,拯救枯竭的灵魂,重新获得与世界本体融合的快乐,代表作品为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九月寓言》等。(2)虚构原则对信史原则的疏离,从史传传统中突围而出,强调历史的审美性与想象性,使文学想象从历史的依附地位中独立出来,使叙事结构打破了一贯性的时序、因果、整体化结构,回忆、联想、闪回、蒙太奇、抒情等手段的运用为历史叙述带来了丰富性。(3)个人的、心灵的历史从群体历史的普遍性中脱颖而出,把历史看作一种叙述的权利,通过想象找寻到深入人的精神世界的途径,用情感与内心的历史来对抗“胜者为王败者寇”的庸俗的历史逻辑,张承志的《心灵史》、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李洱的《花腔》,都是个体与历史展开深层对话的文本。
其次,在价值形态上,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相对主义是两对双胞胎,他们互为犄角,有时又相互融合,譬如《白鹿原》的“鏊子说”和《故乡相处流传》“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闹剧,居然在历史循环论的岔口奇妙地汇合。道德理想主义立场倡导回归到以自然、原始、群体、道德为本位的理想主义,《白鹿原》在精神还乡之旅中对民族文化从背叛到重新皈依的过程,在向后看的沉醉中寄托了作家渴求民族文化复兴的梦想与希望。而怀疑一切的倾向所导致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将主体对虚假的、欺骗的价值规范的否定,引向对价值关怀本身的否定,在抛弃虚妄的理想、正义、幸福的同时,也抛弃了所有的意愿、意义与目的。
再次,在形式建构上,“村落与家族”叙述是一种流行的风尚,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文化的根底,而村落文化是农耕文明鲜活的细胞。作家们大都以一种诠释“大历史”的抱负,要从一个横断面来表现现当代或20世纪中国的曲折历程,进行全景式的审美观照,反映出建构“气魄宏大、规模巨大”的文化史诗的形式自觉。但是,作家围绕家族的想象与编织的故事如何避免历史与想象完全同构的陷阱,是普遍没有解决好的艺术难题。
最后,作家们自觉通过对民间传统的激活来寻找审美的新突破,譬如《檀香刑》中的茂腔(作品中为猫腔)唱词,《秦腔》中的秦腔戏,《圣天门口》内嵌的民间说唱《黑暗传》,都成为作品重要的结构元素。而《白鹿原》对于蓝田县志以及其中的《乡约》文本的创造性化用,使其具备了人类学视野中作为文化收藏形式的民族志风格。此外,《金瓶梅》对《废都》的影响,在贾平凹、尤凤伟的“匪行小说”中摇曳的《水浒传》的文化投影,《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启示,都是当代文学与古典传统展开多元对话的表现形式。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的形式的独特性,也离不开藏地民间的灵动启示,作家也坦承“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自由穿越的方式,给了我自由,给了我无限的表达空间”[3]。
王小波、李冯、崔子恩、李修文等作家对历史和中国古典文本进行戏仿的小说显露出另外一种才情,尤其像《青铜时代》在对唐传奇的拼贴式重写中释放出一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这类小说的缺点在于,作家缺乏节制的戏仿,往往只能是以一种荒唐嘲笑另一种荒唐,价值基点的缺失使戏仿成为价值迷惘的文化表征。不过王小波的《青铜时代》的戏仿并没有迷失在形式主义的泥淖中,它对灭绝人性的权力覆盖和躯体摧残的戏谑式描述,勃发着一种酷烈、沉痛、激愤的抗诉。正是在此意义上,戏仿小说无法割断与反讽的血脉相连的联系,否则,戏仿就会成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舞蹈。
中国文学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关键是要向世界提供“人无我有”的独特奉献。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英语和英语文学的版图不断扩张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的语言与文学正在消亡,审美经验也呈现出逐渐趋同的一体化倾向,世界文学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文学如何发掘传统资源,如何在与外来资源的互动认知中,通过对传统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孕育仅仅属于中国的艺术形式,这是中国作家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生发出别样的审美情趣,犹如在黑暗尽头的辉煌日出,照亮全新的视野和无限的可能性,为世界提供无可替代的艺术享受。
参考文献:
[1]韩少功. 文学的“根”. 作家,1985(4).
[2]汪曾祺. 关于《受戒》. 小说选刊,1981(11).
[3]阿来. 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 民族文学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