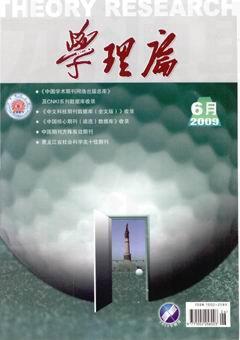大潮涌动下的时代乐章
朱 军
摘要:史诗性可以概括一些长篇小说的特点。十七年间的一些长篇小说作家以左翼史观为指导,利用文本讲述、演绎单一的“中共”史,为“当下”服务。文本一般以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为基调,有重大的时代主题,宏大的结构、叙事模式,对“时事”、时代英雄的抒怀,符合时代的共名,文本整体上呈现有恢弘的气魄。
关键词:历史;历史功用;宏大叙事;诗性抒怀
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085—02
史诗作为一个西方诗学概念,一般指长篇叙事诗歌,其主题崇高,主人公多是神或者半神半人的英雄。但是也可以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类长篇叙事文学,不完全是诗体,一种全景式的描写作品[1]。而史诗性是从这类作品透露出来的恢弘、磅礴的气势、风貌。具有史诗性的文本一般从宏观把握历史和现实题材,拥有宏大的时代主题、崇高的英雄人物和庞大的结构与叙事模式,作品整体上呈现宏大、庄严风格。一般可以从“史”与“诗”的角度分析史诗性的作品。
史诗性是十七间不少长篇小说家在其创作中的一种自觉的追求。这种创作追求缘于当代小说家的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件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这种追求既有中国传统的“史传”和“风骚”的影响,也有对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借鉴,更多的则是对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战争长篇小说和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剖析小说”的借鉴和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成为一些左翼作家的高度责任。这种集体意识,主要表现在用革命历史题材来“揭示历史本质”。这种追求具体在以“红”系列(《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一代风流为主题的《三家巷》[2]和历史小说《李自成》中。
一
这些作家亲历旧社会的黑暗和苦难,怀着感激新社会的心情,虔诚地学习马列毛著作。在他们看来,历史意味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规范内的“中共”历史。他们通过叙述既定的、“合法”的历史,为现存的合理性证明,进而对“历史”的本质做出规范性的叙述,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其文本构思多从政治的角度切入,用艺术论证政治,为“当下”服务。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较早是《保卫延安》和《红日》。《保卫延安》取材于1943年陕北延安战事,达到这样叙述目的,“只有真正的掌握了胜利的关键和全部力量……启发他(读者)进入历史现实……从而得到鼓舞和教育。”[3]《红日 》也是对解放战争历史进行艺术的抒写,说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历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4]历史的功用性、文本的现实性是很明显的。将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叙述伸向更远时代的是《红旗谱》和《三家巷》。《红旗谱》对革命的叙述从20世纪30年代初在河北“反割头税运动”等,到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斗争情况。从而与楔子比较形成这样的阐释目的:党和群众的结合是天然的;只有党领导团结群众,走群众道路,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同样,《三家巷》也叙述中共领导斗争的历史,表现了20世纪20年代工人运动艰难的成长过程和中国革命初期复杂的社会画卷。其历史是作为人物活动、思想斗争、成长的背景,意寓革命洪流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决定个人的成长方向。而被喻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5]的《红岩》在当时被有意组织写作,来讲述对革命更纯洁的追求实现对当下生活的观照——革命历史教科书的性质非常明显。最具有深意的是《李自成》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揭示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实质,指出农民起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表明农民革命战争的必然性,参现代历史本质(革命、斗争)的揭示。现实指向性很明显。质言之,这些文本所反应的历史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发生、发展、壮大、领导民众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抗争的、反压迫、反剥削的历史。其代表先进方向、顺应历史潮流,强调社会进化,其实质是一种进化史观。
时代呼唤革命史诗。由于新生政权通过几十年的战争才建立起来,所以“创造出无愧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时代的作品”[6]成为时代的祈求。同时,许多经历这场战争的作家,时代信仰观念无不受到左翼文化的影响,于是他们感应时代的号召,通过描写革命、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史和党史来证明其存在合理性。然而,许多时候,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筛选为单一的政党史;这种纯净无瑕的历史在当时有合理的一面:历史是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7]。历史是精神活动的产物,利用文本来书写历史也是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都是当前的,因此一切历史就永远都只能是当代史——历史正是以当前的现实生活作为其参照系。历史只有和现实政治结合在一起时才有意义;历史的意义是主宰现实的判断,规训现实。
二
史诗在结构上是有机的整体。史诗性的作品一般结构庞大、叙事宏大,整体上呈现恢弘、阔大的气魄。十七年的革命史诗性文本追求宏大叙述规模,或在空间的层次性、时间的广延性上挖掘,或在文本内注重多线索、网状的结构,这种叙述模式成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内在叙事特点,也为当代文学创作中对革命史诗性的叙述提供了经典范式。
战争油画。这种模式主要是对战争全景式的叙述,注重宏大的战争场面,通过不同的空间连接突出时代背景。《保卫延安》出版后,被誉为“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3],它通过青化砭伏击战等不同类型的战争场面,成功地描写各类战争的特征。同时作家把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置于全国战争大背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军事行动与之相呼应,展现了解放军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的宏大的军事画卷。而《红日》则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来展示战争的独特魅力。文中描写三次战争,以中共一支“常胜将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之间的大规模战役为叙述中心,将笔触从军师团一直延伸到连排班,从高级将领一直到普通战士,从军队到地方,从前方到后方医院。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点面结合,具有整体性的特点。
重构现代历史。这种模式注重时间的线性挖掘,将中共的发生、发展、壮大的历史与农民抗争的历史进行淋漓尽致的描写,显示出历史的纵深感。《红旗谱》从历史长卷入手,着眼于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矛盾斗争,对民主革命运动时期农民的历史命运以及中共革命艺术概括,有一种历史的深远感。而《三家巷》则描绘三代人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悲欢离合,反应了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此叙述模式以历时的角度,挖掘中国近代社会变迁,通过一系列时间“点”成“线”从而呈现出历史凝滞、厚重之感。
观照封建历史。这种模式主要以左翼史观为指导,能够“深入历史,跳出历史”[8]来描写封建史。如《李自成》大视角、大眼界的观照历史,写出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过程、结果和影响,深刻的把握“历史”本质与规律;文本通过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艺术描叙,呼应20世纪20年代工农红军斗争的意义。这种模式除了具备宏大的叙事模式外,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列的进化史观来看待过去(历史),写社会政治风云变化,强调革命的进步的力量,摒弃封建的天道循环的史观。
三
十七年革命史诗性的作品既具有西方史诗中透露出来的崇高的美,也具有中国传统诗画中优美、静穆的氛围。
崇高的美在于作者的主观情绪,叙事中抒怀言志。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几十年的战争建立起来的,新生的人民政权理所当然地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用艺术形式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正确性。而作家的“社会历史学家”意识促使他们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作出证明。同时,这些作家绝大多数是战争的亲历者或目击者(多为政治工作者),他们利用手中的笔,较真诚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是如何诞生的,这项开创性事业的领导阶级所付出的前所未有的努力,以及他们在血雨腥风的历史洪流中如何改变自身的命运,通过这些内容来书写自己的情感。进而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倾吐在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像周大勇、朱老忠、江姐等一批体现时代审美理想人物,这些英雄人物已成为作家对那个时代的特殊赋予、不可重复的理想形象特质。这些透明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种为压迫人民的解放而赴汤蹈火的无畏气概,那种为追求崇高理想而百折不屈的坚毅精神,那种无私的胸怀、真诚的品格,正是作家对时代的赞美,对历史的抒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而对对立的敌方丑陋的刻画、漫画式的勾勒、戏谑式的嘲讽是作者对阻碍历史、时代潮流的丑陋人物的鞭挞。
而作者对民间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描写,构成另一种诗性抒怀。在战争史诗《红日》叙述中,作者或战争场面和和平场景互相对照、转换的描写中,如医院后方的生活场景、爱情生活场景中,达到一种日常生活诗意化,衬托战争的残酷,暗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在《红旗谱》作者对北方民间生活场景描写,在看似自由散漫的叙事中,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风土人情画卷,如“脯红鸟事件”,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眷恋。《李自成》中社会图景的描写,从民间到宫廷、从都市到乡村,从元宵节施放的烟花、米脂的火塔、精雕细刻的器物到风俗人情,真切的表达下层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寄寓作者的民间情怀。
然而,十七年的战争史诗性作品缺少西方史诗应有的反思,多盲目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充斥文本,且艺术较粗糙等;这是特定的时代的规范、选择而形成的十七年特有的文化特征。
参考文献:
[1]阎浩岗.史诗性与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评估[J].文艺争鸣,2007,(6):76;张荣翼.史诗的三次衰亡[J].人文杂志,1995,(3):115.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08.
[3]冯雪峰.论《保卫延安》[G]//冯雪峰论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30.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62.
[5]罗荪,晓立.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J].文学评论,1962,3:99.
[6]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G]//周扬文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28.
[7][意]克罗齐(croce.B).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
[8]姚雪垠.关于《李自成》探索与追求——致胡德培同志[G]//长篇小说研究专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563.
(责任编辑/李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