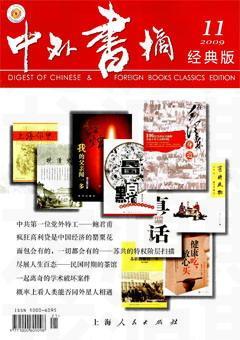尽展人生百态
蒋伟国
茶馆的阶层、职业分野
长期以来,茶馆的职业界限、阶层界限相当分明。因而不同阶层的茶客。只能到自己所属的茶馆去饮茶品茗。而不能随心所欲。误入与自己身分不符的茶馆的。这种惯习,在民国初期相当流行,后以社会的变动而逐渐被打破。
常熟,地处东南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且为商品经济的生长准备了理想的场所,因而,作为末业的商业在农、工、商各业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商业的兴盛,一些服务性行业也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茶馆业就是其中之一。整个民国时期,常熟城内的大小茶馆有91家之多。其中,枕石轩、琴一楼是专门招待官吏和地方士绅的;挹辛庐、新梅岭、天香阁、琴园、环翠小筑、栗里等则是邑中知识界、医务界、书画界、教育界、金融界人士品茗聚谈之处;而市中心的仪风、湖园,是少爷公子们聚友聊天之所在:至于一般的商贾市侩,则大多聚集在南门外长兴、得意楼、长乐等茶馆里。
民国年间,不同的品茗者根据各自的身分和地位,相聚于固定的茶馆。各不相混的情形,不独常熟为然。其他诸如上海、杭州、成都、扬州等地区也是如此。
在天府之国成都。茶馆主顾的阶层分界、职业分野也很为明显。譬如,东城根街的梁园茶馆。是厨师们的集中处;陕西街的顺江茶馆,是建筑工人的聚集处;三桥南街达观茶馆,是油漆工的聚会点;东大街新园茶馆,则是铸造工的天下。这些茶馆,在成都很为出名,以至于雇主在茶馆里就能雇佣到某个工种的工人。
文明雅集
在上海九江路口的小花园附近,有一家茶馆,名文明雅集,系书画名家俞达夫所开。这家茶馆,不仅名称典雅,而且室内陈设雅致,环境布置得体,茶具选用讲究,有一种不落俗套之感。因而,它所接待的大多是斯文人。
一般而言,接待某一种职业、某一个阶层品茗的茶馆,其开设、经营者的地位,与他们所服务的对象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一些黑道上的人物,专门开设茶馆作为联络各方同道的媒介,也就不足为奇了。
“立码头”
袍哥是活跃于民国时期的一个主要的帮会。他们之间的见面仪式,除了正规的在香堂里举行之外。还有一种是在地方性的袍哥集会地——茶馆里进行的。通常,地方上的各帮主,都开设有各自的茶馆,名为“立码头”,实际是袍哥送往迎来、广为结纳的活动中心。在这里,饮茶品茗已经蜕变成了帮会分子借以扩大力量的一种手段了。
青帮在商埠口岸处开设茶馆以资联络的情况,与袍哥大同小异。季云卿是20年代著名的青帮老头,久居上海,门徒众多,能与上海三闻人分庭抗礼。1928年,为寻找英国一外交官失窃的重要文件,他专门到汉口走了一趟。由于他深谙帮中门道,一到汉口,便到江边的大茶馆得意楼里坐定待茶。季氏所去的得意楼,确非一般茶馆,它是由汉口一个青帮老头子杨某所开的秘密联络点。因此,当季云卿落座,将茶壶茶杯摆出青帮中会友的格局后,茶馆里的跑堂就知道了他的身分,并把他领到老板家里相见。由于英国外交官的文件袋恰巧是杨氏的门徒偷去的,季云卿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回了重要文件。说起来,季氏汉口之行的成功,茶馆这种联络点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茶馆开设者的不同,决定了其服务对象上的差异。但是,不管茶馆有广式、苏式、杂式等的分别。还是有雅俗、贵贱方面的等差,其作用基本上是相同的。
茶馆功能之一:休闲场所
茶馆的主要功能是休闲场所。最初,茶馆是为官僚、士绅等社会上层服务的。这些人聚集一处,饮茶品茗固是要项,但借此消闲也是一个主要方面。迨至茶馆推向民间,其消闲作用愈益减小,休闲作用逐渐增大,茶馆也就成了劳苦大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休整一下的极好去处了。
在上海,有一种吃包茶的名目。所谓吃包茶,就是饮茶者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到固定的茶馆里,在固定的茶桌上用茶,并支付固定的茶资的一种饮茶方式。由于这种方法,较一般到茶馆去用茶来得合算,因而深得收入微薄的大众的青睐。可以说,吃包茶是茶馆所起的休闲场所作用的一个绝好体现。
如果说,茶馆作为休闲场所,只是为劳苦大众提供了一个苦中作乐的场所的话,那么,它作为娱乐宫,就纯粹是为有闲阶级增加一个活动处所罢了。
在茶馆这个娱乐宫里,有的活动是比较粗俗的,有的则相当高雅。在上海豫园,有好几家茶馆,除了一般用茶者外,还有许多养鸟人聚在一起。每天清晨天刚亮,养鸟人便拎着鸟笼到茶馆里“冲鸟”。他们把各式鸟笼挂在茶座前,一边品茶,一边听着啁啾的鸟语,以此寻求乐趣,消磨时光。
还有不少茶馆的娱乐活动,不似冲鸟喂食这般低级、市侩气息浓,因而引得不少文人雅士也乐此不疲。上海豫园的春风得意楼‘既是一个啜茗饮茶之处,又是一个影响颇大的书场。凡是到上海来说书的艺人,首先必到这里说上几场作为亮相。这里,通常要演日夜两场,书目有《三笑》、《杨乃武与小白菜》等,都是当时十分流行的。有时,每天两场还不敷所需,于是只得另加早场来补不足。
上世纪40年代,李德才在四川蓉城中山公园的茶馆里表演“打扬琴”的节目。他在当时以雅美的词曲、声情并茂的表演演唱的描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自由恋爱故事的《凤求凰》一曲,至今还被人忆起。并作为“茶馆里的说唱艺术”的典型。
由于地区的差异与中国方言民俗的不同,茶馆里的说唱艺术也各不相同。南方以独脚戏、评弹、道情为主,北方则以说书、京韵大鼓、京剧等为主。陈封雄在回忆他叔父、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时写道,有一天,陈寅恪忽然带他去东安市场的一个茶馆去听说书和京剧清唱。他听得津津有味,大出其侄子的意料。
除了说唱艺术外,茶馆里的娱乐活动,还有射虎、画展、兰展、菊展等。这些活动,与说唱艺术的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是:说唱艺术大多由专门的艺人为品茗者表演。而射虎及一些展览,则由用茶者在自娱自乐中得到享受。
茶馆功能之二:交易所
成都的茶馆在全国享有盛名,因而在民间有“天下茶馆数中国,中国茶馆数成都”的俗语。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大多为行业、会社的聚首之地。商贾、贩子在这里了解行情,洽谈买卖,成交看货。茶馆俨然成了他们的交易所。
事实上,把茶馆作为交易所的,不只是在成都。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茶馆,大多有这种功能。上海春风得意楼,名为茶馆,以茶招揽顾客,实际上,光顾此地的人,并非专为品茗而来,绝大部分是以此为场地。进行各种活动的。这里最主要的一批顾客是商人。每天早晨,布业、糖业、豆业、钱业……各行业的商人,都到此交易论市。这样。茶馆便成了他们晤会、应酬、谈交易的理想场所。
在这批商人茶客中,有一种被称为“白蚂蚁”的经纪人。他们也是每晨必到,把这里当作交易市场。“白蚂蚁”是专门撮合房屋顶租交易的中间人。由于他们是从交易中提取佣金为生的,因而利用商人聚集的茶馆,趁品茶之机介绍生意,就成了他们特殊的活动。
在旧日的都城北京,茶馆里也存在此种情况。据《旧都三百六十行》载,在北京,凡介绍买卖、典质房地与租赁房屋者均称为“拉房纤的”或“跑纤的”。操此业者,每天出入于大小茶馆之间,专门打听何人要出售或出租房屋,何人想购买或租赁房屋,然后代为奔走,从中撮合。他们以茶馆作为交易所,用意与其他地区是大同小异的。
茶馆的交易所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上的,但也不乏反映在政治方面。常熟的琴一楼茶馆,貌不惊人,然在上世纪20年代,却成了名噪一时、能左右全县政治、经济形势的“小楼内阁”。当时,常熟各界实力人物钱南山、张美叔、邹朗怀、蒋瑞平等十余人,常常聚集在琴一楼茶馆,以品茗为名。暗中进行政治交易,因而控制了全县的政治、经济命脉,以至于在1926年所进行的一次县政府改选中,当选的大部分是他们的嫡裔。中国人把茶馆作为操纵政局、进行政治投机的交易所,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
茶馆功能之三:联络点
民国时期,帮会的活动很为频繁。但由于一向以来,帮会基本上是作为不合法组织而存在着的,因而它的活动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帮会的这种自我保护的努力,在民国时依然十分讲究,以至于各地帮会成员之间的接洽,还非得借助诸如茶馆一类的联络点不可。
茶馆作为帮会的联络点,有一套独特的联系方法。尽管这一套方法,对于不同帮会而言,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着差异,但它利用茶馆本身的氛围,借助茶馆里既有的器具实现不同地区间同道之间的联系,则基本相同。
青帮成员每到异乡客地,先去的总是当地码头的茶馆。当外乡的青帮门徒按帮规,把茶碗盖或帽子仰放在桌上,伸出左手三指或右手四指端起茶碗时,当地的青帮成员便会前去跟他攀谈。他们间一问一答的交谈,是以切口或暗语进行的,局外人难以理解其中的含意。但对青帮成员来说,这却是一条相互沟通的纽带。只要他们的暗语或切口一对上号,他们的关系就算接通了。
当然,把茶馆作为联络点的,并不限于帮会。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江南游击根据地的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日伪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保存好革命的火种,与一些由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赤色群众开设的茶馆所做的掩护工作是分不开的。
茶馆在联络点作用上的两重性,并不是茶馆的本质特性。茶馆本身是没有倾向性的,但是,当不同的政治力量,借助茶馆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时。茶馆带上一种附加的政治色彩就完全不可避免了。
谋生之地
自古以来,茶馆就是一个人多势杂之所。不同的人,到茶馆去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对于富有者来说,茶馆是逍遥津、寻欢作乐处;而对于绝大多数穷人来说,茶馆则是他们解除疲劳,甚至是藉此谋生之地。
民国时期,北京的不少工匠迫于生计,要专门到茶馆去招揽活儿,当地称为上街口或上口子。上口子的人,大多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处所的瓦匠、厨师等。由于他们靠自己家门口张贴的招牌,难以获得生活必需的经济收入,因此,在每天清晨去茶馆,以喝茶为名打听生意。就成了他们日常的功课。
与他们同样处在生活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另一些人们,因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只得靠在茶馆里兜售点心、瓜子、糖果,以及卖唱、耍弄杂技为生。尽管凭这种买卖是不足以谋生的,以至于在茶馆忙时,他们还得充当暂时的伙计,帮助茶馆照料客人,从而得到主人的一些照顾。但此项小本经营,终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收入,所以一年到头,总有不少人置身于茶馆间、穿梭于茶客中。
茶馆的特殊功能:“吃讲茶”
在茶馆众多的功用中,还有一种是很为独特的,那就是“吃讲茶”,把茶馆当作调解纠纷之处。所谓吃讲茶,就是争斗双方借吃茶讲理,化解纠葛。通常,争斗双方在调解人的劝解下,是能达成某种谅解,并使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淡化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吃讲茶都能平息双方的争端。在吃讲茶之时,因言语不合而大打出手的事并不鲜见,因此,不少茶楼,宁可损失些茶资,也要挂出写着“奉宪严禁讲茶”字样的木牌,以免遭受无妄之灾。
民国年间,以创办大世界闻名的上海商人黄楚九,各种生意都做过,就是没有办过正式的报纸,因而跃跃欲试,想以接办不景气的《时事新报》加入日报公会作为进身之阶。对此,主持《神州日报》笔政的汪瘦岑大为不满,便利用报纸揭黄的老底。由于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但道理在汪一方,因而黄只得请上海商会会长朱葆三出来做鲁仲连。汪时常去味莼园喝茶。一天,他才觅位坐定,朱葆三便走过去对他说:你来得正巧,我介绍一个朋友和你谈谈。说完就从近座中拉过一个人来,说这位就是黄楚九。黄见了汪,装得非常谦恭。经过双方交谈,又加上中间人的调解,黄、汪达成妥协:黄不接办《时事新报》,汪停止在报上对黄进行攻击。这场争执,就在“吃讲茶”中消弭。
民国时的茶馆,对于社会各界所产生的吸引力和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恐怕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文人骚客,都认同茶馆这一俗文化现象,并借此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