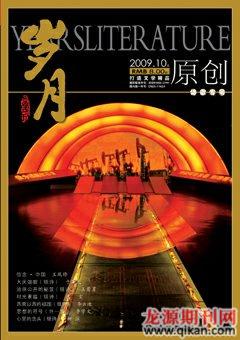写给大庆的歌(组诗)
2009-10-28 07:01陈宗华
岁月 2009年10期
陈宗华
大庆不再是一句口号
我渐渐走出儿时的口号
深情地注视着大庆的磕头机
因贫油而生机不息
新兴的城市在曾经的荒原
是否遍布饿狼的眼睛
那时也许真的很穷
北中以北
蔓延全国的苍白
紧迫着我父亲的壮年
争分夺秒 至今还在
你摸一摸就知道他们浑身是铁
那密布的管道完善了大庆的经络
动脉源于深层的远古一次一次
生死轮回 血液变得黏稠而张力
激动的岁月 白菜和大豆
同时传承到我们肩上
父亲挥着他的余辉
将生锈的那几个铁字擦亮
漆上红漆放进他的卧室
——“工业学大庆”
也不再是我儿时的口号
圆月终归要下山
朝阳正要从东方升起
湖泊凝聚的城市
多么豪迈的称谓 大庆多湖泊
不论大小 一律都叫“水泡子”
宅居环“泡”而立 夜光倒影
良辰涟漪 美景如玉
何时一河贯穿百湖疑似在“威尼斯”上行船
望不尽草原的嫩绿托起天空的明净
看不够磕头机的调速驱动红彤彤的朝阳
向过去的荒原致敬!
龙凤湿地
绿草间 不规则的水泽
反着绸彩的涟漪
丹顶鹤悠闲地踱步
芦苇丛中的窥视
按下纯洁的快门
泥鳅偶尔从脚心滑过
心痒痒地
我却对一头称为水怪的鲶鱼产生了好奇
猜你喜欢
中国宝玉石(2021年5期)2021-11-18
少儿美术·书法版(2021年8期)2021-10-20
科教新报(2021年22期)2021-07-21
海峡姐妹(2020年11期)2021-01-18
红楼梦学刊(2020年5期)2020-02-06
小雪花·成长指南(2018年2期)2018-03-16
创新作文(小学版)(2016年11期)2016-11-11
太空探索(2016年2期)2016-07-12
延河·绿色文学(2016年8期)2016-05-14
中国火炬(2013年9期)2013-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