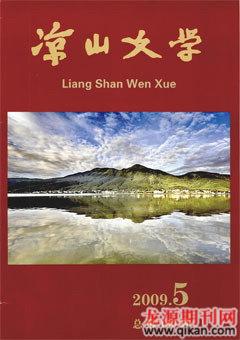矛盾中求和谐
钟继刚
语言是一种文化阐释,文化是人类观念性的存在形式,文学免不了作为意义世界对生命的存在和运作予以关注。九十年代大肆呼唤人文精神,其实质是一种生命观照,给混乱无序的人生寻求一种整饬的、审美的秩序,充分完善生命的自由形态,这在文学早已有之,只是不那么理性罢了。在四川凉山,蔡应律的文学地位是不能忽视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其文学创作较为丰富,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随笔等多有涉及,作品刊载在《诗刊》、《星星》、
《小说界》、《青年作家》、《萌芽》、《四川文学》、《现代作家》、《凉山文学》等杂志及一些报刊上,并先后获过一些奖项。1992年以前以小说创作为主,之后偏重社会随笔,蔡应律的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写实成分更重,但他对社会人伦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对理想人生的呼唤同样表现得非常强烈。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的心灵内部,常有很多不协调、矛盾的成分,如何消除人类面临的各种矛盾,建立和谐之境,这是蔡应律笔下思考的严肃问题。
蔡应律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他的小说,当然,文体形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文本世界的断裂,作家对人生的体悟和思考自有一致处,蔡应律的随笔是他小说的延伸和补充。只是小说内蕴,而随笔外显,本文拟将重心放在他的小说,把随笔当作必不可少的补充,其他文体形式的作品则相应搁置,探讨蔡应律小说世界及随笔世界对人生、社会的思索。
文本世界不等于现实世界,但不是不联系着现实。蔡应律的小说总体来看还是走的现实主义道路,创作题材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亲密关系。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与其人生经历、精神结构和审美情趣相关,甚至他要给文本以什么样的阐释也大致可以揣摸。写重大事件,重大人物的文学时代已经过去,小说并不靠这些来奠定价值,“文学是人学”的关键在以具体的人为目的,不是为图解政策,也不是为粉饰太平。更充分地诠释和逼视心灵的恰恰是容易忽视的日常生活,一切的苦难在此凝聚,一切的理想在此滋生,在这一点上,蔡应律深得其中三味,常深入当下,通过对普通人事的选择和组建,展现形形色色的人生,阐释人类生存的诸种形式,揭示人生面临的诸种问题。《旱魃》、《江流》、《楔子》均在展现无意的自然对人伦的破坏和伤害;《月亮》写一个单纯的保姆在人际关系中的挣扎及其美好心灵;《深山里的喜事》将落后山寨的地方陋习对人性的压抑及人们对和谐人伦的向往展示出来;甚至像《落雨的天气》借司机与乘客的小小冲突,思考的也是很严肃的道德问题;《浴室》展现脆弱心灵在无情岁月下的自卑及伤害;还有《断桥》、《过第一个教师节》这样一类触及教育问题的作品,多为农村题材,因真实到可怕的地步,生存实相获得一种深度的坦露。
但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复制生活,以审美的文本使读者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在相对超然中进入现实背后,揭露人生真实,触摸灵魂深处,这才是文学主要的目的。日常生活杂乱而无联系,有客观的价值而少审美的意味,蔡应律的方式是常以单一的叙述视角和选取某一重要事件为中心向外辐射或向内伸张,达到小说世界的凝炼和对现实世界的超出,“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
“向外转”或“向内转”并不是固定的、相互排斥的,故事、情节、事件是人物活动的轨迹,是人物塑造的载体,蔡应律并不满足于此,常将笔触伸到日常生活中人物的心理层面,平常事、不平常心,努力揭示人物深处的心灵内涵。确定的事件、行为并不证明精神世界的确定,同样的“老年瘢”,有人将之作为岁月的侵蚀无奈地接受下来,有人千方百计想拒绝这一事实,遂有《老年瘢》的心态。《浴室》、《老弯和他的狗肉摊子》之类短制小作,重心仍在心理世界的追问,竭力展示灵与肉的冲突,深入丰富的人性深处,其叙述常执着地穿梭于人物的心理层面,陶东风说,“小说叙述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也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更是人类经验、理解、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文体·语言·文化》),当理论家如此说着的时候,作家们却早已做出了。蔡应律的小说人物常困扰于心灵,苦难与幸福、快乐与道德、怀疑与肯定相互斗争,导致人面临的窘境,从人物生存的窘困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人物被作家有意地推到环境的面前,推到行为决断的边缘,人物随之陷于两难,活动主体与外部环境明显地不相容,根源在于对象世界与主体欲望的相悖,作为个体的人常被抛离社会、自然、人群,个体的欲望经受着社会法则、自然环境的打击和限制,人成为可哀的存在,反映出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与灵魂世界的反复追问。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1988年发表的《尤股长》都是一篇不协调的小说。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的七扭八拐、人事紧张予人的烦躁与晴朗无云的蓝天和清新活泼的儿歌形成鲜明对比,自然的清新纯朴常为人修饰了来作忍受现实的后盾,作家常诗化那想象中的自然而在心灵保持一份疏离现实的审美的超然,但作品不像。社会与个人也不协调:执着认真的尤股长与漫不经心的人事环境相矛盾,尤股长一些小事化大的行为免不了碰壁,像堂·吉诃德式的认真和滑稽。凸出可笑的庄严,夸大尤股长与社会群体的行为习俗之间的矛盾,如阿瑟·波拉德所说,“敏锐地意识到事物怎么样与事物应该怎么样之间的差距”(《论讽刺》),又两不否定。承认社会的现状,也同情尤股长的执着。尤股长最后大意淹死,与纷扰的社会彻底脱离,一边是悲凉的死亡,一边却是清亮的鸟叫、简朴的儿歌和葱郁的“怀乡之情”。活着不容于社会,死了不容于自然,尤股长几乎只是一个反讽的符号,从出现到死亡,只是自我否定的过程,他的执着只增加他的虚妄和悲剧意义。全文无一字正面描写尤股长心理,但味之远穷的心理世界却凌胜其他注重心态描写的作品。
因尤股长与社会、自然的不和谐而生悲悯之情,潜在地呼唤一个和谐的理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之一就是无可置疑地对某种永恒法则的坚信,无论歌赞现实,描写人性的美好,还是批判现实,揭起那丑陋的一面。蔡应律揭起心理的矛盾冲突为的是消灭矛盾和冲突,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双方走向融合,追求心灵的和谐和超越之境。永恒世界可使现实人生获得超验的意义,永恒的和谐可在纷然的世界建立起审美的超然之境,不一定实在,但更加优美。《回声》一文展示了人与自然从对立走向凄美的和谐。主人翁是山林的强人,他的力量体现在与自然的对立,对猎物屡次成功的捕捉,但也是缺少爱、内心焦躁的弱者。小说以“他”为叙述中心,让他在过去的回忆和与母獐相对的现在时之间往返奔波,采取全知视角,将他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都裸露无遗”(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既有对猎物和哑巴女人暴烈的征服欲,以此发泄压抑囚禁的焦灼;也有对爱、对美好人伦的呼唤,表现在“他”面对母獐的那种软弱,
“他多愿和它亲近,和它友好,和它坐下来看山,看云、看雾,看夕阳和彩虹……”,因一头母獐亦完全消融了人对自然的仇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并以人的最终死亡完成了人性的升华。人与自然由对立走向和谐是一寓意;另一寓意则是:母獐只是一象征物,在“他”眼中成为母爱的化身,小说深处呼唤的是人伦的优美,而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协调。
现实提供的是比理想复杂得多的世界,非善即恶的评判方式并不客观。《替身》是一篇道德评判小说,与贾平凹《天狗》在题材选择上异曲同工,但结局处理迥然相异。曹金英与一个瘫子相守十几年,身心所受折磨不少,对朱半山的眷恋在情理之中,瘫子竟恶意地毒杀了朱半山,曹金英的郁闷与屈辱同时进发,丧失理智地将瘫子置之死地。法律以结果论断,道德还虑及环境、动机等因素。行为只是作为处境的产物,处于被动选择地位的人物常是道德同情的对象,犯罪的曹金英又是人性大受摧残的曹金英。《替身》将人与人的关系作了悲哀而怜悯的展示,要评论人物就得陷进伦理的困惑。《主体》叙述了一出“错位”的尴尬,妻子有成就,导致丈夫自卑;怀抱传统观念与现实相撞,悲哀、失落、恐慌,免不了受伤。《深山里的喜事》以藤藤与肖银贵的婚事为主线,聚结了僻远山村凉风岗和肖家屋场的嫌隙与对立。从爱情角度折射伦理冲突的产生和发展,挖掘到老少两代人在村寨冲突中承受的打击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呼唤建立人伦理想的愿望极切。人物纷纷被推上圆满的结局,彰显了山村人性伦理的素朴与优美,淡化了悲剧成份。《断桥》、《月亮》淡化情节冲突,着重展现素洁美好的心灵世界。《断桥》语言清新,人物简洁,将诗情画面作间断性的闪现,使叙述富有节奏和韵律,相得益彰地描摹出几个受陶老师影响的孩子在单纯明净的世界里的朴实,美好的人伦理想得到完整的阐释。
小说是虚构的世界,并不就表示不诚实。审美理想的产生和诠释都无法排除社会生活的影响,作家的使命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更深刻地探寻人类的生命轨迹,用审美的理想打亮现实的人生。蔡应律对社会的关注,常以忧虑的形式表现,有时甚至压抑不住,时不时从隐指状态现身出来,直接表白自我的观点。这种叙述形式的操作逐渐将作者推到现实面前,与现实直接对话,小说语言的客观化和审美化相应淡化,而化成杂写杂忆的社会随笔。
以1992年为界,蔡应律创作转变的脉络是清晰的,从小说转向随笔,从叙述语言转为议论语言,从客观转为主观,从隐蔽转为明朗,蔡应律按捺不住情绪的流露。社会现象以它繁多、纷乱的本来面目不断摇撼作家的安稳心态,为了拒绝颠覆,免于吞噬,作家们乃采取与之相对相抗的姿态宣布自己的位置,遂对诸多社会现象发愤激之语,在否定的语境中确证主体的力量。表现于作品,则是作家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各类社会现象赋予人生的形态,不符合理想的,就现身干预,“我们的人文理想越炽热,我们的存在方式就越危险,越有侵略性。”(《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读书》1994年第3期)理想欲望强烈,则急功近利些,重情绪,少节制,实际上,理想在情绪激烈的时候远离了主体,成为一种模糊的尺度,不知道什么是,但可判断什么不是,这样,作家省了许多功夫,可以运用随笔的短、平、快特色,迅速伸到各社会领域,对理想构筑、因果联系的思索相应减少。《凝视一张照片》带着现实的关注,深入历史内部,发掘民族灵魂的强劲及衰弱,也将现实中的弊端一一照出丑陋,以警世人,忧患深入文字。《嘴为何物》贬责当今泛滥的吃喝风,《“级”的玩弄》批评不正常的虚伪心态,《上帝的滋味》在消解人生苦味的劝慰语里满蕴着苦味。《谁来保护泸山邛海》愤责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吁请保护。心有所感,事情无拘大小,皆可人题,蔡应律的随笔世界涉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生活、甚至服装、吃食之类日常琐事,琳琅满目,色彩纷呈。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中指出:讽刺是一种伦理。而“伦理学属于实践的科学,它的职能就是展示人生必须以何种方式度过,以实现它的目标或目的”,“立足于对一般人性的知识。目的在于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使生活达到最充分、最美好和最完善的发展。”包尔生甚至称之为“普遍的营养学”(《伦理学体系》)。讽刺的伦理是从否定方面来评析世界,它照见社会的伤口,抑恶是为扬善,以针贬丑来达到完善美的目的。蔡应律关心公益的精神无时或灭,促使他尽其所能去“修补”社会的缺陷。屈原以降,中国文人一直秉有一种“政治情结”,身在局外而操局中人的语气和关切,非为多事,乃为良心驱策,《给教育试开一个处方》曾掀起不小波澜,无病之人不怕说病,社会人士对教育或其他社会现象发表言论,有他的自由,当事者不以之检视自身的缺陷,反悍然指责,讳疾忌医的古风犹存,可不又是一篇可“随”之笔吗?面对社会众生,深思人类生存,作家当有我为天下而生,天下为我而存的自我扩展意识。从《服装是啥东西》的日常琐屑到《遥望莫斯科》、《血染的和平鸽》,已超越小我,为人类生存而忧,沧桑的文字下跃动着拳拳赤子之心。正是这种思索赋予生命庄严的意义,人在思想状态才将生命纳入意识层面,才有切肤之痛的真实感。但由于作者情绪激烈,思考难以冷静,再加所论题材的浮泛,认识往往难以深入,有为事造文的痕迹,这是不少随笔作品的遗憾。
一个人与现实保持多远的距离,也就进入与之相应的世界。随社会阅历增多,蔡应律生了更切的关注之心,或否定或肯定地与之对搏,但并未超拔于世,而是身在泥塘的藕心,因池泥的粘附牵扯而生急功近利的改造之心,小说世界向现实世界倾斜,等于审美理想向功利世界倾斜,人情味浓了,文心少了,于作家乃是一种损失。当然,无论蔡应律的小说还是社会随笔,都是其人生理想或清晰或模糊的呈现,因并不流俗的真诚坦率与现实相应疏离。因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之心又与现实相粘联,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对平凡生活的内在热情,对社会公德的持续呼唤,正是这世间难得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