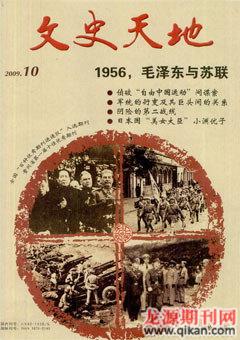白衣山人李泌
李德生
七龄童子名动京华
李泌,字长源,祖上是北魏达官,入唐以来,徙居长安,李泌的父亲李承休以藏书著名,这种家庭环境为他的早年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泌七岁就已经能够赋诗写文章。这一年,唐玄宗举行了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让他们在朝堂上彼此辩难。会场上一个叫俶的九岁小孩力压群雄,把其他在座者驳斥得哑口无言。唐玄宗很惊讶,问俶是否知道还有和他一样聪慧的小孩。俶回答说李泌。玄宗马上命人去请李泌。李泌到来的时候,玄宗正在和燕国公张说观看下棋。张说当时担任中书令,不仅负责朝廷诏书诰令的写作,而且诗文也非常出名,和另一大臣苏颞并称“燕许大手笔”。玄宗叫张说测试李泌的才能,张说出题以“方圆动静”赋诗。李泌想了想,请张说做个示范。张说看着棋盘,随口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听完脱口而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客观地说,这两首小诗都是一时即兴之作,尽管李诗的立意远远超过张作,我们也不能说他的才能就可以胜过张说。但是李泌的才思敏捷给玄宗君臣留下了深刻印象。
经此一试,李泌的名声迅速在长安达官贵人中传开。宰相张九龄对李泌非常喜爱,经常领他到自己家里聊天玩耍,甚至处理公务时也让他在旁。宰相身边自然不乏能人,当时深得张九龄欣赏的有两个:严挺之和萧诚。萧诚言辞巧妙,态度柔顺,很会讨上司欢心,而严挺之则认为“巧言令色者,鲜矣仁”,经常劝说张九龄远离萧诚。有一天,张九龄在家想到这两人,不觉自言自语:“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打算吩咐下人叫萧来陪他说话。这时在他身边玩耍的李泌突然说道:“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张九龄听了大惊,意识到自己的不是,马上改容谢过。从此,张九龄不敢再把李泌当小孩看待,改口称他为“小友”。
运筹帷幄平叛安史
李泌长大以后,喜欢上了神仙不死之术,经常去嵩山、华山、终南山游历,希望碰到传说中的仙人。这时他的学问更加渊博,尤其精通易经,唐玄宗给了他翰林供奉的职衔,让他陪太子(后来的肃宗)读书。李泌与太子的交情甚好,但不久就因为遭到杨国忠嫉恨而挂冠出游。
安史乱起,唐玄宗避难。四川,肃宗(当时玄宗任命他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在灵武即位,随即下令寻访李泌。李泌在得知叛乱消息以后,也决心为国效力,不避危难自己找到了肃宗。李泌和肃宗谈起天下大事,肃宗非常满意,打算授给李泌官职,李泌不接受,而是以布衣客卿的身份为肃宗出谋划策。肃宗对他非常信任,讨论一切军国大事时都要听取李泌的意见。有时肃宗出行,竟然和李泌同乘一座銮舆,看见的人都说:“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
肃宗问李泌如何才能平定安史之乱,李泌首先分析了战略前景:一,叛军把所有掠夺得来的财物都运回范阳老巢,可见根本没有统一天下的抱负;二,甘心参与叛乱的中原人很少,多数是边疆少数民族,这说明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民的支持。因此,尽管眼下叛军声势浩大,但只要我们策略得当,不出两年就可以平定。接着他详细提出了作战方略:“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翦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应该说。李泌的这个方略是非常高明的,它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故意不切断叛军老巢范阳与长安(长安和洛阳号为两京,当时都已经落入贼手)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叛军兵力分散,在千里战线上疲于奔命,这就把战争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肃宗最初认为李泌说得很有道理,等到他身边汇集了大批各方赶来的军队以后,急于求成的心理就占了上风,“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他不听李泌的劝告,指挥重兵一举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种做法虽获得了表面上的政治效应,却造成叛军主力汇集,为祸八年之久才得以最后平定。
尽管自己设想的最佳平叛方案没有被采纳,李泌还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全心全意贡献自己的才智。他的付出得到了有识之士的肯定,时人柳现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新唐书》作者也肯定了李泌“先事范阳”的平叛策略。
皇室矛盾巧妙斡旋
封建皇权所能产生的巨大政治利益使得它身边充斥着流血与阴谋,古往今来为了争夺皇位而发生的骨肉相残数不胜数。应该指出,皇位能否顺利交接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皇室家务,它严重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和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在国家遭受动乱的形势下,皇位的不安定因素危害更大。李泌洞悉政治人物心理,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总是仗义执言,巧妙斡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唐肃宗的第三子建宁王李倓性格英明果决,雄才大略,他跟随唐肃宗从马嵬向北行,因随行兵力单薄,屡次遭遇强盗,李恢亲自挑选骁勇的士兵护卫在皇帝身边,拼死保卫肃宗。肃宗有时逾时未进食,李恢就悲伤得不得了,军中上下为之瞩目,后来肃宗想封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东征。李泌说:“建宁王确实是元帅的人才,然而广平王(李豫,初名傲,即后来的代宗)是长兄,如果建宁王战功大,难道让广平王成为第二个吴泰伯吗?”(泰伯是周太王长子,知道父亲喜爱弟弟季历的儿子昌,也就是后来的文王,就和弟弟仲雍逃到荆蛮地带,建立吴国)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以后的皇位继承人,如何去担当元帅的重任?”李泌说:“广平王尚未正式立为太子。现在国步艰难,众人所瞩目的对象都在元帅身上。如果建宁王立下大功,陛下即使不想立他为继承人,那些同他一起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肯罢休吗?太宗太上皇帝(李世民)就是最好的例子。”肃宗最终任命李豫为元帅,要求诸将服从他的号令,并且任命李泌做元帅府行军司马。李倓听到这件事,向李泌致谢说:“这正符合我的心意。”
安史乱起,肃宗在灵武自立为帝,当时声称为了平叛,需要权威来镇抚诸军,由于没有经过正式的皇权授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收复长安和洛阳以后,唐肃宗曾经上奏远在四川的玄宗,请玄宗回京,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当太子。李泌听说以后,断言玄宗不会回来。肃宗向他问计,“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肃宗奏章,果然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直到接到李泌起草的奏章,这才高高
兴兴地回去当了“天子父”。
唐德宗时期,李诵(即顺宗)为太子,李泌是宰相。当时太子妃的母亲郜国公主因为蛊媚罪而被幽禁,德宗因此而责备太子,太子惶恐不知所对。德宗还多次在李泌面前称赞另一个皇子舒王的贤能。李泌见微知著,知道德宗有废除太子的意图,因为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太子是无辜的,所以他态度相当坚决,反对德宗借此废除太子。由于他言辞激烈,多次进谏,大大触怒了唐德宗。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重大威胁时,李泌并不因此退缩,他说:“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很明显,李泌为太子的事情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因为再聪明的人也不会拿近在眼前的灭族之祸去赌未来的可能回报。何况疏不间亲,古有明训,以诸葛孔明之贤,在荆州时都没有正面答复刘表父子之间的问题,李泌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父子骨肉之间,都挺身而出,仗义直言,调和其矛盾,确实难能可贵。《新唐书》作者在对李泌做出否定评价的同时,笔锋一转,说李泌“明太子无罪,亦不可诬也”。这种肯定更为实在。
为人谦退为政有方
李泌虽然到唐德宗时期才正式当上宰相,但由于他与肃宗、代宗的特殊关系,事实上他参与了很多时期国家大事的决策。正如德宗自己所说:“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考察李泌的一些事迹,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态度和为政方略。
李泌为人谦退,于名利之间看得比较淡薄。对于人臣至尊的宰相高位,李泌就曾经多次辞让。肃宗在灵武时,想授给李泌右相。李泌固辞。代宗时,“欲以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辞”。德宗在正式任命他为宰相时也说:“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也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皇帝下令恢复实赏,名将李晟、马燧、浑碱想把自己获得的封赏让给李泌,“泌不纳”。
李泌的谋略得到了后世的公认,许多复杂棘手的问题到了他的手里,就变得简单易行。德宗贞元元年,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杀了节度使张劝,自己总理军务,并要求朝廷下令承认自己的地位,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还暗中勾结李怀光部将达奚小俊为援。这种行为无异于谋反,朝廷当然无法容忍。德宗深知事态严重,授予李泌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的职衔,叫他亲自去处理这件事情,并问他需要多少兵马。李泌说:陕城地势险要,如果用兵,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够攻打下来,我一个人前去就可以了。德宗大惊,详细询问原因。李泌分析说:我估计当地军民并不是都想参与造反,这件事情应该只是少数首领人物的行为。如果朝廷大军压境,则可能引发当地军民的一致抵抗。现在我单骑前往,达奚抱晖想动员军民则没有名目,毕竟他们没有公开宣称造反,如果只派下级军官来杀我,说不定我还可以说服这些军官。现在陕城旁边的河东军将领马燧就在京师,皇上可以下令他与我同时离京,这样陕人如果想加害我,还要担心马燧的军队讨伐,我此行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德宗还是担心李泌的安危,声称宁愿丢失陕州,也不能冒失去李泌的风险,打算另派其他官员前往。李泌说:其他官员可能根本到不了陕城,这件事处理的关键在于当机立断。趁着当地人心未定的时机突然出击,一旦达奚抱晖牢牢控制了局面,那就无法挽回了。德宗最终同意了李泌的建议。李泌在京师就放出风声,宣称此行只是为了押运江、淮粮食,顺带考察达奚抱晖,如其可用,朝廷就正式授予他节度使的官职,将来如果立了功勋,还可以继续封赏。抱晖得知这一情况,心里稍微安定。李泌出了潼关,鄜坊节度使唐朝臣声称奉了皇帝密诏,要带三千兵马护送他去陕州。李泌坚决不让军队跟随,孤身单骑往陕城而去。进入陕州境内,抱晖不让手下将领迎接,还一路派出探子侦探李泌动静,李泌对此都视而不见。临近陕城。抱晖手下的一些将官不听命令就来见李泌,李泌知道自己的判断正确。到了城郊十五里的时候,达奚抱晖才亲自出来迎接,李泌对众人说:抱晖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出来稳定人心,保全城池,这是有功劳的,请大家不要把闲言杂语放在心上,安心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抱晖听了很高兴。李泌进城以后,也只是过问一些民事上的问题。对于一些想私下求见他的官吏,李泌一概拒绝,宣称:在这种特殊时期,难免会有很多传闻,我不想听流言蜚语。李泌的这些表现让那些参与叛乱的人们都安下心来。等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李泌这才单独召见了达奚抱晖,说清楚厉害,劝其离开陕州,抱晖只好接受。一场弥天大祸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之中。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实力严重削弱,地方藩镇势力则急剧膨胀,成为中央王朝的极大威胁,边疆少数民族也多次提出无理要求。在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李泌总是极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权威。唐德宗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部下造反,德宗被迫离京避难。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也聚众反叛,加上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日:‘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对国内的悍将态度如此,对国外强敌的态度也如此。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平叛过程中,吐蕃不但没有积极作战,还趁机把武功地区抢劫一空。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打算同意,李泌坚决反对,他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吐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除此之外,李泌还劝说德宗联合回纥、大食以困吐蕃而安定边陲,由于德宗对回纥向有成见,李泌不惜反复申辩上奏达十五次之多。
李泌还极力保全一些遭受诬陷的朝廷大臣。当时朝廷的军事柱石有李晟、马燧等人,由于地方统兵的节度使将领屡屡叛乱,皇帝对统兵大将疑忌很深,有件小事情很可以体现这种紧张关系。李晟在长安的府邸中有一片竹林,某段时间突然很多人议论起李晟的府邸,李晟听了以后吓出一身冷汗:竹林—藏兵—造反?想到这些,李晟赶紧命人把那片竹林全部砍光。李泌在拜相当月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他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希望皇上不要加害功臣!李晟和马燧为朝廷立过
大功,最近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皇上不会相信,但我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不再疑惧。假如皇上把这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其实,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皇上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毋需担忧,那么国家有难时他们可以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则卸甲闲散,这样不仅君臣和睦,还可以保证天下太平无事。这番披肝沥胆的话一说出,李晟和马燧当场“泣下”,德宗也诚恳地表示接受。由于天下战乱频仍,镇海军节度使韩混在其境内加强战备工作。由于韩混个性刚烈,不肯依附权贵,当时有很多人上奏称韩滉正在密谋造反,德宗也起了怀疑之心。这时李泌却告诉皇帝,他愿意以自己全家人的身家性命担保韩混不会造反。德宗劝说李泌:别人的事情怎么可以随便保证,再说你又不是韩混的什么亲故,何必呢?李泌说:从韩滉以前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朝廷忠贞不二的好官,如果平白遭受诬陷,恐怕更多的地方官员将会为之寒心,那样国家将会受到重大损失。我举家保证韩混正是为了国家的全局利益着想。后来事实证明韩混不仅自己没有谋反,还挫败了其他地方的叛乱阴谋,“上闻之喜,谓李泌曰:‘混不惟安江东,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谓知人!”
在许多政事上,李泌都显示出了过人的政治才能,如整顿漕运,恢复常官,罢斥冗员等,其中一件处理外国使节的小事最能体现李泌的机敏。唐朝因陇西黄河一带被吐蕃侵占,所以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有事来奏的人,以及西域来长安的使者,都无法顺利返乡。这些人及马匹的生活费,完全由鸿胪寺负担。礼宾则将这件事交给府县来负责,度支随时要付钱给他们,“不胜其弊”。李泌知道这些留在长安的外国人,时间最久的已来了四十多年,不仅已经娶妻生子、还买了土地房屋,有的甚至还开钱庄,生活过得很好。他调查得知有土地房屋的外国人共有四千多人,于是停止了对他们的供给。这些外国人前来投诉,李泌说:这都是以往宰相的过失,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听任他们留在京师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从今天起,可以借道回纥,也可以从海道,分别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就到鸿胪寺来说明,再授予职位,领取俸禄,做大唐的臣子,不能继续算是外国使者领取津贴。结果没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回去。经过这番整顿,需要鸿胪寺供给生活费的外国人只剩十余人,度支每年节省了五十万钱,“市人皆喜”。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李泌受四代皇帝宠幸,出入宫禁,执掌权柄,这难免引起其他大臣的嫉恨,因此,李泌也曾经多次受到排挤,被迫离开权力中枢。
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得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安置。李泌干脆脱离官府,“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自唐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虽然没有正式出任要职,却“权逾宰相”。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唐代宗即位,把李泌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娶妻,“欲以泌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权相元载见李泌不肯依附自己,把他看作潜在的威胁,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充江南西道判官”。后来元载被诛,李泌被召回,又一次受到宰相常衮的排斥,以李泌才干可以开化蛮荒之地为理由打发他去了偏远地区。
一次次被排挤,又一次次重新受到重用,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它对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考验是十分巨大的。我们没有看到李泌的怨言,只知道他每次辞官就去名山修道,而且还很有成效,可以长时间不吃粮食,“绝粒栖神”。我们不知道李泌是否完全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但他的进退出处,确实当得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八字考语。“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应该说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旧史给予李泌的评价是“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且不说李泌修道、好谈神仙是否有全身避祸,调节心境的因素,考察李泌一生的事迹,相信读者不难做出公正的评价。才女汪小蕴咏史诗说到李泌,有“勋参郭令才原大,迹似留侯术更淳”的名句,颇可参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