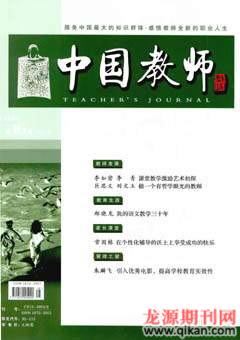叶圣陶先生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学生》杂志(下)
商金林
三、 “实质与趣味兼美”
1935年秋,叶圣陶在苏州滚绣坊青石弄造了几间平屋,搬回苏州居住。苏州离上海很近,交通又极为便捷。迁居苏州之后,他仍担任《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每月总有一段时间在上海开明书店,处理编务工作。青石弄在葑门附近,僻静得很。叶圣陶经常到苏州金城书店,“看看青年人买书踊跃的状况”,关心青年的进步成长。有一次,苏州文艺青年邀请叶圣陶在怡园举行一个座谈会。叶圣陶在会上说,近年来时势不同了,青年人都在追求进步,他看见了小学校中每天有时事报告,国内和世界各地发生的新事情随时会汇集到小心灵里头。他看见了中学生功课虽忙,报纸杂志不可不读,常识方面,比较20年前的中学生进步了。他看见了新书报很有销路。站在书店角落,好些人在那里贪馋地翻看陈列品,好些人专诚地跑来问:“某某期刊到了没有?”他们之中,至少十分之六七是店员学徒。他们在店里为店规所拘束,不能够公开看,只好把书藏在抽屉里或衣袋里,遇到相当机会,就偷偷地拿出来看这么一页两页。叶圣陶说他“知道从前店员学徒只看小唱本或‘哈哈笑之类,至多也不过看看《岳传》《三国志》之类,现在这突跃的进步并不是一个奇迹,乃是‘时势教育迫着我们每个人觉醒到不得不努力求知……现在有些人还是停留在从前的模型里。然而,时势转变越急,他们终于要直跳起来,一齐赶上进步的路,这是可以断言的”(白雪:《叶圣陶安居苏州》,刊《辛报》1936年10月19日第2版)。
正是这种要满足“觉醒”的青年人“努力求知”的热情,正是这种要使那些“还是停留在从前模型里”的青年人“直跳起来,赶上进步的路”的愿望,促使叶圣陶处处为青年着想。他和开明同人设立了“中学生劝学奖金”(奖金专作学费之用),以劝勉在校初、高中学生好好学习,还创办了“开明函授学校”,帮助广大失学青年通过函授完成中学学业。从1930年至1937年的7年间,叶圣陶先后担任了《妇女杂志》《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和开明《月报》“文艺栏”的主编,哺育了一代青年。以《中学生》为例,“为了替读者计划内容的充实,趣味的丰富”,叶圣陶“无时无地不竭尽着全般的努为”,“言论则务求能策励读者的奋勉精神;各科谈话则务求能指示读者以勉学方针;时事及科学则务求使读者与世界潮流接触;文艺及各种杂文则务求引起读者的兴味”(《一九三一年的〈中学生〉》,《中学生》第10号,1930年11月出版)。
“《中学生》是永远在进步的,而她的进步更有着一贯的轨道,从没看见她出过一次轨(这里所说的“从没看见她出过一次轨”,指的是从未登过一篇思想倾向性不好的文章——引者注),“她始终保持着一种诚恳的毅力为我们青年努力”( 陈詈《读一九三四年的〈本志〉》,刊《中学生》1935年1月号),“不但年年在改进,而且期期在企图着改进”( 忆秋《一九三四年本志概况》,刊《中学生》1935年1月号)。《中学生》先后开设过“中学生的出路”“出了中学以后”“致文学青年”“我的中学时代”“贡献今日的青年”“革命者的青年时代”“青年论坛”“青年文艺”“青年美术”“地方印象记”“学习指导”“阅读指导”“世界情报”(后改名为“内外情报”)、“时事瞭望台”“每月讲台”“每月人物”等专栏,以及“科学特辑”“世界现势特辑”“中国现世特辑”“升学与就业特辑”“读者特辑”“文艺特辑”“研究和体验特辑”“非常时期教育特辑”“青年与文艺特辑”“华北与国防特辑”“大学生写生特辑”,等等,仅从这些专栏和特辑的名称,就可以看出《中学生》确实是青年的“知己”,处处给青年以“忠实的安慰和督促”。青年读者从中“学会了呼吸正义,诅咒黑暗”(陈原语),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社会名家对《中学生》也格外青睐。黄炎培在给青年的题辞中说:“现时青年对于读物的要求,一、实质上可以济知识饥荒,二、富于趣味。欲得实质与趣味兼美,莫如——《中学生》月刊、《新少年》半月刊,敬为绍介”(刊《中学生文艺季刊》第3卷1号,1937年3月11日出版)。
与《中学生》的“专栏”和“特辑”相呼应,作为“开明书店的奠基者”( 徐盈《从我应试作文说起》,见《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和“开明书店的灵魂”(萧乾《向叶老致敏》,见《我与开明》),叶圣陶和开明书店同人一起,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旨在使青年人认清“世界的大势”“中国边疆的现势”,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读物,仅就《中学生》杂志介绍过的专著就有《中国近世史》(魏野畴著)、《五卅痛史》(陈叔谅编)、《济南惨案史》(李宗武编)、《上海中日战区图》(陈铎校注,葛烺编制)、《满州事变与各国对华政策》(日本田中丸一作,默之译)、《沪战纪实》(韦息予、工臻郊著)、《最近中日外交史略》(李季谷著)、《最近的日本》(李宗武编)、《帝国主义与文化》(伍尔夫著、宋桂煌译)等。叶圣陶说出版这些书籍的目的,就是要“使那些‘健忘的人也知道‘有外来的侵略”(《中学生》1933年9月号《编辑后记》),使那些“有血气”的青年,“循诵此篇,跃然奋起”(《〈沪战纪实〉广告辞》,见《中学生》1933年4月号)。叶圣陶真不愧是“无名的泥土”。
四、呼唤“赤热的真诚和明澈的理智”
1936年1月28日上海《大美晚报一·二八纪念专刊》,在论及国难日深的事实时说:
“九一八”以来有四年多时间,虽不怎么久,但所遭遇的国耻已经打破中外古今历史的一切记录。有人估计这短短期间,我国共丧失只以土地而论已有八百余万方里,比百年来满清共失的土地还超过一百万方里,等于日、英、法、意、德、奥、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国本国面积之和;换言之,也可以说是等干四个法国,五个德国,六个日本,十个英国,六十个瑞士,七十个荷兰,八十个比利时。这多够骇人听闻,照四年以来这样的速度断送下去,再不了十年,全个中国便会送得干干净净。
这一年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崭新的一页。清华大学救国会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在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平静的书桌了……”(竹衍《一二·九运动记》,刊《中学生》1936年2月号)请愿学生一吐心声,全国民众警觉同气,山山海海相呼应。“我们要把救国的责任担在肩上”“我们要用热血浇灭敌人的凶芒”,这震天撼地的怒吼响彻中华大地。
为一二·九运动所鼓舞,叶圣陶当即在《中学生》上发表《度过了非常时的一年》(《中学生》1936年12月号“卷头言”),文章说:一二·九运动开端的“抗敌救亡运动,也像一个激怒的洪流,泛滥到了全国。学生民众的英勇抗争,演成了五四、五卅以来一首空前悲壮的史诗”。他在《纪念第二十五度的双十节》(《中学生》1936年10月号“卷头言”)中,郑重地宣告:“新的希望”并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用以安慰自己的幻想,而是确确凿凿的事实。”在《“九一八”五周年》(《中学生》1936年9月号“卷头言”)中,又不无欣喜地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下去,像暴风雨一般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斗争无疑就会到来。”
叶圣陶坚定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阵线上,尤其是在1936年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的一年半里,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杂文,抨击当时国民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批评我们民族的弱点,寄厚望于正像“日头出山”“笋子报芽”的青年。《“笼统病”》(《中学生》1937年2月号“卷头言”)批评“中国人”浑浑噩噩、糊里糊涂的心态。他说“中国人一向都中了‘笼统毒,对于一切事物和现象,只是笼统地看,笼统地想,从来不肯从合理的分析中求得明确的判断……老是在玄学里兜圈子”,结果造成思想上的惰性,对外来的学说和主义,“不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便是不假思索地拒绝,很少有人肯加以正确的分析和合理的判断”,进而指出“像这样不想把这近乎遗传的‘笼统病医治一下,那是永远不会有正确的认识和自觉的信心的”。他谆谆劝勉青年“不忧不惧,把握住心情,认真地生活”,“对于纷然四起的说教”不要盲从,一定要把“斟酌取舍之权”操在自己手里。
《关于青年的修养》(《中学生》1937年1月号“卷头言”)着重批判“偶像”。文章说“有人在鼓吹无条件地信仰偶像”,其目的就在于“养成青年盲目的、被动的服从性”,“造成一些供驱策的奴才”,竭忱地希望青年“能运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力量来克服不合理的欲望”,“着眼于国家”,保持“以社会为本位”的节操。叶圣陶在这里所说的“有人”,指的显然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其御用文人。
《论非常时期的领袖》(《中学生》1937年2月号“卷头言”),批判了国民政府鼓吹的“一个领袖”的谬论。文章在阐述了领袖的意义、领袖权力的来源后说:
中国现在非常时期中……举国一致的愿望便是抗敌救国。谁能领导民众,诚意抗敌,他便可以获得民众的信仰,做民族领袖……领袖的产生决不在他的本身而在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换一句话说,就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以领袖要想对时代有所贡献,唯一条件是认识他所担负着的历史使命,把握住当时群众的迫切需要,然后运用群众的力量,努力去求实现。如果只想利用机会,牺牲群众的福利来造成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地位,那必然要为群众所遗弃。毁灭一个领袖比造成一个领袖要容易得多,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例证是举不胜举的。
这些深刻的论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独裁政治”和“暴力压迫”,是对当年的统治者鼓吹的“一个领袖”谬论的有力抨击!1937年3月号《中学生》上有叶圣陶写的“卷头言”《到统一之路》,谈他对“统一战线”的看法。他说“统一”的道路应该是一条堂皇的路,“在一端,是以和洽的民主化的方式,使整个民族统一团结起来,没有内战,而只有内部的建设,除了破坏我们民族利益的卖国汉奸之外,在我们民族内部,不能以一些政见上的差别而自相摧残压迫,这样开诚布公的合作,便是一条宽广的民族统一大道的起点。在另一端,则是以不妥协的战斗的精神,对付外来的侵略我们的敌人,这种战斗可以使统一的合作加强,而惟有对于侵略的敌人坚决不妥协的战斗,才可以把民族发展的道路开辟得益加宽广起来,使我们从民族统一的起点达到民族解放的终点” 。为此,他一方面希望青年以万分的热诚,去响应这种“统一战线”“统一救国”的呼号;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家警觉,督促这个伟大的“统一”运动,使它达到原来的神圣的目的,提醒人们不要被“统一”的口号所蒙蔽: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人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之国”,许多字眼尽管如何说法,干下来的结果却又另是一个样子;假使我们只是盲目地守着这个“统一”的字眼,而不看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去,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还是值得顾虑的。
在二十几年来的民国历史中,“统一”两个字不是没有人喊过的。袁世凯谈过“统一”,为的是要把中国统一起来,做他皇帝宝座的垫脚板;吴佩孚也谈过“统一”,他要用武力的统一来扩大他封建势力的统治。但这些统一运动结果都由荒唐的幻梦变成破碎的噩梦,为了他们把统一当做个人的事体,为的他们不走民族革命的堂皇的大道,而走自私野心的邪僻的路子。当这些野心家利用统一的幌子,走了一段路程,要想“过路拆桥”时,他们立刻成为民众唾弃的独夫,断送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了。
仅从这几篇杂文我们就不难看到叶圣陶当时的心情。无论是抨击国民政府鼓吹的“偶像”“领袖”“统一论”,还是批评我们民族“软弱”“文明”“镇定”等“病害”,都是为了激励青年人“睁开眼睛”,认识“现今的世界”,振发力行、耐劳、坚忍、奋斗的精神。他说只要青年们不悲观,能以“赤热的真诚和明澈的理智”与“各色各样的人”携手,“锲而不舍”地“爱国”和“救国”(《“爱国”和“救国”》,《中学生》1936年4月号“卷头言”),就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他在《春假》(《中学生》1936年4月号“卷头言”)一文中希望青年学子利用“春假”,回到乡村去看看农村“破产”的现实,向民众宣传救亡的意义。结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到乡村去,还有一点应当看看的。今年开头两个多月,天气特别寒冷,有几处地方,据老辈说,四十多年来没有这样严寒了。草木的芽迟迟不见萌发,耕种为主的农民叹着气,玩赏花木的“雅人”也叹着气,大家说,“春天不会来了!”但是,现在时交四月,草木的芽到底萌发了出来,绿色又遍满郊野了。这些从酷烈的寒冷中挣扎出来、解放出来的“新绿”特别值得看看,因为这可以鼓舞我们的热望,坚强我们的信念。
叶圣陶写的是“春假”,抒发的却是“忧患还须惜好春”的情怀,激脚青年们与“酷烈的寒冷”搏斗,坚定“酷烈的寒冷”过后就是生气蓬勃的“好春”“春天一定会到来”的信念。
叶圣陶编《中学生》一直编到1949年9月。1949年9月《中学生》与在北平出版的《进步青年》合并,名称改为《进步青年》。从1931年1月到1949年9月,叶圣陶编《中学生》编了将近16年半(1937年8月至1939年4月因“抗战”停刊),真的是历尽艰辛,劳苦功高,希望能有机会和读者朋友一起叙说。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朱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