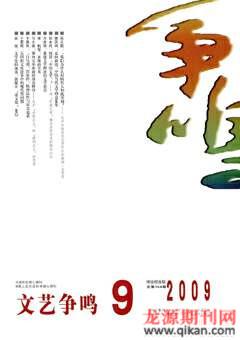废名小说中的儿童世界
石明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朱光潜在论及废名的诗时,就曾说过:“废名先生富敏感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风味。他的诗有一种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1)细读废名的作品,感到其中的确有着浓烈的道家精神气息,尤其是最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的中后期作品——田园诗化小说,充满静柔之美、素朴之美、梦幻之美,体现了老庄哲学淡泊避世,无为不争的方面。在当时复杂的现实面前,废名因为无奈、失望、缺乏把握,而将能量转向了内心世界,道家思想使他获得了精神的提升与救赎。
儿童时期或更早的婴儿时期是人生的最初阶段,人的思想在此时是一种天然状态,他只是按照他的本性活动,完全没有形成社会要求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因此,卢梭说:“跳出童年时代吧,朋友,觉醒啊!”他的这句名言很能代表西方文明的生命价值观,他把个体告别童年看作是“觉醒”,看作是成人的标志。
但是告别童年的成人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呢?成人虽然比儿童更强大,更有智慧与理性,同时也有更多的欲望、挣扎与苦恼,成人世界中的功利、欺诈甚至杀戮是儿童世界没有的,儿童世界是真实、柔和的。一个个体从儿童走向成人,正如社会必然进化发展一样,是自然规律使然。但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乐观的趋势,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都有发展的负面结果,这一切于人们理想中的人生相差甚远。
“朴”“婴儿”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朴”一般可以解释为素朴、纯真、本初、纯正等意,是老子关于社会理想及个人素质最一般的表述。“婴儿”其实是“朴”这个概念的形象解说,只有婴儿才不会被世俗的功利宠辱所困扰,无私无欲、淳朴无邪。老子明确反对用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规范约束人、塑造人,反对用这些说教扭曲人的天性。而应当让人们返回自然的素朴状态,即返朴归真。
道家在肯定儿童的单纯、美好的同时,更进一步把婴儿或童年时代看作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是人生最完美的境界,即儿童就是最完美的人。因此,道家主张返归自然,遗弃人的社会本质,是生命如一个孩童。
在《老子》中,他经常讲“婴儿”。“婴儿”已经发展为一种人生哲学概念。婴儿是充满生机的,是圆满的象征。既是人的初始状态,也是人全面发展的象征。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好这一尺度,只要偏离这一形态,就是生命的夭折。
庄子继承与发展了老子的婴儿哲学,《庄子齐物论.》曰:“天下莫大于秋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殇子”即夭折的婴儿,因为永远地保留了婴儿的状态而得到了圆满的人生,所以称之为“寿”;彭祖虽然肉身长寿,却早早就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婴儿时期的圆满,所以称之为“夭”。在《大宗师》中,所谓得道之后的真人,其特征之一就是“色如孺子”。
废名小说中的儿童与成人两个世界
“儿童”在废名的小说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几乎每篇小说都是由成人与儿童两个世界构成的,这如同沈从文的文学中存在城市与乡村两个世界一样。处处流露出废名对儿童世界的向往,对成人世界的无奈。
《柚子》回忆了我与表妹柚子在十岁以前的童年生活,那时的柚子快乐、天真、健康、无忧无虑,两个人一起游戏,爬山、折杜鹃、剪棕榈叶子……童年的柚子对家事一无所知,其实此时柚子的家已是家道中落,连房子都典给了别人,所以和姨妈一起住在外祖母家,只是因为年幼无知,没有寄人篱下之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外祖母去世,柚子才意识到家境窘迫的人生苦痛,她得替人缝补衣服,赡养母亲。这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与成年闰土的差别。儿童对现实充满着无知的隔膜,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是诗性的。柚子感知到生活的苦痛与艰难,并不是世界变了,而是她离开了童年。
废名不止一次在小说中表达对童年的留恋,“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看见门口树上的鸦鹊,便也想做个鸦鹊,要飞就飞,能够飞几高就飞几高……没有人能迫着我做别人吩咐的工作;除掉飞来飞去,飞得疲倦了,或是高兴起来了,要站在树枝上歌唱,没有谁能够迫着我叠下翅膀等候别人。”(《少年阮仁的失踪》)
这样的自由与快意,恐怕只有在四五岁的童年才能拥有,而与此相对的则是沉重冷漠的成人世界。即使梦想中令人向往的大学生活也同样令人失望。“在那里仍然只有痴呆的笑,仍然只有看着令人发抖的脸。我所喜欢的渴望的,一点也不给我,给我的仍然只是些没有人味的怪物。”阮仁看到的“痴呆的笑”“令人发抖的脸”“莫不相关的神气”,都是“没有人味的怪物”——成人的特征。
废名是寂寞的,他的文学也是寂寞的。他也害怕寂寞,“我想,倘若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也好,同我一样,心被火烧着,我将拥抱他,也不讲话,也不流泪,只把我俩的心紧紧贴着……”他的孤独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总是流连于童年的世界,不愿成人化。在他看来,成人意味着放弃自由、戴上面具,而这一切是一个成年人生存下去必须具备的能力。废名同阮仁一样梦想着永远停留在童年美好的时光。
但走向成人是必然,最终是事实,退回去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过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接受生理的成年的同时,把精神的异化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在精神世界留有童年时期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协调与澄明的美好状态。
废名的这一观念符合道家讲的“成也毁也”。他一直在思考的,一直在努力的是如何阻止这种内在的分裂。他找到的方法就是还原儿童视角。在他看来,小孩总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每当看到小孩,他总像久热后下了一阵大雨,不知不觉清爽了好些。甚至从不关心世俗得失的街头流浪的乞丐、过着与世人隔膜的生活不问世事的又聋又哑的人、乡村的妇女等,因为相对于别人更少世俗的纷争,也被他认为是以儿童的方式生活着的人。因此,这些人成为废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儿童形象几乎存在于废名所有的小说中。《浣衣母》中的驼子姑娘、城里的太太们送来求李妈看护的“有事跑到沙滩,赤脚的,头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许许多多的小孩、《桥》中童年的小林、琴子、细竹……共同构成了儿童的天堂,世外的桃源。
童年与成人的距离——十年
“十年”是一个时间概念,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会发现它作为一个时间意象在文本中反复的出现。
《柚子》中,“我”回忆十年前与表妹柚子共度的快乐的童年生活,十年后重逢时柚子妹妹即将出嫁,姨父入狱,姨母病弱,家境凄凉。离别时,柚子妹妹走在泥泞的路上,留给“我”的是并不回顾的身影;《少年阮仁的失踪》中,废名写道:“我将在大学里的一员时,我的十年来忘掉的稚梦,统行回复起来了。我的十年来被恶浊的空气裹得几乎要闷死的心,重新跳跃起来了。”由于废名小说大多具有自传的性质,并且这篇《少年阮仁的失踪》又是以书信体来完成,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我们可以推断他的自叙传性质。尽管作家“……不一定都像郁达夫那样,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但其创作或多或少带有作家个人的影子。”(2)《少年阮仁的失踪》创作于1923年,作者23岁,正在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读书,与阮仁的情况相符,他所留念的“十年前”,是十二、三岁的年龄,这正是废名理解的童年与成人的界限。
《半年》中,“我”辞退了差事,决计住在家里,一次雨后,见到了“十年没有吃过然而想过的地母菇”。“十年来,每当雷雨天气,我是怎样的想呵”。“我”回忆小时在城外捡地母菇的情景,留恋的当然并不只是地母菇的美味,实际上是童年的无忧无虑。而十年来,过着成年人生活的“我”是黄瘦的、病态的。“我”最怕与世人应酬,每当此时,犹如被晒在刺目的太阳底下,总是急得想找个窟眼躲藏。半年的居家生活,使“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使日后回到北京的“我”时常羡念。
《半年》中还提到一个“我”在半年中结识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小朋友。他不愿读书、不听话、贪玩、不懂生活的悲伤。“我”喜欢小朋友的率真、懵懂,不谙世事,又替他不能理解母亲的辛苦担心。当小朋友终于要为母亲买盐而放弃玩耍的天性时,我又是欣慰而悲哀的。在这个时常令“我”挂念的小朋友身上,体现了废名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矛盾心态,对儿童过渡到成人的无限留念与无可奈何。
《初恋》中,回忆“我”美好的童年时代,那里有令“我”暗恋的美好的银姐;天真快乐的时光、伴随“我”童年的慈爱的祖母。而当“我”结婚后第一次还乡时,祖母已经去世,银姐已是一个嫂嫂模样的姐儿。这之间“已是十年的间隔了”。《鹧鸪》中,“我在都会地方住了近十年,每到乡间种田的季节,便想念起鹧鸪”,“十年”的都会生活是成人化的生活,念起鹧鸪也就念起在乡间度过的童年,如今“我”以成年人的身份回到故乡,物是人非,昔日的女孩子都成了插花敷粉的大人,柚子也不例外,使他感到一片空虚。
《去乡》中,“我”也用“十年”指代自己告别童年之后,在成人世界度过的时间,“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天天计算我的行止的,只有我的母亲,最近十年中,我捱她住过七天——”“十年当中,首先进入死亡之国的,是这位姐姐。”《竹林的故事》从开头就诉说着:“十二年前,菜园的主人是一个和气的汉子,叫老程。”当然,十二年前,三姑娘是一个害羞又爱笑的女孩子。在《桥》的上篇与下篇之间,废名写道:“在读者眼前,这同以前所写的只隔着一页的空白,这个空白代表了十年的光阴。”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中,经常出现“十年”的意象。其中透露的大多是一种不堪回首的寂寥与惆怅。如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陆游的“事态十年看烂熟”,黄庭坚的“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等,“十年”在这里是一个虚化的时间概念,表明人生的恶性损耗。“十年后”与“十年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状况与境界
静止在童年
周作人在《竹林的故事》序中说:“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了……”(3)《竹林的故事》的确是一个梦,废名也说过:“……现在还时常回顾他一下, 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梦是如何做起,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我的杰作呵!我再不能写这样的杰作。”(4)《竹林的故事》何以被称为是梦呢?小说从三姑娘快乐的童年、慈爱的父母、一家人贫穷但又知足的生活写起。他们居住在远离尘嚣的自然怀抱之中,自然意味着未经雕琢,与人类的童年相应。“山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坎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是菜园。”
在三姑娘成长的过程中,有三次向社会化、成人化发展的机会,但她都拒绝或者躲开了。
首先,爸爸的离开虽然使母女悲哀,但对死的恐惧“然而这并非是长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样的勤勉,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院子里的菜,都一天天绿的可爱。老程的死却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鹞鹰在屋头打圈子,妈妈呼喊女儿道,‘去,去看担里放的鸡娃,三姑娘才走到竹林那边,知道这里睡的是爸爸了。到后来,青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几乎也没有了。”
三姑娘仍然生活在单纯美好的童年世界里。
正二月间赛龙舟,女人们都到城里看热闹,但三姑娘无论母亲如何催促鼓励,都不愿去。这实际是三姑娘成人的第二个机会。母亲是希望女儿长大的,但在成人世界的喧闹与竹林的宁静之间,她还是留恋后者,三姑娘对母亲的依恋、关爱是她停留在童年世界的依据。
三姑娘依然保存着童年的质朴、纯真,她种菜、卖菜,并不像商人那样为了牟利,只要维持生活的需要就可以了。她的菜“隔夜都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而且她从不与别人计较多少。在小说中,三姑娘卖菜和不愿去看龙舟的事,都是发生在她十二、三岁的时候,正是向成人过渡的时期,但在小说中,三姑娘的成长停止了。
几年以后,“我”再次回到故乡,远远地看到了已经嫁到别村的三姑娘,但只是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音。既没有描绘她的模样,也没有写她说话的内容,虽然“我分明听到了”。小说的结尾写道,我虽然很想见到三姑娘,但我却面对河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了。
废名没有写成人后的三姑娘,在他的记忆中,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三姑娘就永远留在了童年了。废名就这样编制了他的一个梦,一个静止在童年的梦。废名在《说梦》中说到:“我有一个时候非常之爱黄昏,黄昏时分常是一个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欢在深巷子里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起《黄昏》为名,以希腊一位女诗人的话作卷首语——黄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找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5)废名的《黄昏》(《竹林的故事》)招回了什么呢?找回了童年的三姑娘,召唤着永远的童年。
废名另一个更加完美的梦,就是他的代表作《桥》。
《桥》与废名的其他小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叙述方式的特别。叙述者总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在作品中出现,提醒读者,他是在讲述着一个故事。而且似乎也在暗示读者,他所感受到的、他所表现的并不与小说中人物的感受相同,也就是说,小说中的人物只是他构造的境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他是在按自己的想法构建一个新的世界。
在《芭茅》一节,他这样写道:
“这一群孩子走进芭茅巷,虽然人多,心头倒有点冷然,不过没有说出口,只各人笑闹突然停止了,眼光也彼此一瞥,因为他们的说话,笑,以及跑跳的声音,仿佛有谁替他们限定者,留在巷子里尽有余音,正同头上的一道青天一样,深深地牵引人的心灵,说狭窄吗?可是今天才觉得天是青的。同时芭茅也真绿,城墙上长的苔,丛丛的不知名的紫红花,也都在那里哑着不动——我写了这么多的字,他们是一瞬间的事,立刻在那石碑底下蹲着找名字了。”
这是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界,小说的开篇,小林已经12岁了,这是在这个年龄他遇到了史家奶奶与琴子,并由史家奶奶保媒与琴子订亲。从他放学过桥去史家庄玩到黄昏回家,史家庄短短的一行,使小林与以往有了突然的不同,当他回家见到姐姐时,“仿佛是好久的一个分别。而在小林的生活上,这一刹那也的确立了一个大标杆,因为他心里的话并不直率地讲给姐姐听了。”
《桥》其实写的是成年后的小林,但他并没有使小林有丝毫的忧郁,如《桃园》中的阿毛,《半年》中的小孩一样,他仍然在继续他童年的生活:在祠堂的墙壁上涂抹那么多孩子气的字迹:“程小林之水壶不要动”“万寿宫丁丁响”……偷偷跑到万寿宫听铃、站在街角看天灯、先生出去的时候闹学、跑到家家坟吹喇叭、为了看牛吃草午饭也不吃……小林仍然是孩子气的小林。
《桥》的下篇写的是十年之后,小林已经不是“程小林之水壶”的那个小林了。他走了几千里的路回到家乡。“十年”告诉我们,小林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至于十年间他去了哪里,作者并不想提起,总之,那不是小林想要的生活——无非是成人化的世俗社会。即使下篇的人物小林、琴子、细竹都已经是成人,但三人在柳林、竹林、棕榈掩映下的史家庄仍然过着童年似的生活:夜晚看“鬼火”、赏桃花;在棕榈树下梳头;清明在河岸“打杨柳”;在闺房谈天、说笑……没有生计的负累,没有丝毫成人应该面对的繁忙与劳累,小林对细竹、琴子的爱,也没有产生冲突与猜忌。《桥》是废名的一个梦,是他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如果真的能够停留在童年该有多好?
“童年”在这里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人肉体与精神成长的最初阶段,同时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意味着个体生命与人类社会未经雕琢的、最初的和谐与美满,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在乡村与城市、艺术与现实、自然与人工的对立中,“儿童”无疑是前三者的同义词。在对儿童世界的向往与留连中,废名在寻找、追求、建构他理想的社会、人生,在搭建走向圆满境界的桥。
注释:
(1)朱光潜: 《〈文学杂记〉编后记》《文学杂志》1937年6月第一卷第二期。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3)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周作人早期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32页。
(4)(5)止庵编《废名文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2页,第54页。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