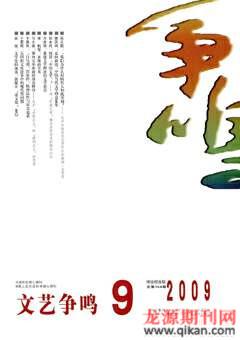二人转变异现象的文化阐释
王红箫 程 革
“二人转”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其动因是艺人们要在新时代下求生存。维系演艺生存的是观众,他们的选择左右着艺人的取舍。于是,二人转随时代的变迁、受众的变化而转,转来转去,其演艺形式与传统二人转相比发生了种种变异:从二人转表现手段的唱说扮舞绝,变成了说学逗浪唱;从“我”(演员)带动“你”塑造“他”的演故事,变成了不演故事,仅唱传统戏片断或演小品;从二人转演唱的九腔十八调,变成了只剩二人转的小曲小帽,流行歌曲喧宾夺主;从二人转“相”和“绝”的为塑造人物服务,到单纯展示一些娱乐性的技艺;从说口的辅助地位变成了主导地位;舞,更是丧失了传统,“三场舞”不见踪影,代之存在的是与二人转无关而与时尚相连的鲜族舞等。这种变异不是突然间完成的,也不是某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更不是文化霸权力量所致。它是在城市小剧场二人转商演中,艺人为满足观众娱乐需要渐渐完成的。
二人转变异没有产生自国有剧团,而是滋生于私营企业。有人说:民办剧团让奄奄一息的二人转重新火爆,但同时也放弃了传统二人转的精华部分。其实,“重新火爆”的演艺形式中二人转元素渐渐萎缩,以至于有的观众称其不伦不类,是变味的二人转;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二人转,而是“二人秀”。说句直爽的话,恐怕是只有“二人转”这个名称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也是因为娱乐性商业霸权看中了、垄断了“二人转”这个名词的市场、文化和历史中的含金量与号召力,并使我们今天无可奈何地在另一种意义上来阐释这当下的“二人转”。
娱乐欲望: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二人转变异
二人转变异是在今日中国市场经济语境下从大众文化中生成的现象,它是由文化的变异带来的审美的变异,甚至是由审美蜕变为娱乐。
一切都源自于“二人转”的进城。二人转原本滋生在农耕社会的乡土村镇,是中国传统曲艺、戏曲谱系中的一支,其形态和风格属于“土野的美学”领域。而它在近三十年的逐步的“进城”或“城市化”过程中,在经济和市场条件的砝码权衡下,其变异便不可避免了。
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程,民营二人转剧团纷纷成立。1995年,林越在吉林市建立了吉林地方剧院,它是东北三省第一个现代化二人转演出场所;1997年,徐凯泉在长春市成立和平大戏院,以后又相继将和平大戏院建在了徐州、大连。在和平大戏院成立后,紧接着黑龙江、辽宁以及吉林都出现了许多类似民办性质的二人转剧场。譬如 2003年马普安成立了吉林省东北风二人转艺术团,在北京中国评剧院大剧院和长春客车厂俱乐部演出二人转,两年后,马普安经营的东北风二人转大剧院在长春民康路开业。同是2003年,赵本山成立辽宁民间艺术团,其后不久,赵本山在沈阳开办“刘老根大舞台”剧场,建立“绿色二人转”的大本营。时至今日,“刘老根大舞台”已在沈阳、哈尔滨、天津、长春、吉林市、北京开办了8家连锁剧场,“天天有演出,场场都爆满”。
民营二人转剧场在城市的涌现,标志着二人转的演出重心已经由农村转向城市,观众的组成也不再仅仅是农民,而是城市夜晚休闲的各色人等,他们的喜好决定着二人转的演出,二人转观众的变化引发了二人转的变异。
一般来说,城市人,即使是东北人,也不怎么喜欢二人转老腔老调老段子。《新世纪周刊》记者张邦松在《二人转,万人转》一文中说:“很多传统二人转艺人发现,在城市舞台上大段的唱,观众并不买账。一出传统的二人转剧目如《包公赔情》、《西厢》等一场演下来至少要40分钟,很多观众根本没有耐心听完。往往是演员唱着唱着就被哄下台:‘下去,下去,来点粉的,来点逗乐的。”如果说,“粉”是二人转坚决要去除的(但却一直没有去除),乐却无罪,观众的求乐欲望是应该被允许和满足的。今日老百姓宁要不载“道”的“乐”,也不要没有“乐”的“道”。快乐仿佛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快乐是无法压抑的人类本性,追求快乐的二人转具有张扬生命的文化意味。
中国曾经拥有“高” 的文明,这种文明为成就其理想,十分苛刻地限制人的自然欲望。比起以往,中国今日的文明更加宽容。“生产快乐”的二人转艺人求乐可以,但怎么求乐,是需要艺人的智慧和创造的。我们决不能以违背人性的元素在二人转舞台上赚取笑声。譬如,被二人转术语称作“上托”的旦丑互相打,以及旦丑互相掐、互相撞、互相踩。再如,小小侏儒做艺人,他或是背起人高马大的搭档,或是向旦求爱被人贬斥,丧失人性尊严,以及儿童艺人的成人话语等等。
市场经济的“顾客是上帝”,具体到商演二人转的“观众是衣食父母”,观众掏钱看戏,就要满足观众的欲求。长春和平大戏院的总经理助理梁学田说:“老百姓不愿意看的,那你就不能演了,愿意看的,你就多研究点,他们到剧场来就是找乐子的,我们必须尽可能满足。市场需要哪些,我们就按照市场去做。”观众不喜欢老剧目、老唱腔,商演二人转就舍弃了它们,尽管“唱”是二人转最主要的形式,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是二人转的特色。笔者还清楚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人转刚刚发生变异萌芽时曾在和平大戏院看二人转演出,女丑赵晓军与搭档唱完一段正戏之后,她演唱了一段流行歌曲,深受观众欢迎。渐渐地,为观众的缘故,二人转演出往往把一部戏掐头去尾,选最精彩的一段,唱几分钟,本为主干的正戏反倒变成了点缀,而名之为二人转的演出,实际上变成了唱流行歌曲和二人转小帽,讲笑话,演小品,弄杂技,模仿秀等。这些新的时尚元素,很适合观众的口味,它们被加入到二人转演出中来,以至于这种所谓的二人转演出其实已在某些方面背离了二人转的传统。
可以说,二人转变异产生在今日宽容的时代,但二人转艺人绝不能愧对时代的宽容。在艺人心中,不能仅把二人转作为文化产业,以生存或攒钱为最终目标;还要将二人转视为文化事业,凭智慧、精神、情感、才艺来打造二人转精品。
变异与本性:谁为二人转定下了尺度
二人转变异是就二人转本性而言的,我们阐释二人转变异,就不能不追问二人转本性究竟是什么?谁为二人转定下了尺度?二人转是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发展中被东北人所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曲艺、戏曲文化形态。它原本是东北黑土地上鲜活的民间演艺,它是民间群体的创造,它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形成一套自己的东西,民间艺人和民间观众为二人转定下了尺度,二人转的本性是民间的约定俗成。
“兼性”是二人转本性之一。所谓“兼性”, 是说二人转既有此种艺术的元素,又有彼种艺术的元素,诸种元素共存在一出戏中,更具生命力。著名戏剧家吴祖光认为二人转是“一网打尽”的艺术,就指二人转这种广泛吸收的“兼性”。“兼性”的产生,归根结底源于二人转是民间演艺,民间创造好比是没有篱笆的大地,摆脱束缚,远离规则,人们无法用一种属性界定它,因为在它身上蕴含着诸种品性。往昔的乡土二人转既沾戏性,又带说唱性和秧歌性,它处在戏曲、曲艺和歌舞之间;今日的城市小剧场商演二人转,如果能做到“像歌曲不是歌曲,像舞蹈不是舞蹈,像杂技不是杂技,像小品不是小品,像戏曲不是戏曲……”,那么,它就延续了二人转的“兼性”。可惜的是,一台商演二人转就是由歌曲、笑话、舞蹈、杂技、小品构成的“综艺晚会”,“艺术”的“兼性”已不存在,发生了变异。
“二”的形态,也即先由王肯先生阐发的二人转的“双玩艺儿”,虽然在中国民间演艺中具有普遍性,但二人转“二”的形态是独特的,它是以丑角为中心的旦丑组合,这是二人转的又一本性。王肯先生认为丑是二人转之魂。二人转艺谚亦云:“三分包头的,七分唱丑的。”足见丑角在二人转中的分量。老艺人程喜发对徒弟说:“演丑角得知道我是谁。”二人转丑难演,就在这里。丑的一撮一站,一进一出,既要有点戏中人物的意思,又不失二人转一旦一丑的本色,这是很难的。“我”是丑,但又不仅仅是丑。如果只是丑,像戏曲中蒋干那样的文丑,或像戏曲中时迁那样的武丑,就失去了二人转的艺术感染力。“我”要有说口的本事,能够与观众直接交流,令观众开心。“我”要有相,身上可以不换装,脸上要有变化,傻相,虎相,呆相……大戏班唱丑的对二人转丑的表演方法很难适应。“我”是谁?“我”就是又说口、又有相、又数板、又起霸、又唱小曲、又进人物、又叙事的随机应变灵活调动观众的人。
商演二人转的丑角,继承了二人转的演艺传统,它具有唱说扮舞绝多种功夫,并能灵活掌控观众情绪,引发观众的阵阵笑声。具体表现在:第一,丑角的别样造型,譬如赵本山的扮老太太,小沈阳的男扮女,魏三的装傻子,孙小宝的小芳打扮,张晓飞的大姑娘形象等等,都会在造型上使观众感到好笑。第二,丑角的自我矮化,会使观众产生突然荣耀感,喜从中来。第三,丑角能说会唱,演谁像谁,又有绝活丑相,以及与观众互动的能力,必然会产生种种喜剧效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二人转丑角的走红,不仅仅在演技,还在艺人的气质,他必须是观众心中很得意的人。所谓“台上有台缘,台下有人缘。”中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看过二人转后说:“丑就是开心的钥匙。”东北二人转的丑角,实惠,可靠,也可乐,观众看他就像是自己熟人似的。东北老乡见他高兴,走了还想,丑是观众的知心人,蕴含着“真而率”的民间喜剧精神。
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在唱腔上显现了二人转的浓浓特色,这是我们何时也无法扔掉的本性之一。二人转唱腔承载在二人转老段子中,老段子的接受对今日观众来说有一定的障碍,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二人转唱腔,我们要新创具有二人转味道的音乐,虽然它比在大众文化的“文本海洋”里拿来流行歌曲要艰难得多,但却也有价值得多。二人转艺人张涛的《四大扯》,就运用了二人转的窑调,今日观众也爱听。二人转艺人在唱腔上若一味学唱流行歌曲,那就只能满足观众的一时喜好,它会赢得观众,会赢得市场,会给特定时空下的人们留下瞬间快乐,却不会给二人转历史增添什么,像二十世纪50年代沈阳小剧场二人转就唱苏联流行歌曲,当时人们喜欢,过后无所积淀。
以上我们从二人转的形态、表演、手段、唱腔方面强调了二人转的本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要传承二人转的本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我们更要在坚持二人转本性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建构。
正负两面:二人转变异的文化经验
清代中叶产生的二人转,距今300多年,它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到底是怎样一种存在?不管怎么说,面对今日观众无法接受逝去文化的演艺形式时,二人转艺人有所退却,也有所进展,他们求生存,谋活路,他们的脚步带给我们正负两方面的文化经验。
当下的变异了的“二人转”重新拾回了二人转的民间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选择,也是二人转变异的正面经验。与计划经济背景中的 “文人化”二人转相比, 在这一点上它是回归二人转传统的。“文人化”二人转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对民间二人转的改造,往往是用二人转资源实现个人的艺术理想,在将二人转艺术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二人转民间之魂。而当下变异了的“二人转”虽然重新拾回了民间精神,但却没有从民间立场出发,创造出堪称艺术的作品。如果说“文人化”二人转需要从文人的眼光转变为民间的视角,那么,当下变异了的“二人转” 其实也非常需要学习建国以来二人转文人化、舞台艺术化的成功经验,非常需要一个创作班底,包含导演、编剧、编曲、编舞、服装、舞美等多方人才,这些人才无论是艺人出身,还是文人出身,一旦进入创作状态,都要保持民间立场,他们不是将二人转之俗提升到雅,而是将俗做到极致,使其蕴含着乐人、醉人、迷人的力量。
可以说,人们看二人转,并非看高雅,而是看民间——民间的欲望,民间的生存,民间的男女、民间的形象,民间的情绪,民间的喜乐,民间的智慧,民间的想象,民间的夸张,民间的话语,民间的游戏……二人转的一切都是民间的路数,活力就在民间。
民间的视角,关涉到二人转的成败。
在创作方面,民间视角和文人视角是不同的,文人的表现方式与民间的表现方式亦不一样。王肯先生以其多年的二人转创作经验,深切地认为:
文人感觉多余的,民间感觉不多余;
文人感觉揪心的,民间感觉不揪心;
文人感觉真实的,民间感觉不真实;
文人感觉合理的,民间感觉不合理。
譬如民间二人转《燕青卖线》,是一出小唱,艺人常常把它当作开场码,多半让所谓葱花即徒弟唱。但观众始终爱听这个小段,它是二人转300多个剧目中常下单的剧目。
若从文人视角看这出二人转,它的人物刻划的确很差。但若从民间视角看,这出二人转最打动人的是好多篇和景。燕青在没进神州城以前,就有夸山景、夸城景,进城以后也还有不少曾被认为是多余的篇,像燕青眼里的“穷饭市”、“热闹市”等等。这些在文人眼中是多余的,因为它不是写人物的,燕青眼中的“穷饭市”、“热闹市”是这样,别人眼中的“穷饭市”、“热闹市”也是这样。但民间百姓看《燕青卖线》,就喜欢听这些。有的篇景是文字的游戏,文人认为不好,观众却非常喜欢。如《燕青卖线》开头的倒十字唱词:“十里听不见人喧嚷,/九里听不见买卖声,/八里修下巡更处,/七里修下接官亭,/六里倒栽垂杨柳,/五日荷花向日红,/四里长老焚香火,/三层大殿念真经,/离城不过二里路,/一条大河紧对城。”
这些语言从文人视角看,没什么意思,但演员唱得有滋有味,观众听得兴致盎然。燕青进城门之后的“观街景”,唱得有根有蔓:“道南开的天顺当,/道北开的福顺兴,/瓷器铺里碗摞碗,/黄酒馆里盅摞盅,/木匠铺里锛凿响,/铁匠炉里冒火星,/当铺就把龙牌挂,/烧锅挑着锡镴瓶。”还有“饭店景”,也很精彩:“这边卖着豆腐脑,/那边卖煎饼卷大葱,/这边卖着油煎饺,/那边卖包子才出笼。”今天的二人转作者在进行剧本创作时,一定不要失去二人转的民间视角。同样,在当下二人转向前发展的立体创造中,非常需要导演、编曲、编舞、服装、舞美等人员的加入,但这种加入一定切记将民间味弄得足足的。
我们时代夜夜商演的二人转,需要好节目,需要文人帮助。文人若有民间立场,一定会产生好作品。《擦皮鞋》就是如此。它起源于民间,最初是民间二人转艺人创作的一首歌,经常在舞台上演出。后来演员不满足于这么演出了,他们中间唱的时候就加了几句朗朗上口的词,恭维台下的观众,但戏词很乱。当时正在长春和平大戏院任艺术总监的著名二人转作家宫庆山,看艺人总演《擦皮鞋》,但戏词又不尽如人意,就创作并连续推出了区别于民间一本《擦皮鞋》的二本《擦皮鞋》、三本《擦皮鞋》、四本《擦皮鞋》……非常精彩,颇受欢迎,显现出文人介入二人转的价值。
找回了民间,是当下变异了的“二人转”的正面经验,而负面经验之一是它没有从民间出发,创造蕴含民间艺术理想的二人转作品。今天所谓从事“二人转”的人们,究竟为二人转做成了什么?有什么作品称得上是二人转的成功,而不是小品的成功?有多少进行商演二人转的艺人,他们从心往外不爱演现在的节目,他们也是无可奈何地为肯掏钱的观众卖艺。与此相关,便产生了负面经验之二,即是一味迎合观众。二人转历来是艺人和观众共同创造的结果,观众的喜好关涉二人转的存活,而艺人的选择同样决定二人转的命运。在二人转变异中,偏离二人转本质的建构,虽然赢得了观众,赢得了掌声,赢得了票房,却致命地失去了二人转某些本性,同样是一种死亡。令人心存希望的是,近来我们在二人转演出市场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新现象,即有些二人转艺人走出丧失个性的小品模式,表演具有二人转特色的拉场戏,用上了口,用上了九腔十八调,用上了舞蹈,有人物,有故事,有魅力,令观众津津乐道。这是在二人转本性基础上的新的建构,这也是二人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二人转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它身上汇集了诸多文化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固有观念的一次转变或提升。譬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厚资源,也就是面对渐行渐远的传统,以往我们只是一种态度,即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现在,我们依然坚守这种立场,努力创造既合乎本性又有变化的真正二人转;同时又允许另外两种选择:一种是只有继承没有创新,力求原生态,力求不变,就像日本狂言500年不变那样,永远保留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这其实是对二人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力保护。另一种是只有创新很少继承,它只随观众的求乐欲望而转,只满足观众的一时喜好,它与传统二人转相差悬殊,它已“变异”,变异成一种新的演艺形式。它不应该再被冠以二人转之名,应该另有新名,就像今日上海滑稽戏演员周立波的“海派清口”。再譬如,二人转本是民间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雅俗问题、文人立场与民间立场问题,我们一定固守二人转之俗,不失其民间之魂。一个深谙二人转发展史的人,会很清楚这是历史留下的经验。
我们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适应多元文化的二人转不可能是一种风格,一种模式,一种味道。每个二人转从业者的理想不同,追求不同,趣味不同,能力亦不同,因而,他们所创造的精神产品——二人转的价值或分量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提供给我们解惑当代“二人转”的现成答案,我们只能真诚地面对它“变异”的现象和事实,并以开放和建设性胸怀来试图说明它。
注释:
(1)此语出自王肯先生,是其一本关于二人转的理论著作的书名。
(2)张邦松《二人转,万人转》,发表在《新世纪周刊》2009年月19号。
(3)二人转“二”的形态,最初是由张未民先生提出并阐释的。见其论文《先说二,再说我和你》,《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4)王国维语,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