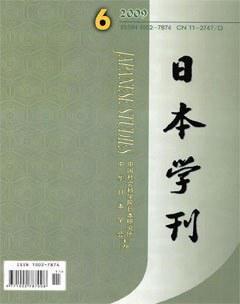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感情模式特征简论
张建立
内容提要:“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分别是日本人和中国人所推崇的快乐形式之一,它体现了日本人与中国人感情模式的一些典型的文化特征。“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有着很多共性,特别是彼此所追求的境界以及体悟该境界的程序都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但“侘茶乐境”遵从的规则是“和敬清寂”,“孔颜乐处”遵从的规则是“孝悌忠信”,彼此间又有着很大的区别。以“缘人”和“伦人”为特征的中日两国国民的基本人际状态,是造成二者所遵从规则不同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感情模式侘茶乐境孔颜乐处缘人伦人
感情模式是国民性研究的重要内容。明治维新以来,大概是因日本崇拜欧美倾向的影响,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显日本人的国民性。诸如“耻感文化论”、“纵式社会论”、“娇宠理论”、“间人理论”等等,都是这种比较研究所获得的重要成果。但是,当把日本放到对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来考察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性在东亚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便会油然生出一种“泯然众人矣”的感觉。“耻感文化论”等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莫如说是整个东亚文化的独特之处更为恰当。由此,就会愈发给人一种日本人一笔难画、且多少笔都难画得逼真的感觉。究其原因,恐怕不在于画笔乃至颜料、素材等不够专精,更重要的是因为画者的取材能力以及技法,也就是我们的研究方法欠佳所致。近些年来,尚会鹏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娘光的“心理一社会均衡”(DSH)理论的完善而创立的“缘人”、“伦人”理论,为我们分析认识日本国民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本文即借助这一理论分析工具,通过对“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异同及其成因的梳理,来分析日本人与中国人感情模式的一些文化特征。
一“侘”意的变迁
在日本,“侘茶”(wabioya)是“茶道”的本名。自18世纪后期开始,虽然“茶道”一词日益流行,但茶人们日常爱用的还是“侘茶”或“侘茶之汤”这一称呼。笔者之所以不用“茶道乐境”而拘泥于“佗茶乐境”这种提法,原因就在于不愿意丢失“佑”这个透析日本文化的重要符号。“侘”,汉语发音为“cha”,日语发音为“wabi”,它在汉语和日语中的内涵是不同的。为了便于分析“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异同及其成因,下面首先就“佬”意的变迁做一梳理。
(一)汉语中“侘”意的变迁
“侘”字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作品《九章》,而且都是与“傺”一起合用,表达失意、愁苦、哀怨之情之态。
如所周知,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家庭,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举贤任能,改革政治。但是,由于屈原性格耿直,再加上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并多次遭到流放。在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九章》中的“惜诵”篇表达的就是诗人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愤懑心情;“涉江”篇是自叙放逐江南的行迹,反映了诗人高洁的情操与黑暗混浊的现实生活的矛盾;“哀郢”篇抒写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哀思及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侘傺”一词就集中出现在这三篇中。
其中,在“惜诵”篇中出现了两次:“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忳忳”;在“涉江”篇中出现了一次:“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接舆髡首兮,桑扈赢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在“哀郢”篇中出现了一次:“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在《九章》之后的文献中,“侘傺”的用例虽然不是很多,但意思并没有什么变化。如唐代徐坚《初学记》卷二中收录的魏缪袭《喜霁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嗟四时之平分兮,何阴阳之不均?……览唐氏之洪流兮,怅佗傺以长怀。日黄昏而不寐,思达曙以独哀。”这里的“侘傺”的用例,表达的也是一种惆怅之情。
在现代汉语中,“侘傺”一词已经很少被使用了,但在清末民初时依然是作为“失意不得志”的意思来使用的。例如,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吴秋辉(1876-1927),一生中举凡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宣统末年(1911),吴秋辉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之际考获官费留日资格,但因眇一目,被以“有碍观瞻”为名取消了留日资格。其后,吴秋辉返乡从教,曾任山东齐鲁大学经学教员、复旦大学教授,并给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吴秋辉虽然天才卓越,目空千古,但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意,故自号“佗傺生”,并以“侘傺”为轩名。
总而言之,在中国,初见于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作品《九章》的“侘”字,并没有发展成为代表某种理念的概念,它大多都是与“傺”一起合用,主要用于表达政治上的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它表达的只是一种消极的感情状态而已。
(二)日语中“侘”意的变迁
日本文字的产生是古代日本人在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几百年间,尤其是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在万叶和歌的创作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经历了一个从“模仿照搬”到“调整改造”亦即“和化”的两个阶段。在日语文献中,“侘”字亦初见于《万叶集》,但它不是以“侘傺”这种复合词的形式出现,而是单独使用的。
据叶渭渠和唐月梅的研究,《万叶集》中出现了17处“佗”这个词的体言型或这个词的形容词型、动词型的用例。“佗”字“最初是用来表达包括男女、兄妹、朋友之爱情、亲情和友情,或表达烦恼、悲伤或沮丧、绝望的情绪,其中用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悲恋之情最多,达12例。可以说,《万叶集》这些歌主要反映男女为了爱情而产生的忧郁和苦恼”。平安时代后期,贵族生活逐渐由烂熟走向颓废,权势之争和恋爱失意之事日益增多,文艺上的“佗”就“不仅表现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时的烦恼,而且还发展成为反映对生命受压抑的不满和忧郁,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认命的沮丧心境”。这也就是说,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之初,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意。
但是,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汉语的“侘”被挪用到日语中后,在“和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比汉语原意的“佗”具有了更为宽泛的内涵。到了室町时代,日语里的“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表达政治上不得志以及人生际遇上的失意、愁苦、哀怨之情的消极词语,而是在原意的基础上被“和化”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理念。该理念包含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痛苦、悲哀、悲惨、伤感、寂寞、短暂、清淡、空寂等诸多的情绪,它传递给人的已经不全是一味自艾自怜的消极情绪,有时还被赋予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且,自室町时代起,如“侘茶”一词所示,抹茶文化成了“侘”这种理念的独一无二的载体,而“侘”亦成了抹茶文化理念的代名词。
关于“佗茶”之“侘”究竟为何意,教授茶道的师傅们会无时无刻地以各种形式向弟子们口传身授。然而,在学术界,虽然关于“侘
茶”的历史、茶器、点茶法等方面的研究论著早已汗牛充栋,但关于“侘”的意境所发表的专门研究论著并不多。在有限的先行研究中,对于“侘”的界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唐木顺三为代表,比较看重“侘”的汉字原意,认为在侘茶形成期,以将军足利义政的政治失意为典型代表,当时的整个日本社会上下就已经呈现出了一种“侘”的状态,“侘”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了出来。在唐木顺三看来,侘茶的“佗”只是一种贫寒落魄者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实况写照而已,其追求的也不过是一种相对贫困的情调之美。
第二种观点,以水尾比吕志、久松真一为代表,完全否定侘茶的“佗”中具有的贫困、愁苦等消极意义,格外强调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境界,认为“侘”不是一种单纯的性状描写,而是一种被赋予了积极价值的理念,是所有日本人仅凭直觉就能很好地感受得到的日本独特的美意识。“侘茶的侘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单纯的艺术性规范,它是整个生活的规范。侘成为艺术之前,首先是侘人。佬人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家。毋庸赘言,侘人根据侘的规范,对既有、现存的事、物、人、境进行取舍选择,从中发现或赋予其价值,从而形成、创造出新的事物,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独特的所谓侘艺术。”也就是说,所谓“侘”的境界就是能够于“无”中生“有”的境界,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的境界。这种观点也是教授茶道的师傅们长期以来主张和支持的观点。
第三种观点是,近年来,有的学者通过考察“侘”在茶书中的使用情况,断言日本茶道看重“侘”的精神是1930年之后的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茶道家元、禅学者及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出身的学者乃至其弟子们的倡导下,“侘”才成为茶道的精神理念。对于这种缺乏茶道修行体验、只知道做文字工夫的所谓的高论,估计佑茶修习者们是不屑一顾的。
在中国学界,当论述到日本的美学、文学等时,有些学者多少也会涉及“侘”,但是专门系统地论述“侘”这一理念的学术论文并不多,目前笔者仅见叶渭渠、唐月梅及彭修银、邹坚等人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将日语里的“侘”翻译成“空寂”来著书立说,学术观点也都近似于水尾比吕志和久松真一的观点。笔者作为一个修习日本茶道将近20年的人,也主张应该带着久松真一所解释的那种理念去修习侘茶。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所谓的“佗茶乐境”,也并非完全是充满了久松真一所向往的那种高迈之情,其中也还含有很多极其世俗性的情感。也就是说,佗茶的“侘”,绝不是一个“空寂”就能够完全概括得了的,完全忽略汉字“侘”的原意,片面强调侘茶精神的积极层面,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侘茶发展的过程中,诸如唐木顺三所指出的那种侘茶状态事实上也的确存在。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对“佗”的意境等有一个基本把握。下面,进一步地分析一下“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这对相媲美的快乐理念的异同及其成因。
二“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共性
中国不仅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深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自江户时代兴起的日本煎茶文化几乎就是中国明代以后的煎茶文化的翻版。佗茶,是自唐代就已经传人日本的抹茶文化的一种形态,若只做表象比较的话,无论是抹茶以及被日本人视为无价之宝的茶器,还是礼仪做法以及“侘”等精神理念,几乎都能从中找出中国文化的内容。其中,“佗茶乐境”与“孔颜乐处”作为中日两国所推崇的快乐形式之一,其最突出的共性就是,不仅二者追求的境界相近,而且体悟那种境界的程序亦非常相近。
首先,我们来分析“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是儒家传统的论题,它源自孔子及其弟子颜回的故事。宋明新儒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1017-1073)以“孔颜乐处”点化二程,常令其“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自宋儒提出“孔颜乐处”这一论题以来,历代诸多学者站在不同角度,从各家各派的立场出发,对“孔颜乐处”做出了诸多的解释和探索,因而“孔颜乐处”也便成为后世诸多文人学士终生追求的至美至乐的精神境界。
本来,人之常情是“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但是,颜回却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贤哉回也!”,孔子不仅赞叹颜回,而且还曾自我表白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另外,当子贡询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还告诫弟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后世儒者在探究“孔颜乐处”时,就如同禅僧参悟“公案”一般,主要是围绕上述《论语》中孔子的话展开的。在被奉为侘茶圣典的文献中,虽然措词用语不尽一致,但侘茶集大成者以及诸多重要传承者们所阐述的“侘茶乐境”,与孔子及其弟子颜回所追求的这种人生境界——“孔颜乐处”,是很相近的。
佗茶之集大成者千利休及其师傅武野绍鸥都曾对“佗茶乐境”有过很细致的解释。
武野绍鸥说:“侘这个词,古人歌中也曾多有吟咏,但近来称正直诚实、谦虚谨慎、不奢侈为侘”。
千利休在《南方录》“觉书”中阐述“佗茶乐境”时说:“小草庵里的茶之汤,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的房宅、美味的食品,那是俗世之举。屋,能遮雨避风;食,能饱腹,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之本意也。汲水、取柴、烧水、点茶,供佛,亦施人,亦自饮。立花焚香,这一切全是践行佛祖之举止也。”
虽然上述佬茶大师提出了这样的理想境界,但却未必每个修茶之人都能轻易做到。泽庵和尚在《禅茶录》中对“佗茶乐境”的论述,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侘这个字,在茶道中受到重用,成为其持戒。然而,庸俗之辈表面上装作佗之样子,但实质上绝无一点侘意。因此,在外形呈侘态的茶斋里,耗费了许多的黄金,用田园去置换珍奇瓷器,来向宾客炫耀,竟将此宣扬为侘风流,实在是不知佗本意为何之举。本来,所谓侘,乃物品不足,一切难尽顺心、蹉跎不得志之意。侘常与傺等连用,离骚注称‘佗立也,傺住也,忧思失意,住立而不能前。另外,《释氏要览》有记载称‘狮子吼普隆间云:少欲知足有何差别?佛言: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综合这些释义来看,所谓侘的意思应该是:虽然不自由,但不生思量自身不自由之念,虽有不足亦不起不足之念,不完备也不抱有不完备之念。因不自由而生思量不自由之念,因不足而愁不足,因不完备而叫嚷不完备,则非侘人,而应称作是地道的贫人。……固守侘意,即等于保守佛戒,故知侘则不生悭贪,不生毁禁,不生嗔恚,不生懈怠,不生动乱,不生愚痴。另外,以前的悭贪者也会变为乐于布施,毁禁者也会持戒,嗔恚者变得能忍辱,懈怠变精进,动乱变禅定,愚痴变智慧,此乃为六波罗蜜。波罗蜜是梵
语,翻译为到彼岸,即达到了悟道的境界之意。如此一来,侘之一字,配伍六度之行用,不就成了应该遵信奉持的茶法之戒度了吗?”
在所有佗茶文献中,《禅茶录》中关于“佗”的论述,是唯一做到史论结合地全面论述“侘”的古典文献。佗茶大师结合禅来对“佗茶乐境”进行解释,这种做法与后世儒家对“孔颜乐处”进行解释的手法也很相近。例如,阳明学派中泰州派的杰出人物罗汝芳,就曾对“孔颜乐处”做出过如下解释:
“问孔、颜乐处。罗子曰: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乐哉!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明于品汇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指引学者以人道之要。后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混融,纯一无二,故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故却忘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
在上段引文中,罗汝芳虽未明确提到“禅”字,但“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故却忘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等文字无一不充满了追求“究明自己”的禅意,也会令人自然地联想到被誉为500年一遇的日本著名禅师白隐(1685-1768)的“坐禅和赞”:“众生本来佛,恰如水与冰。离水则无冰,众生外无佛。对面不相识,却向远方求。譬如水中居,却说渴难耐。本是富家子,沦为穷乞丐。六道轮回因,只缘愚痴喑。”
可以说,素有“茶禅一味”的“侘茶乐境”与宋明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都不同程度地有着“禅”的底蕴。
另外,无论是体悟“佗茶乐境”,还是寻觅“孔颜乐处”,都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长期的修为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对这种快乐的感知、体悟也是循序渐进,要遵循一定顺序的。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自叙其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自年轻时起,就热衷于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出色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却始终对他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孔子坚韧、执著的一生中,充满了曲折坎坷。可以说,孔子在其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穷困潦倒的,50多岁时迫于形势开始周游列国进行政治游说的十几年间,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甚至险些丧命。孔子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被敬而不用,72岁时病逝。虽然孔子在仕途上屡屡失意,空有一腔定国安邦之志之才而无处施展,但其一生却是坦荡无忧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君子风范,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佗茶大师们。
《山上宗二记》是记录了利休茶全盛期的茶法、精神的重要文献,在该书“茶汤者觉悟十体”中有如下一段话:“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云云,此语乃绍鸥、道陈、宗易之秘传也。从十五岁至三十岁万事由师也。从三十岁至四十一岁,在茶汤风体上要体现出自身特色,要用心体悟作为一个茶人应有的言谈举止。但是,表现自己的特色应该只需表现出十中之五即可。从四十到五十的十年间,师东则我西也,此期间,要独立门户获取上手之名,使茶汤更富有朝气。另外,在五十至六十这十年间,则要像将水从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容器一样来完全模仿师傅,以名人之言谈举止做万事之标本也。到了七十,诸如宗易如今的茶汤之风体,名人之外者无用也。茶汤出自禅宗,故举止皆当以僧行为是也。
虽然佗茶大师传授弟子的从师修习心法与《论语》的做法不尽一致,但《山上宗二记》的记述,很明显是对孔子之言的一种发挥。也就是说,追求和践行“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者,在体悟人生境界的程序上亦是相近的。
三“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区别及成因
“佗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二者所要求遵从的规则不同。
“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的境界,如果分别只用一个字来表述的话,则可以表述为“侘”与“仁”。
侘茶讲究“平常心是道”、“日日是好日”、“步步是道场”,为了营造侘茶乐境,要求修茶者必须遵从传由千利休创立的“四规七则”。所谓“四规”,即“和敬清寂”,是指“事物人境之和敬清寂”;所谓“七则”,即“(1)茶花要如同开在原野中;(2)炭要能使水烧开;(3)夏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凉爽;(4)冬天办茶事要能使人感到温暖;(5)赴约要守时;(6)凡事要未雨绸缪;(7)关怀同席的客人”。由上述可知,佗茶“四规”是对侘茶精神理念的具体阐释,而“七则”则主要是一些实际操作性的法则。
另一方面,“孔颜乐处”,亦即如阳明学派中泰州派的杰出人物罗汝芳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乐者,只是个快活而已。“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孔颜乐处”就在于“仁”,“所乐”之“事”也就是“仁”。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仁”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虽说君子应该“无终食之间违仁”,但达到“仁”的境界又谈何容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就连其最为赞赏的弟子颜回才仅仅能做到坚持三个月不违仁。
在《论语》中,孔子在回答其弟子提问时也讲过许多实现“仁”的方法。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
但是,正如《论语》开篇的“学而”篇中所述:“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对弟子们“何谓仁”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回答,其实无非都是对“孝悌忠信”的演绎而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也就是说,只要做到“孝悌忠信”,就一定能达到仁,也就一定能够体验得到“孔颜乐处”。
如上所述,为了获得“侘茶乐境”与“孔颜乐处”,二者所要求遵
从的规则显然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正是由中日两国国民的基本人际状态不同所造成的。
所谓“基本人际状态”,这是一个最早由美国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娘光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人”是一个心理和社会的平衡体,称为“心理一社会均衡”。该平衡体由内向外分为八个同心圆,依次为:无意识、前意识、不可表意识、可表意识、亲密的社会与文化、运作的社会与文化、较大的社会与文化、外部世界。“社会心理均衡运作的基本特征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第三层中的情感关系;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会使用第四层的一小部分作为与他人互动及沟通的心理基础。以人来说,人基于情感而产生亲密关系。这层关系使得每个人的存在变得有意义,它对我们的重要性就像是食物、水和空气一般重要。它基本上给个人一种完整存在的感觉。人如果突然失去这层关系,则会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而导致生命无目标感或自杀。”这最重要的第三层“亲密的社会和文化”层和第四层“可表意识”层,再加上少许第二层“运作的社会与文化”和少许第五层“不可表意识”,便组成他称之为“human constant”的部分。日语文献中将“human constant”译作“人间常相”,台湾的出版物将其翻译成“人的常数”,笔者则赞同尚会鹏的观点,认为还是译为“基本人际状态”较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术语,实际上,它比我们现在习惯使用的“国民性”一词更为缜密。
关于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许烺光认为:“对中国人及其他类似的人来说,由于其文化规定一个人的自尊与未来都必须与他的基本群体紧密连接,因此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就成为他第三层的永久住民(permanent inhabitants)。这群人可以和他分享荣耀,也是在他失意时,必须寻求慰藉的对象。”“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可以轻易地在第三层内完成社会心理均衡要求而不需要跳到圈外层。”对于中国人这样一种基本人际状态来说,“孝悌忠信”无疑会成为群体内最高的伦理准则,因此只要做到了“孝悌忠信”,也就一定能达到仁,而“孔颜乐处”就在于“仁”,“所乐”之“事”也就是“仁”。因此,在这种基本人际状态下,“孔颜乐处”成为中国诸多仁人志士首选的快乐方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于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日本文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滨口惠俊,在许娘光的影响下,提出了著名的“间人”概念。他由“间人”概念出发,把与“间人”相关的价值观体系称为“间人主义”。滨口倡导“间人主义”,旨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他的这种努力虽然值得高度评价,但“间人主义”理论的缺陷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恰如尚会鹏所指出的那样,滨口所强调的“间人主义”以及“间人社会”诸特征,“似乎并非日本所特有,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社会似乎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尚会鹏通过对“心理一社会均衡”理论的完善,以及对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的剖析,进一步提出了“缘人”、“伦人”的概念,他建议作为“间人”的下位概念,用“缘人”指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用“伦人”指称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将更有助于明确中日两国国民性格的特征。“缘人”与“伦人”,“皆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故其感情配置都较集中于对人关系方面,都具有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而非解决内心焦虑的特点”。但是,“缘人”感情投注的范围比“伦人”要广泛,这是因为“缘人”用来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依关系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身内”、“仲间”、“他人”,这与“伦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关系圈子相类似,但与“伦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资格而是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他因素)走到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伦人”的亲人和熟人之间是不可转换的。换言之,“缘人所属的最主要集团情境并非完全依据亲属集团划分,亲属集团和非亲属集团有一定的可换性,故集团情境的范围更广泛和更不确定,因而所要参考的变量更多样和不固定。而伦人行为的集团情境在亲属集团成员与非成员之间有严格区分,亲属集团与外部世界这两种情境的区分被强化,具有不可转换性。伦人行为要参考的主要是‘角色情境,角色情境较为固定且趋于有固定的规范,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爱妇敬、兄爱弟悌、朋友之间的信等。”
处于“缘人”这种基本状态下的人,欲维持心态的愉悦和平衡,需要的更多的规则是“和敬”;处于“伦人”这种基本状态下的人,欲维持心态的愉悦和平衡,需要的更多的规则是达仁之本的“孝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的气候、地貌、风物对人心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固然不可小视,但是,社会基本人际状态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在中国,特别是在文人学士之间,大家都清楚“孔颜乐处”是如何受到推崇的;在日本,推崇“侘茶乐境”者也不在少数,佬茶修习人口分属的社会阶层非常广泛,既有皇室贵族政客大贾,更不乏地位低微的普通民众。广大的侘茶修习者们或将侘茶视为其不为无益事且度有生闲暇的娱乐手段,或将侘茶视为创造交友之缘的工具,或将侘茶视为修行得道的指月之指,每位茶人都按照适合自己的形式,追求、体味“佗茶乐境”。缘人,皆因缘而聚。缘起缘灭,缘长缘短,缘尽人散。佗茶的点茶法,其实质就是在创造、点化这个让人聚散的“缘”。人生于世,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或许都是一个相对的佗人。“侘茶”其实就是在启示侘人们,应该如何去珍惜和好好把握在那诸多不如意中唯一能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情实意。用和敬的心态去待人接物,从而修正了无牵挂清寂的自我,去体味一期一会的那份缘,去体味那瞬间的永恒。对于一个缘人,这份乐境弥足珍贵,相对而言,“孔颜乐处”所遵奉的“孝悌忠信”,对于缘人则显得有些无关紧要了。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无论在形而下的器物方面,还是在形而上的精神方面,按照以往单纯依靠文献进行分析的方法,通过与中华文化的对比,来研究包括侘茶在内的日本文化时,一般是很难找出日本文化与中华文化有什么大的本质性差别的。我们作为日本人最近的邻人,时常对其国民性格感到难以捉摸,反倒似乎不如欧美人对日本人看得那么透彻,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在于方法欠佳。以本尼迪克特等人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采纳文化模式论以及心理学知识关于日本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曾让人眼前一亮,但对于其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而凸显的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性,最终让我们这些最近的邻人看日本时,还是难免有些雾里看花般的遗憾。因此,欲真切地认识日本人,今后还有待进一步摸索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
(责任编辑:林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