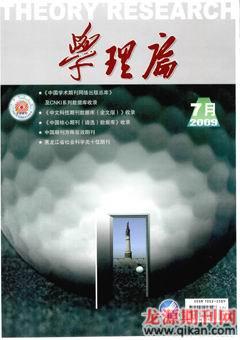清教与十七世纪西欧的科学发展
孙 波
摘要:与中世纪宗教与科学相比,十七世纪清教与科学是一种崭新的互动与制约的关系,分析十七世纪清教在西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根源;清教与科学的内在关联;并指出其哲学意义,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信仰与认识的关系。
关键词:清教;科学;清教伦理;互动与制约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7—0138—02
科学与宗教,由于其产生的同源关系,所以从产生到后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这二者之间都有着极其复杂的互动与制约的相互关系。因时代不同,二者这一互动与制约的关系也在演化发展。本文试图从宗教与科学关系的一个具体时期:文艺复兴后十七世纪清教与科学这一特定视角着手。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清教已与今天的基督教、天主教类似,而十七世纪牛顿力学的提出也被认为是近代科学的奠基。这正体现了对这一时期二者关系进行探讨的意义。
1.清教的产生及其社会影响
清教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运动,16世纪的西欧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先后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对这一运动,恩格斯曾从政治意义上这样评价:“宗教改革——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这是包括农民战争这一危急事件在内的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1]加尔文教派(即清教)最早出现于16世纪上半期的瑞士,随后在法国、荷兰、一些北欧国家以及英国等国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针对清教在英国的影响,罗伯特·金·默顿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们不要低估了当时宗教对清教徒的思想所施加的强有力的控制……总的说来,清教主义在当时是一种强大的、不容轻易反对的社会力量。”[2]“清教主义所激发并塑造出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这个时期人们活动的各个方面,清教主义是明显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相结合的宗教运动。”[3]
清教作为一种信仰既然产生于对自然现象无法理解而进行的一种先验判断,所以在某些时候宗教情结在一些人那里可能会表现为一种冥冥中强大的内心力量。理想、信念一般都不会得到现实的承诺,但这一切在当时对信仰清教的科学家们来说却鼓舞着他们运用科学向未知世界挑战。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关联,即使在十七世纪遭受教会极大迫害的伽利略那里也得到了体现,他说出了这样的话:“我跪在尊敬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面前。我抚摸着《福音书》保证,我相信并将始终相信教会所承认的和教导的都是真理……可是,地球是在运动。”[4]
可以说,清教顺应和体现了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清教的创立者加尔文本人来说即是如此。“他(加尔文)在1532年出版《论仁慈》一书,明显的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想和斯多葛派对他的影响。”加尔文并于1533年开始公开从事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清教的后继者更是无论在教义还是行动中与时代吻和,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它提倡人性,批判神性;提倡人权,鄙薄神权;歌颂世俗,蔑视天堂;崇尚理性,摒弃神启;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宗教桎梏。”[5]
上帝由外在走进人的心灵时,清教徒们心中似乎具有了一种极端可怕而又可敬的力量。清教徒这些传统宗教的“‘异端是一种精神产物,刀剑斩不断,烈火烧不尽,洪水淹不死。暴力无济于事,因为精神是强力无法进入的。‘上帝的话就是驳斥异端的唯一根据,而如果这没有奏效,世俗的强迫仍旧无济于事——纵使把这个世界淹没在血泊中。”[6]
2.清教对科学的促进与限制
宗教产生之初,其教义和思想就是建立在当时哲学、科学的基础上的。托马斯·阿奎那运用理性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丹皮尔曾这样评价托马斯·阿奎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新的综合。他把基督教教义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科学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理性知识体系。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他却巧妙的完成了。”[7]“正如罗马法的存在使得秩序的理想在整个混乱时代和中世纪得以维持不坠一样,经院哲学也维持了理性的崇高地位,断言上帝和宇宙是人的心灵所能把握的,这样,他就为科学铺平了道路,因为科学必须假定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在创立现代科学时,应该感谢经院哲学的这个假定。”[8]但在中世纪宗教与科学的共时态关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宗教对科学的促进,在中世纪后期却看到了二者关系的另一面。约翰·齐曼在其《真科学》一书中曾这样说:“‘科学与‘宗教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人们为他们的生活世界思想和行动寻求指导的一般系统。”[9]
十七世纪西欧,宗教与科学正向的互动与制约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1)清教宽容思想的产生有利于科学的发展。1553年,最先阐述血液小循环的西班牙医生米歇尔·塞尔维特被清教创始人加尔文在日内瓦处以火刑,“加尔文的行动立即使宗教改革者舆论哗然。它是应改革后的教会的要求而被烧死的第一人,在此之前,改革者们怀着某种复杂的骄傲情绪,认为只有他们自己在为真理而受迫害。”[10]这一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冲突事件最终导致了宗教宽容思想的产生。其后,卡斯特利恩在其论著《可疑的科学》中提出了知识与信仰的区别,从而奠定了反迫害论据的基础。“我们所能认识的只能是真理,他有赖于经验的感知或‘证明,既通过可以接受的前提推导出必然的结论。但我们能够信仰并非真实的东西,信仰的基石不是证据或‘证明,而是‘相信……信仰的开始就是知识的终结。因为是什么或可被确定是什么属于知识的范畴。”[11]堡垒在受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时就更容易被攻破。对于清教这种半是主动半是被迫的改变,怀德海曾说过的话可算是最为确切的解释:“宗教如果不用与科学一样的精神接受改革,它就不能恢复其固有的权威,宗教的原理或可永存;但此种原理的表现,需要不断的发展。……宗教思想可以发展为愈来愈精确的表现,摒弃未来的偶像;而宗教与科学的互相作用,就是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12]宗教宽容思想的产生无疑为科学的发展开始赢得极为宝贵的思想空间。
(2)清教伦理培养了科学家的科学兴趣与科学精神。宗教与科学的这一关联环节主要是通过对科学家思想动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在17世纪英国,正如默顿所述的那样:“有一句公式语成了清教徒们的强烈思想感情的汇聚中心,这就是:‘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所以,因社会经济、军事的需要而使科学家找准了研究的方向,同时因科学研究而能实现“颂扬上帝”这一伟大目的,从而实现信仰与认识的结合,这将更能赢得个人生存、发展的空间,赢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从而也使科学家内心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满足和荣誉。清教教义所体现出来的“入世禁欲主义”和勤奋刻苦的伦理思想与当时的时代精神相吻合,也符合了人们(包括科学家)在文明教化下所培养起来的隐忍与自律的内心需要,清教的功利主义原则更是启发人们去追求现世的幸福,乐观的面对世界,尽管这种功利有时可能带来理智上的近视。
此外,清教教义所渗透着的“神佑理性”的思想也在崇拜信仰的同时光大了理性精神,尽管清教教义对理性的运用反过来摧毁自身,但在当时这鼓动了科学家们“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内心无比激动地去追寻造物主神迹”的科学研究。关于清教伦理对科学的作用,默顿以下的这一个总结显然是经典性的:“我们所说的新教伦理既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的直接表现,又是新动力的一个独立源泉,它不仅引导人们走向特定的活动轨道,而且施加出经久的压力使人们忠贞不移地献身于这种活动,它的苦行禁欲的教规为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基础,使这种研究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13]
(3)清教的“预定论”,使得信仰得以引导认识。这在17世纪是清教与科学关系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关联环节。加尔文清教哲学的根本思想是“预定论”,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按上帝预先做好的安排而活动的。上帝不仅创造世界,而且管理世界,一切‘都在上帝掌握之中。上帝的主意并不是随遇而生,临时决定的,而是在太初就已经决定好了的。”[14]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准备了“世界是确定的”,进而产生出“世界是有规律的,可以用理性把握的”这样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假定,尽管这些假定是超验的,但科学的发展却无法离开这些假定。这样“清教主义证明的这样一个定理:带有超验内容的非逻辑概念对实践行为却也可以产生相当可观的影响。如果说对一位高深莫测的上帝的种种想象本身没有介入科学研究的话,那么关于这位上帝的一种特殊观念为基础的人类行动则的确参与了科学研究”。[15]
3.清教與科学关系的哲学思考
默顿在其著述中不止一次的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某些走马观花地浏览了此书的评论者想把下属观点强加给笔者:即,若无清教主义,就不会有近代科学在17世纪在英格兰的集中发展。如果笔者真的持有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愚昧之极了。”[16]宗教的重要性首先但不是唯一地,在于一般的影响着对科学的兴趣的程度,而不在于把科学研究引导向某些特定的方向。”[17]
纵观宗教与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人文还是科学都是人类所需的。但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却总看到它们有着冲突与对立的一面,也有着互相促进的一面。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表明:它们的趋同有时或许表明它们活力的丧失,而它们的分裂或许正在给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对错功过的评判依赖今天的判断,但接近客观的答案却总在身后给出,回顾过去人类走过许多弯路,留下更多遗憾。
参考文献:
[1][14]于风梧等.欧洲哲学史教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217、224.
[2][3][15][16][17]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1、90、119、13、260.
[4]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5:44.
[5]王德胜,李建会,董春雨.自然辨证法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5.
[6][10][11]R·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49、642、643.
[7][8][12][13]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38、638、118、649.
[9]约翰·齐曼.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374.
(责任编辑/彭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