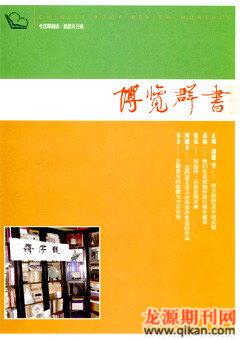穆时英的一篇佚文
赵国忠
被称为“新感觉派圣手”的作家穆时英,死于1940年6月。长时期以来,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从大节上来说吧,抗战时期,他曾先后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就这些情况而论,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名副其实,其被国民党“军统”特工刺杀遭惩罚也理所当然。然而,还有一种说法也流传甚广,1972年10月,康裔在香港《掌故》第14期上发表了《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一文,讲穆出任伪职是受国民党“中统”派遣,他非但不是汉奸,还是一名地下工作者。只是这样的说法仅为孤证。穆时英到底是汉奸还是一个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至今仍是一个谜。
由于穆时英背着“汉奸”的恶名,长期以来学界予以漠视,不屑于对其作品的研究,使之在文学史上长期沉没。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对穆时英的研究慢慢多了起来。其中既有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梳理,也有对其创作个性的分析,还有对流派特点的研究,颇不寂寞。他的作品也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版。去年初,北京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严家炎、李今两位先生编辑的三卷本《穆时英全集》。这部书在辑佚上下了一些功夫。比如它收入了1930年上海芳草书店印行的长篇小说《交流》,这是穆时英的早期作品,淹没于文坛几十年,几乎无人知晓。《中国行进》是穆时英倾全力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当年曾列入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可惜最终未能出版。编者从茫茫报海中寻觅,终于打捞上来,基本上恢复了小说的原貌。再比如穆时英还写有大量的散文、评论和译文,很值珍视,这些作品均散佚于旧时的报章杂志中。此次辑入,对了解穆时英的文学艺术见解、理论修养、创作态度,乃至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应该说,《穆时英全集》的出版,为读者了解穆时英的文学创作确实提供了一部相对完整的资料。
当然,编辑全集并不容易,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往往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如果辑佚的功夫不到家,全集之“全”就会受到影响。《穆时英全集》的编者显然清楚这一点,《编后记》中有云:“虽然我们自信这部《穆时英全集》中收入了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线索而搜求到的所有资料……肯定还会有遗漏。”
近日,我逛潘家园冷摊,偶然见到《王少陵画展目录》。这是一本32开铜版纸印刷仅20个页码的薄薄小册子,素朴的封面,毫不起眼。我之所以买下它,全赖于里面收入了孙福熙、胡藻斌、穆时英三人为画展写的序,当是稀见的文化史料。而穆氏这篇,我怀疑是佚文。回来一查,印证了我的判断,果然《穆时英全集》未收。这篇序的文字不长,现抄录如下:
少陵画展序
第一次走进少陵兄的画室,站在他的作品前,我感到了一种异样的魅惑。对于英国传统的田舍图,风景画,一向没有怎样好感的我的眼里,少陵兄的学院味很浓重的构图,线条和色彩,忽然令意外地给与了魅惑,那是连我自己也始终在暗暗地惊诧着的事。以后和少陵兄稍稍熟悉了一些,从谈话里知道了他对于艺术的理解和态度,便不禁被深深地感动着,这位年青的艺人是有着更辉煌的将来的吧!
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纪,到处充满了招摇撞骗,虚伪与无耻,轻浮与幼稚;人们的企图和目的似乎只在欺世盗名。每一年,我们可以读到很多理论,看到很多展览会,然而在这许多理论里边,在这许多展览会里边,出了一些新名字的播弄和一些连基本线条也描不正确的作品以外,还有些什么呢?在这样的时代,少陵兄却能坚持着艺术的良心,刻苦地,坚忍地做基础的工作,那是不能不使人钦佩并且感动的事。现代几个绘画方面的大师,毕加梭,克罗滋,藤田嗣治,虽然在表现上采取了最新的最自由的形式,都是在素描和构图方面有着极深的根抵的。对于那些夸放的窃取了形式主义的皮毛,自称为毕加梭的后继者,天才,其实却什么也不懂的骗子们,少陵兄的努力,将是他们觉得惭愧吧。
少陵兄的技术方面的长处是严整的构图,纯正的线条,异样和谐的色调,和沉郁的笔触,最难得的是他对于神韵的把握,这正是画家和画匠中间的界线。
现在少陵兄的作品,多偏于自然的描写,稍忽略人间社会的描写,但这缺点是很客易克服的。希望少陵兄能把这一次画展作一个终止点,同时作一个新的出发点,使自己的才能更多方面地发展。
一九三六,十一月,十目,穆时英
穆时英的这篇序,写作于香港。他是1936年4月从上海启程到港的,自述去做一次愉快的旅行。在《怀乡小品》之一《Nostalgia》一文中,他这样写道:“一个浸透了闲寂的阳光的四月的下午,我提着一只皮箱,走上‘红伯爵的甲板上去的时候,是只预备到香港去住两星期,愉快的旅行心境。爽朗的海风吹着脸,吹着领带,望着天边飘逸的云丛和辽远的水平线,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灵魂全流向将展开在眼前的,新的城市,新的山水,新的人物和新的日子了。”但据侣伦《穆时英在香港》一文回忆,穆时英离沪来港,旅行并非目的。肯于中断已在《时代日报》连载数日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而跑到港岛来,是为了追踪离开自己的太太。穆时英的妻子仇佩佩,原是上海滩有名的舞女,穆因爱好跳舞,在大学念书时,每到周六,总会去舞场消磨,在这样的场合,追求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这位舞小姐。二人结合后,1936年春不知为何闹起意见来,仇一气之下离开了他,独自跑到香港。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穆时英受到很大刺激,为缓和关系,他追至到港。因为太太“约法”,要想挽回关系,除非他剃光头表示诚意,穆时英果然照做了,最终二人和好如初。穆时英预计留港两星期,但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后,战争的阴影日渐扩大,形势使然,便耽搁下来。在港期间,他参加了一些文化界举办的活动,同不少艺术家建立了联系,与王少陵就相识于此时。
王少陵,著名画家,1909年出生于广东台山的一个农村家庭,1913年随家移居香港,由于天资聪颖,自幼便和绘画结下不解之缘。“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港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北伐时期,他到白崇禧部下的第二路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从事漫画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他返港学习西画,1932年水彩画《欲雨还休》获香港美术会画展首奖。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到上海、南京、苏州、北平旅行写生,创作了《沪江大厦》、《苏州虎丘》、《故都风景》等一批优秀作品。1934年底回港后,他组织参加了香港文艺界的许多活动,画室常常还被用作活动场所。1935年冬,王少陵用半年时间为香港思豪大酒店的礼堂绘制了一幅167平方尺的壁画《凤凰》,在当时的香港堪称创举。著名画家孙福熙为此评价说“用油画表现在彩霞与群花的背景,作华美的双凤,其色彩古朴高雅,极尽庄严伟大”。1938年8月王少陵赴美国三藩市加州美术专科学校进修,此后作品经常参加展览,成为知名度很高
的油画家、水彩画家。1981年后他曾多次回中国大陆旅行,1989年在纽约辞世。
关于穆时英与王少陵的交往,所见资料不多。李今撰写的《穆时英年谱简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六期)也未见涉及。我从朱晨光著《王少陵》(1989年5月南粤出版社、东方文化事业公司联合出版)这部图文集中却见到一点史料。如书中收入一幅1938年初在香港血厂街23号王少陵画室举行中华文艺家座谈会的照片,参加者有张光宇、张正宇、穆时英、马国亮、丁聪等人;1938年8月,香港文化界在思豪酒店为赴美前夕的王少陵举行的送别宴会上,张正宇创作了一幅漫画《八仙送别图》送给王少陵作为留念,“八仙”即指穆时英、戴望舒、张光宇等人。侣伦《向水屋笔语》(1985年7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穆时英在香港》一文中,也收了一幅穆时英夫妇与王少陵夫妇摄于九龙城宋王台畔的照片。可见两人之间交往不少。另外。香港文学研究家小思(卢玮銮)女士的《香港文踪》(1987年10月华汉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中《香港文艺界纪念鲁迅的活动记录》一文的小注,涉及到“香港文艺协会”,其中有云:“该会为旅港青年文艺界所组织,以‘联络友谊,研究文艺创作方法为宗旨,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主要成员有杜衡、穆时英(一九一二——一九四零)、杜格灵、王少陵、刘火子、李育中、李晨风等人。该会主要活动是举行文艺茶话会,并向《大光报》借用副刊,出版《集体文学》及《文艺阵线》两个双周刊。”这里也写到了二人的交往。为了获得更多史料,我请教了小思女士。她在回复我的邮件中写道:“谈及穆时英与王少陵,他们一群南来文友,在港期间,颇多交往,活动多环绕在文协所组织的活动中。”小思女士当时患病,退休后。她把所有的档案资料都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手边已无,我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了,便打消了获取更多资料的念头。
1936年12月2日至4日,在香港思豪酒店礼堂,王少陵举行了第一次个人画展。思豪酒店是一所大型酒店。地址在今天的历山大厦,当年香港文艺界经常在此举办活动。港督郝德杰亲临画展并主持开幕酒会,还当场购藏一幅《香江舟舶》的水彩画,可见给予的待遇之高了。穆时英既然为画展写序,参加开幕式更在情理之中了,只是至今未见到确切的史料记载。画展的成功举办,使王少陵在香港画坛引起了更大的瞩目。
这本《王少陵画展目录》的小册子,就是为这次展览会准备的,届时在会场派发,参观者均可获得,既能起到导读作用,又具有纪念性。这次王少陵画展,共展出一百幅作品,小册子中收了这些作品的详目并画作五幅、照片一帧和部分作品的售价。
穆时英在《少陵画展序》中,很推重其人其画,但避开了只说好话的俗套,对其得失的分析十分中肯。从小册子收入作品的详目上悬测,王少陵的创作以风景画居多,如《波光帆影》、《香江夜景》、《南国烟雨》、《故都秋色》、《黄埔滩头》等等,穆时英说他的作品偏于自然的描写,是恰切的。至于稍忽略人间社会描写的画作,小册子也收入了《劳工》、《黑童》等不多的几幅,特别是那幅《沪战后之商务印书馆》。描绘了战后遭难的商务印书馆的荒凉景物,断壁颓垣,纵横错杂,令人见之唏嘘,痛恨不置。著名画家陈树人先生后来为这幅图题了“触目惊心”四字,何香凝女士亦曾题有“国破存遗迹,光荣血永流”的诗句,极力推赏。对于艺术特色,穆时英同样进行了分析,虽只有“严整的构图,纯正的线条,异样和谐的色调,和沉郁的笔触,最难得的是他对于神韵的把握”寥寥几句,恐怕也是外行所不能道的。
穆时英的这篇佚文,在他的创作中,算不得是多么重要的作品,但穆时英很少对美术作品发表观点,他借这篇序言不仅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见解,或许还能为研究者认识一个完整的穆时英提供出新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