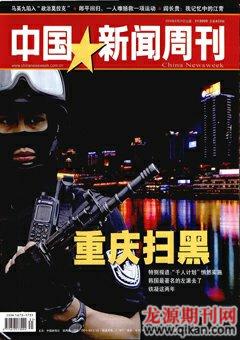随笔
好花红
陈晓守
同老大(婷婷舅)送小马老师上了地铁,然后从阜成门走回紫竹桥。之前老大教小马老师唱《好花红》。这是一首布依族民歌,曲调简单,却悠扬婉转。我们都会。一因我们生活在布依族聚居区,二是这歌在十年前被官府弄成了县歌,每天都在县城的大喇叭里哼哼,比东方红响得还早,就有点庸俗化了。
这是我在北京头一次听人唱起,虽然炸酱面馆有些嘈杂,稍一闭眼,还是能见着家乡满坡的艳山红。“隔河望见艳山红,七十二朵作一蓬,想着哪朵摘哪朵,都是那个艳山红。”
这是后人重填的词,疑似爱情歌曲。事实上在布依山寨,即兴灌词实为常见,男女对歌时信手拈来。所以从前我对别人唱,总是胡乱编些字句。
我跟老大相识早,但真正好得跟兄弟一样那是高二。语文老师喜欢提问,答不上来的同学都得站着,然后可以请另一位同学帮助回答,答不上也得站着,继续点下一位。有时一节课下来,全班有一半人站着听。
同学点同学,也是在一个自己的小圈子,生怕开罪了其他人。我同老大自然不是一个圈子,虽然同在一个球队,也分化严重。我属于老实但成绩很好那种,他成绩好但在调皮捣蛋之列。调皮捣蛋那个圈子里,他常被别人点到,他答不上来的时候,每次都会让我起来代答,火就烧到我这个圈子来了。
有一次老师提问声音低沉,也可能同学说话声音大淹没了提问。反正老大没听清楚问题,但不敢再问。同学都在低语,老师刚才问什么来着,面面相觑。老大作思考状,最后却把我点起来了。
“说实话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老师。”我说。全班大笑。
这话却让老大兴奋不已,也轻松得不行。你知道吗,他又抿了一口小二后,看着我:你当时的回答吸引了我,没人敢这样回答,你这明摆着不给老师面子嘛。
可我当时确实没听清楚他的问题。
九年后我去了广州,和老大就再见得少了,有时几乎一年谋不了一面。又九年,2007年那次回家过春节,约了一伙人吃饭,不到,说是打麻将,走不开。麻将几乎是他们业余生活的全部。
很快我就喝了一斤白酒,中间不断电话,仍是麻将声。席间我说,我得去找他们了。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说领着我去。门开了,一桌人赌博热火朝天,围观者也不少,下外彩。
借着酒劲,我掀翻了牌桌,并把几个要好的朋友轮流摔在地板上。桌上无数的人民币翻飞。
第二天飞回广州,我强迫自己忘了所有的不快。
两年后的这个夏夜,同老大走在阜外大街。说起这一幕,他哈哈自顾笑个不停。我们事后挺欣慰的,他说,你其实还有血性,还念着旧情。“好花红来好花红,好花生在茨梨蓬,好花生在茨梨树,哪朵向阳哪朵红……”他又唱起来。
歌声让我想起,那个落寞的青春期。
姓名即人生
闫晗
“快女”越往上晋级,剩下的名字越不俗:曾轶可、郁可唯、江映蓉、刘惜君……就凭人家这名字,就有感觉,有星味儿。“郁可唯,姓郁的这个姑娘,可以,晋级必定大有可为。”有人如此解析。
之前获胜的“超女”安又琪、张含韵、李宇春、周笔畅,名字也都朗朗上口,有品位又容易记。没有哪个新生代明星现在名字中还有丽、娟、玲、红这些俗字——当然,如果有个出色的姓氏来挽救另当别论。女作家池莉感谢自己的姓氏挽救了整个名字,也想让女儿跟妈姓,夫君不同意,折中取了名字叫“亦池”。原名童忠贵的苏童,改用笔名后投稿都顺利了许多。作家尚且如此,何况明星乎?
看原名见出一个人的底儿。原来这些人也不是贵族,都是草根出身,爹妈随便抓了几个字儿就叫上了。你瞅瞅,梅艳芳原名何加男,成龙原名陈港生,舒淇原名林立慧,杨钰莹原名杨岗丽……
周燕红改成“周艳泓”一下子大气了许多,让她星运顺畅,但后来又变成了“周彦宏”——那是人家百度老总李帅哥的名字哪,观众能买账吗?所以周姐姐也没了前几年国内歌坛如目中天的红火了,只在娱乐版偶尔炒炒八卦,还往往是情变受害者。
港台艺人出道兴看风水改名字,所以萧雅之改成了萧亚轩,蔡宜凌改成了蔡依林。大陆这方面远没有港台专业化,像黄晓明,大红大紫时才想给自己改名字,将“晓”改为“小”,说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邓小平把自己名字解读为“一个小小的平民”。黄晓明也想当“一个小小的明星”。
只是,若是他早把名字改了,也不至于比赵薇、陈坤晚红那么多年。这“明”字和男同学的刚、强、超、杰一样,扔个砖头过去打倒一片的。不过幸好他的姓氏多少挽救了他,不是李晓明、王晓明、张晓明,而是黄晓明——当然,成名之后,粉丝团成了“明教”,大大提升了名字的质感。
现在大家对名字普遍重视,没有家长给孩子起名叫“翠花”“桂花”这样类似“金三顺”的名字了,名字的吉凶取名时就想好了,不用打入娱乐圈之后再兜兜转转地改了。
但也有像刘欢老师这样的家长,为了显示自己的品位,语不惊人死不休——人家从佛教用语中给女儿取名“刘一丝”。你倒是有文化了,可刘一丝小朋友上学时该受多少调侃、过得多痛苦啊。
用裤裆起誓
寇研
想想这一幕一定很有意思:法庭,证人席,以及能救被告于水火或是将他丢进火坑的证人。回答问题之前,照例要先起誓一哦,不,他可不是把手放《圣经》上,而是抚着裤裆,用他身体最重要的部位起誓,其身体语言翻译过来便是,“我要是说谎,你可以把我的蛋蛋割下来。”
不知后果是否真如誓词所言,但不管怎样,这一仪式相比于后来的那个象征性动作,威慑力是蛮强的。只是它的局限性比较大,首先在女证人面前,这一招无效;另外,肯定也涉及到风化问题。于是数个世纪以来,这一习俗渐渐败落,最后,证人的手不再伸向裤裆,而是规矩地放在桌面上。
用裤裆起誓,这一行为本身表明生殖崇拜的源远流长,只不过母系社会“历史性地败北”之后,男人们一脚踢开得墨忒耳(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和丰收女神),洋洋自得地迷恋起自己的裤裆。这种得意可以从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脸上的表情看出来。这位现身子1世纪庞贝威第别墅壁画里的神,斜靠着一座石台,左胳膊支在台面,悠闲慵懒,其姿势很像吧台前的男子,一面呷着酒,一面扫视大厅,搜寻猎物。但这位神的眼神倒没乱晃,他专注地盯着右手的一杆小秤,那样的秤在现在的中药铺很是常见。但他在干什么吗?我们的神啊,他在称量自己胯下的宝貝。
这种自恋体现在服饰上就只有一个目标:裸露。直到14世纪,贵族和绅士的着装还是令政府、教会头痛的事,以至德国康斯坦茨地方市议会不得不颁布告示:“仅穿短上衣出入舞会或上街的人要格外留意,要将身体前后遮盖好,不要露出耻部。”而爱德华四世时,英国下院还对各个阶层的服装做详尽规定,目的只有一个,号召国民在衣料上不要太过节俭,至少要保证当人直立时,衣服能遮住自己光溜溜的屁股。奇怪的是,“勋爵或任何更高一
级的贵族”,不受这一规定的限制,想必裸露也是贵族特权。
14至16世纪的欧洲,骑士、贵族阶层还流行一种专为男人下半身设计的服饰,名字很有临床意味,叫做“下体盖片”。与女人的胸衣功能相当,这下体盖片,与其说是为了遮盖,倒不如说是为了突显其“伟大”。因此,量身打造是免不了的。而且,如同有的平胸女将袜子、手套等小物件塞进胸衣以求夺人眼球的效果,据说,有男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异常挺拔,甚至用水龙头做装饰。这想法比20世纪50年代带塑料管的文胸还霸道。穿这种文胸时,女人只要时不时掏出塑料管,对着文胸预留孔使劲吹几口,逐渐瘪下去的胸脯就能瞬间恢复生机。
声音“美容术”
亦桑
周六和朋友饮夜茶,我手机震,一看号码,公司的,在判断号码归属于谁的同时,无名怒火已经冉冉升起,但甫一接通,馬上拿出百分百职业素养,嘴角还残留着没抹干净的微笑,耐心解答。挂了电话后,我却又开始厉声厉气地说人家坏话:“这男人,上班时就每天若干电话来索资料,今天休假也不让人安宁,居然说是找不到昨天我给他的那两份资料。”
说完之后,我惊叹自己简直可以去做配音演员,还能一人分饰几角。电话前后的声调,像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后来和一闺密聊起,她竟有更深的功力:那些工作中越是讨厌的人,她对他们讲电话时就越客气,语气温婉有涵养,张口一个“您”闭口一个“您”,因为不愿意给对方任何可以借题发挥的余地,也因为希望保持距离。
我有个女同事,讲电话时对语调的驾驭能力,堪把东北话讲成吴侬软语。然而在挂电话的时候,则几乎是将听筒从耳朵边直接摔到座机上(除了对领导)。那震撼的一声“啪”,若是被尚未挂掉电话的对方听到,可能他在心惊肉跳的同时,得迅速检讨自己刚才是否说错了什么。
而公司一个部门经理,则被我引为经典。谦谦君子状的他,相貌上可归为好好先生,但在电话里要为自己部门争取利益的时候,总能面带微笑,用正常语速表达强势的态度,容不得别人反驳。微笑虽然看不到,但能让人感觉到,这柔软和刚硬Mix Match,令其他人的焦灼语气,显得很稚嫩、很不专业。
以上,算是“美容”。声音要出街见人之前,得先化个妆,收拾妥帖;要是事情特殊,偶尔整个容,也是得豁出去的。话说英文中“人格”一词最原始的含义,还是指戴在脸上的面具呢。不过,“美容”的事,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实也有另类。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大学毕业刚进北京的一家机关时,发现了一个“怪”现象:那些头天晚上还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的人,第二天在电话里说起公事,声音就像千里之外一块还没解冻的肉,让他又委屈又疑惑。经过几年的摸索后,他成长了。他发现这冷漠是一种保护色,冷漠的背后则是一场心理博弈。“热情有时,冷漠亦有时,这样别人才吃不透你。”
我听他这么总结时,脑子里不停地冒出一句话——“谁不曾年轻过”。如今的他,也算叱咤职场,什么风吹日晒雨淋的场合都见过。还好,他是用原生态的声音给我讲这段“委屈史”,因为朋友之前的对话,是不需要“美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