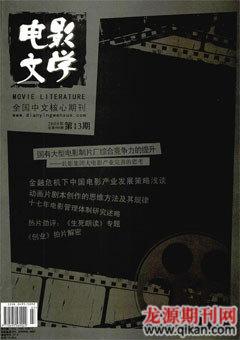《创业》拍片解密(上)
华 克
一、话启《创业》蒙难
一篇以《乱世影劫——电影(创业)蒙难纪实》为题的长篇报告,连载于1986年长影《电影文学》。在其后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作者乔迈写道:“不知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像《创业》那样大起大落,巨兴巨衰,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而叫人愁容惨淡,说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的确,在十年“文革”浩劫中,一部《创业》闯了“大祸”。自命为“旗手”的江青,高举大帽和大棒,将这部讴歌石油工人在荒原上创大业的影片打翻在地,影响所及,震惊全国。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做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对江青的“宣判”发出宣判!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一部作品的问世或示众,往往会成为政治气候变化的风向标,预示着某种涌动而来的浪潮。例如,建国之初《人民日报》发起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接踵而来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把影片《清官秘史》推向审判台……列数此类登榜之作,被毛主席点名的确实不少,但偏偏对一部电影《创业》,老人家却亲自批示,加以保护,真是惟独仅有,恩遇特殊。
作为《创业》拍片的参与者,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一部表现大庆石油会战题材的影片,为什么会成为江青一伙攻击的焦点?她挖空心思、罗织罪名,究竟是对作品本身、编导本人和制片单位发难?还是别有用心,另有所指,妄图以“写活着的真人真事”之名,抹杀会战史实,把矛头指向组织与领导石油会战的指挥员,甚至指向一直在决策上为大庆会战撑腰并日夜操劳的国务院高端人物?带着沉重的思考,我找到当年的采访笔记仔细翻看,从大量历史钩沉中,我深深感到,真实的会战史实,人在事在,无可争辩:它既不容江青之流肆意篡改,更不容以“有人借大庆红旗掠功”的恶语,含沙射影,蓄意对敬爱的周总理中伤、诬陷!浮想联翩,激动的思绪把我带回初到大庆那难忘的1971年——
二、大庆人说大庆会战
那是在林彪折戟沉沙一个月后,全国人民刚迎来建国22周年,《人民日报》以显要版面发表了社论《工业学大庆》。紧接其后,又登出一篇评论员文章:《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一天刚上班,厂党委书记岳林把我叫去,说:“现在形势已有好转,长影作为老厂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准备继续拍片。昨天经党委研究,决定派出四组人。分别下去深入生活,先抓剧本。家乙导演要去38军,总编室几个编辑下农村。你是年轻的副导演,来厂十多年,肯吃苦,有热情,所以想把你派往大庆。”见领导如此信任,我没有二话,立刻应命。可是去大庆做什么呢?岳林说:“苏云副厂长让你先去体验生活,搜集索材。一旦有创作设想,厂里再做安排。”我匆匆把不满两岁的女儿送往北京姥姥家,便拎起提包上路了。
当时的大庆。正沉浸在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逝世一周年的悲痛中。听说长影派人来,要准备拍表现大庆会战的故事片,油田职工真是喜出望外。很快,我在大庆老领导的支持下,经各方努力,组成了由各油区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四十多人参加的“三结合”创作组,大家以“回忆大会战,都把故事献”为目标,投入群众性的素材收集活动。接着,为加快创作步伐,在众多人员里,又抽出曾给王铁人当过文秘的卢泽洲、运输指挥部的“名嘴”门家利、油田机关的“笔杆”王基等三人,组成汇总素材的写作组。一直热心为捍卫大庆红旗奔走的文化局军代表兼副局长薛涛,出任写作组组长;副组长则由我代表长影来担任。此刻,刚刚恢复工作的原中共大庆党委书记宋振明和政治部主任陈烈民,一直在关注我们。林彪垮台后的反“左”形势,也使他们对这一创作敢于支持,敢于讲话,因此我们在油田深入生活,进展顺利,素材收获相当之大。
提起石油会战,大庆人从上到下,无不激动万分,含泪感叹。在深情的回顾中,不论是当年的老指挥、老工人,还是工程师、技术员以及职工家属、机关后勤,他们一讲起当年来大庆参加会战的情景,便滔滔不绝,充满怀恋。尽管像铁人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其感人事迹多有报道,家喻户晓,但涉及会战高层的背景材料。如上马前夕的种种压力,决策时刻的各类难题,还有千军万马如何摆布,艰难困苦怎样克服等等,其中有不少感人的细节、秘闻,迄今恐怕也只是少部分人知道。至于在大庆传诵的诸如“甩开勘探,三钻定乾坤”“集中兵力,挥师北上”“秀才升帐,大游地宫”“油田岗位在地下,斗争对象是油层”“七嘴八舌搞方案,快摆硬上拿油田”;又如“难忘的4·19,二李出了丑”“把井打歪,推倒重来”以及“一公分,见精神”“千里运石磨,家属闹革命”等等,这些不只是流传于大庆油田的一些经典语言,而且是有真实事件和典故为依据的石油会战史的证鉴。
江青责难《创业》“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问题”,其实,她举枪瞄准的不是别人,主要目标就是片中的前线指挥华程。那么,华程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呢?可以说,石油会战的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原型。这些原型拥有的故事含量不仅比影片内容更丰富,而且他们的性格色彩也斑驳多样,格外生动。比如,我曾经多次采访过当年同总指挥余秋里、副总指挥康世恩经常接触的部下和记者,他们说会战中的领导干部,不少人有余、康特点,作风利落,指挥大胆,有时连说话的姿势、腔调都像余、康。这并不奇怪,他们都来自解放军石油师,相同的性情是在部队里养成的。像曾在前线当过指挥的宋振明、焦力人,一直跟着余秋里、康世恩摸爬滚打,除了军人作风和他们二人相似外,也有自己沉稳机智、风趣幽默的个性。张天民在《创业》中写华程,更多则是以这两位指挥为模特,体验观察也多对这类干部感兴趣,怎么能说这是为活着的余秋里、康世恩借片表功、树碑立传呢?江青歪批华程的真正用意不是别的,而是要借此否定余、康在大庆会战中的超凡作用和历史功绩。但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还是让大庆人说说这段历史吧!
在我对一大批老会战——指挥、矿长、地质师、工程师、记者、调度以及秘书、高参——李荆和、李云、闵玉、李虞庚、李惠新、高为民、赵生振、赵桂来与董平恩等人,特别还有对此时已回任要职的宋振明、陈烈民的采访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像讲传奇故事那样告诉我:“大庆会战是怎么来的?说实话,是气出来的,逼出来的,高压泵压出来的。1960年国家石油短缺。人们只听说是苏修卡脖子,怎么卡?并不清楚,只看见汽车背煤气包在北京街上跑。当时苏联人叫号,说中国人是在小茶壶里炼油,若没有他们供给,打一场现代化战争,坚持不了五分钟!外贸会上跟苏联人谈判,人家把合同一撕,高号油说不给就不给,一下让我们灶台断顿了。1959年,全国产油才140万吨,当芝麻油还差不多。总理办公室的记事牌上,石油部年年完不成任务。石油是能源,是动力,油要上不去,
肯定拖国家工业后腿。所以部长们一有气,二心急,三是背上有压力,中心话题是怎样把石油搞上去!”
宋、陈告诉我:“1957年,毛主席听完原石油部李聚奎部长的汇报后,深感中国石油产量少,家底薄,地质储备没弄清。因此对石油提出了‘革命加拼命,请独臂将军余秋里出山当部长,责令他挂帅出征。这位老红军,中将军衔,放羊娃出身,当过任弼时的警卫员。他一上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针对中国搞石油集中在西北的偏向,提出要改变中国石油工业的布局。他认为,东北是重工业基地,钢、煤、机械都大量喝油,为什么不赶快在东北下手去找呢?恰恰在这时,大地质家李四光,打破了洋人鼓吹的‘中国陆相沉积无油论,指出东北松辽盆地的沉积带,具备藏油条件。找油有希望。于是石油部很快组成松辽石油勘探局,大面积普查。可是,1958年大跃进,头脑发热,让余秋里碰了大钉子,吃了大苦头:由于找油心切,照搬苏联经验,仅凭南充凹陷3口探井的油气显示资料,便匆忙决定搞川中会战。一道令下,队伍上马,把两三万人、五十台钻机调上去后,一打全是干窟窿,不见油,出了大丑!而偏偏《人民日报》还给他们大吹大擂,登了消息,这让头脑发涨的部长们既窝火又憋气,活像在脸上浇了一大瓢冷水。因此到了1959年,当松辽盆地传来见油的消息后。余秋里部长和紧盯松辽的康世恩副部长,欣喜却冷静,渴望而慎重,因为沉痛的教训使他们清醒了。从此,他们不仅对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盲目性深恶痛绝,而且还郑重提出,干石油一定要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要对所有资料进行科学分析,准确判断,反复论证摘明白,再也不能干‘昏头和尚瞎念经。跟着老道上天台的事了。而这,便是以后大庆会战中大学《实践论》《矛盾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倡导‘两论起家的由来。”
提起“两论起家”,宋振明打开了话匣子,他激动地对我说:“文革中我挨斗,有人非逼我承认‘两论起家是假的,胡说学‘两论是摆样子,搞形式。还胡诌党中央派飞机给大庆送毛选,是骗人,是为刘少奇、薄一波脸上贴金,涂脂抹粉。我回答,事实不是这样的。当时的会战,是总理亲自抓,具体管工交的有李富春,下面是余秋里和康世恩。周总理听说大庆人要学‘两论,买不到书,特意派飞机送来,还是我到机场接的呢。”
听到此话,我立刻想到江青一伙对《创业》中“送书”情节的诬评,他们颠倒黑白,囊里藏钉,不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宋振明接着说:“其实,石油会战一上马,大庆人对用哲学武装头脑,非常渴望。50年代在克拉玛依,苏联专家不到现场去,仅凭七八口井资料,在大楼里布井位,地下油层不清楚,让我们吃了大亏,造成了大浪费!川中会战也是地下情况没搞清,盲目下决心,碰得头破血流还得退下阵。这种错误还敢再犯吗?不能,犯不起呀!所以大庆会战一开始,为了打掉盲目性,解决对地下油层认识问题。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工人,会战工委号召大家都来学《实践论》,提倡唯物论,让会战职工真正理解到:‘油田的岗位在地下,斗争的对象是油层。并且通过学习。定出规矩:‘取全取准12项资料、72个数据。也正是这样,大家实实在在地学下来,干上去,这才为后来大庆科学拿油田打下了根基。”
陈烈民特别插了一句:“据说,1964年毛主席在会见一位外宾时风趣地讲过:余秋里不按国家计划办事,他自己讨钱,在东北一个不到600平方公里的草滩上。建成了一个年产600万吨的油田,还有一个5万吨的炼油厂。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创举……当然,这是大意,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余秋里的才干是很赞赏的,绝不是反大庆砍红旗那些人说的,余秋里是贺龙部下,反对毛主席。”
在会战史回忆中,我还听到一段康世恩捞水出油的故事,详情是:早在会战前,松辽找油的形势并不乐观。1959年,松辽局在大庆长垣(盆地沉积)铺开勘探,打了两口基准井,初见油层。但这里含油面积多大?是否为有工业价值的油流?值不值得打井开采?。一时还判断不清,难下结论。接着钻井队在孙竞涛等人带领下。又开打松基3探井。隆隆的钻机打了多天,刚钻进标准层,发现把井打歪,不符合标准。为此,坐镇哈尔滨的康世恩,和在华苏联专家米尔钦科发生激烈争论。专家按教科书式的理论认为,打基准井必须打到预定深度取岩心,打坏了要挪位重新打;而康部长坚决不赞同,他决定马上完钻、试油,不能磨蹭。专家吼叫,老康不听。他们分歧在哪儿呢?康世恩,这位当年清华大学地质专业的大庆会战副总指挥,出身军人,作风干练,如今在他眼里,苏联人那套洋框框、洋教条束缚我们太紧。老康对钻井工人说:“苏联人懂什么?他们就懂溜边转,找鸡蛋(构造),见了鸡蛋就打钻。为什么打钻?不就为找油吗?我们当前主要矛盾是找油。有油好说话,没油叫抓虾(瞎)。以往打探井,只拥抱岩心不逮油,那叫笨打,傻打,瞎打!松基3井如果能先见油,便可证明油田到手,心中有底,过后取岩心资料来得及。不然,照老米那样磨下去,时间我们耗不起!”一昕他讲的有理,井场很快停机……但是,旧矛盾过去,新矛盾又来。你不是急着要油吗?嘿,井场一试油,冒出的偏偏是水流,这下大伙傻眼了。有人出招儿:不行就捞油!但捞来捞去还是水。这时不少人懵了,心想,四川打了干窟窿,我们在这儿打个湿窟窿,大队人马在等令,探井再扑空得了吗?没办法,赶紧给康部长打电话。紧要关头,康世恩来了个绝妙回答:“大家别气馁,没油就捞水。现在,我要你们只抽水,别管油。知道不?水比油重,把水抽干净,消灭压迫,解放油层!”哟嗬,科学显神通,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方面——水,这一招还真灵。于是工人们日夜加班。开泵抽水,等水一抽干,轰地一声,松基3井喷油了!捷报传到北京,余秋里部长亲自跑来祝贺,现场庆功。因为是在国庆10周年前夕出的油,很快,响亮的“大庆”名字就在此地诞生了。——这段回顾,也正是电影《创业》所表现的华程捞水出油的那一幕情景。
1972年7月,我在大庆深入生活半年后。回厂汇报工作,偶然间在宅区碰见了于彦夫导演。我刚来长影时,第一次跟剧组拍片,便是他执导的《自有后来人》;“文革”中相互照应,是好朋友。我们久别重逢,格外亲近,于是我连忙打招呼:“您好吧,最近抓什么剧本呢?”他摇摇头:“咳,看了几个本,题材差劲。听说你去了大庆,那里怎么样?有搞头吗?”我说:“大庆到处有故事,特别是会战素材,内容太丰富了!”他高兴地说:“那好啊,来家说说看!”我走进他家客厅,就座后,他让我像讲段子那样聊起了走访中获取的趣闻——
我开始说:“讲大庆会战,必讲王铁人怎么干。他突出的事迹像人拉肩扛,端水打井,还有压井喷、跳泥浆池……这些您都知道,不说了。我要说的是他一段很出彩的经历,不过不是表扬,是挨批,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总指挥出了他的洋相,扫了他带出来的坏习气。”于导演一乐,说:“嘿,这有意思!”
我看他感兴趣,接着聊:“详情是这样——会战一上手,余、康挥师北上,萨尔图成了主战场。这里一无粮,二没房,大草原上布井网。参战井队山南海北涌上来,不管是顶风冒雪,还是人拉肩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快摆硬上,都在奋力实践指挥部的目标:在22平方公里的试验区内,既要打井采油,又要勘探资料,为油田的开发和建设定方略。王进喜带领的玉门钻井队,喊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冲锋在前,开始打得很漂亮,‘铁人的名字随之叫响。而且在不久的出油祝捷会上,探区指挥李敬、李云给他和另几位标兵牵马坠蹬。王铁人骑着大马,披红戴花,立时成了全战区的打井英雄。但是,各井队铺开打下去,都为了争功勋,抢速度,那种粗粗拉拉、马马虎虎的井场作风,和在老油田不重视资料的老毛病普遍暴露,并接连不断出事故。比如,有不少井队的技术员,现场粗心,钻进笔录记不清,下钻上千米,丢了标准层,给判明井下地质构造带来很大被动,直接影响按标准固井。又如,玉门队有个钻工捞沙样,捞了一整天,往地质所去送,忽忽悠悠只赶路,跑到地方一看,沙样不见。这下可急坏了。他回头又跑跑颠颠去寻找,打着手电扑棱到天亮,才发现丢在了草滩上,让地质师们急得够呛!再如,有一次‘王铁人忙活了几天几夜打完了一口井,忽忽拉拉大搬家,测井队紧赶着开车来测井,到处找井口,不知留在哪儿,查来查去查半天,咳,发现是井队搬家给埋上了!要不是查得及时,井白打,黄瓜菜全凉!还有,几乎所有井场,钻杆铁家伙乱摆放,井架上的工人随手扔工具,大大咧咧一失手,经常把人砸伤。……这类情况接连出现,引起余秋里、康世恩的不安。他们感到,这种一粗二松三不严,马胡凑合不在乎的作风发展下去,必定严重影响勘探质量、开发进程,不赶快扭转决不行。因此决心来一个小题大做,开展火线整风抓典型。”
我喝口茶,继续说:“那么抓典型抓谁呢?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余、康从来是抓干部,护小兵。不许对工人耍威风。一次,指挥部要开干部会,通知第二天8点进会场开讲。余秋里到点抬眼看,嘿,稀稀拉拉就几个人,他一声怒喝,把二号院(指挥部)大门关上。过了半小时,睡眼惺忪的头头们被放进来,总指挥瞪着虎眼开腔了:‘今天开会,就说一句话:明天早上8点整,都重新来报到,哪个来迟,干脆,放你们回家抱娃娃——散会!只半分钟会,吓得人们直咂嘴。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再拖泥带水了,哪怕连夜加班,天亮连滚带爬也得准时到位。……”
接着我把话提题转向康世恩:“这工夫,会战热火朝天,正上得快,打得猛,偏偏一探区出了两个大事故:,一是因操作失控钻杆掉落,砸死了钻工张其刚:二是王进喜队把井打歪,井斜超标6度半。康世恩抓准时机。立刻在4月19号这天,在探区召开上百名的干部大会。他把一探区指挥李敬和李云叫到台上,当众刮胡子(挨批),让他们亮相。老康怒不可遏地大声讲:‘你们两个李指挥,是怎么带队伍的?一丢沙样二埋井,砸死工人你不心疼。这样下去得了吗?现在请你阁下说说,你一探区资料稀里马哈丢了多少?井场没人管,总是乱糟糟,你们是哪门子领导?你们井队只想快,不想好,粗粗拉拉活儿不精。隐患这么严重,你们是看不见,还是耳朵聋?到底推广什么作风?二李当众出丑,满脸通红,一声不敢吭。”
我把话推向主角:“就在这当儿,标杆队长王铁人跑来听会,刚到门口便被人堵住,好心对他说:‘王老铁+康副总指挥正在批你们呢,别进去了!王铁人两眼一扑棱:‘啊,庆功会让我当英雄,这时候捅了漏子却叫我当狗熊,像话吗?我不能挨批就趴下!他把那人胳膊一推,挺着脖子进场了。其实,这几天铁人正在被痛苦折磨:张其刚原本是他徒弟,干活很不错,膀大腰圆吃得多,总挨饿。铁人常把窝窝头塞给他。如今眨巴眼人死了,他心里能不难受吗?现在,破船又迎来顶头风,康部长抓住事故不放正开训,他决不能回避缩脖子。老铁看见两位李指挥戳在台上,因他而受过,便毫不怵头地凑上去,跟他们一块站着。康部长一看是他,更来气,明知故问地:‘你来了,好哇,先报名,叫什么?铁人答:‘王进喜。老康劈头盖脸,不留情面,撂开嗓门叫:‘不对,你是王铁人,大名鼎鼎的铁人!铁,就是铁家伙的铁,人,就是白天黑夜打井的工人。你姓王的铁家伙掉下来,砸死了你的工人,你知道吗?心疼吗?这是为什么?王进喜紧咬嘴唇不出声,泪水直往心里淌。台下上百双眼睛直望着,康部长仍怒气不止:‘我们来拿大油田,要打优质井定方案,可你呢?你王队长井斜超标6度半,稀里马胡把井打歪,你怎么给子孙后人交代?啊?!”王铁人被批得脸面丢尽,连连请求处分。而康部长的大棒高高举起,缓缓落下,肃然对他说:‘现在你昕着,我要你回去赶快整改,不要你的检查,要你的行动,马上给我填井,把井打歪,推倒重来!……整整一上午,康部长把近来的事故数个遍,二李和铁人被刮得无地自容,羞愧难言。在场的所有干部、工人都被震撼。无不为粗拉作风带来的后果痛心疾首,也无不为王铁人面对过错的勇敢而钦佩、赞叹!——这,便是大庆盛传“难忘的4·19,二李出了丑”的故事名段。”
把铁人故事讲完,我刚要起身,于导演拦住:“真不错,哎,接着讲,再来一段!',我想了想,记起大庆创作组伙伴小卢、王基、门加利曾给我吹过一个人,“再说说刘安全吧。也是个会战名人,康世恩点过名的人。一把火烧出来的好人。1961年春,他在试验区当采油队长,干了不少出格事,一下出了风头。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我继续开聊:“石油会战,从1960年3月打响,山南海北来会战的工人们快打井,快出油,个个像在拼命。一年下来,他们太累了,太紧张了,也太苦了。偏偏遇到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恶果,整个油区严重缺粮。工人们干的都是重活、脏活、累活,大部分又是强悍小伙,一天不到一斤粮,肚子填不饱。即便是秀才院、后勤机关,五两保三餐,饿的也直叫唤。再一个突出矛盾是。干部作风简单粗暴,骂人、打人普遍,干群关系紧张,工人受不了。就在这时,刘安全出现了。刘队长原是转业兵,盖井房、装机器冲打在前,战报常为他叫好。他最大的毛病是火气大,脾气暴,手下兵动辄就被他骂哭。有个采油工,因为偷半斤粮票,挨了他一顿揍,还被撵跑。更可气的是,他管的井房装了一台检测仪,由于他作风粗拉,不善管理,一天晚上采油工烧油取暖,突然把这台进口设备烧着了!仪器罢工,采油关机,惊动了全战区!”
“康世恩半夜闻讯,叫来指挥宋振明、报社高为民,让战报记者速往调查,查找原因。也是在这时,指挥部还听到反映,有不少队干部常常批斗工人。理由是这些人一下班就逛大集,先卖掉自家的摩托车、缝纫机,然后去买土豆、买烧饼,还有来路不正的老母鸡。他们说这是歪风邪气,助长资本主义势力。一天早上,康世恩请来十几位队长谈心,刚进门便问:‘吃早饭了吗?大家摇摇头。又问:‘那你们饿不饿?回答:‘当然饿了,没粮票,省了!老
康笑了:‘别别,知道饿,就不错!来来,我给你们准备了热面条,管够!这帮人狼吞虎咽吃完,康部长一挥手:‘走,上采油队,开大会!”
我瞅于导在抿嘴笑,接着说:“这天试验区召开近千人的职工大会,康副总指挥在台上先讲了会战的太好形势,表扬了钻井、采油和油建的拼搏精神,突然话锋一转,怒容满面,把基层干部蛮干、粗暴、骂人、霸道等家长作风的种种表现数个遍。台下鸦雀无声,都在瞪大眼睛竖耳听。当老康讲到火烧了井房时,突然一声喊:‘采油一队队长刘安全来了没有?台下抱头闷坐的刘安全听见叫声,吃了一惊,赶紧站起来回应:‘我在这儿!老康摆摆手:‘来来来,请到台上来,让大家认识认识!这位刘队长一溜快步上了讲台,不知所措。康部长指着他发火:‘刘安全呐刘安全,你是一点也不安全呐!我80万美金买来的测井仪。让你一把火给我报销了,你这叫安全吗?你这个采油队长,给我带的什么队伍?骂人有你,撵人是你。整人不缺你,你干吗对工人这么大气?他们是敌人吗?不,是阶级兄弟!他们拼死拼活拿油田,你把他们当敌人整,什么作风?军阀作风,国民党作风,如果你整死人,就得挨枪毙,懂不懂啊?……老康一顿痛批,让在场的工人们痛快,解气。而刘安全吓得颤抖,据说在台上尿裤子了。康世恩收起怒容,继续讲道:‘同志们,我听说有的工人在队上挨整、挨批斗,罪状是卖了摩托车、缝纫机,去买胡萝卜、买土豆,说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又抬头。大家听听,这话能讲通吗?我们工人辛辛苦苦攒点钱,买点东西,容易吗?他舍得卖吗?他们今天卖东西为什么?就因为肚子饿。饿呀,同志们!人饿了,要吃饭,吃饱肚子,为了会战,世界上你们见过这样的工人吗?没有!这些人在哪儿呢?就在中国,在大庆,在你们眼前!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会场上到处是抹泪、抽泣和叹息!”
于导演兴奋得拍案而起:“好!太好了!”我按他坐下:“别急,还有呢!”我赶快把话引向故事结局——“刘安全挨批后,要是一般人,肯定要趴下。但他毕竟是军人,在基层干,能吃苦,从来不服软。他挨了刮,一直沉默寡言。但他心里清楚,部长还寄予希望,批评也是爱护。所以他每天必找工人谈,一一赔礼道歉。有个技术员。听赔不是近十遍,还是有成见。老刘不气馁,继续谈,直到和解才算完。他还自掏腰包,给伙房买鸡蛋,每天晚上烧热水。让工人们烫脚捂暖……眼看冬去春来,战区为改善生活。开荒种菜,组织打猎,还拣大豆,磨豆腐等等,很快形势大有好转。于是春季会战打响之前,副总指挥康世恩又在动员会上讲话了。他以振奋的口吻大讲基层如何鼓士气、渡难关,大讲各队干部如何转变作风,让井场井队鳝出了笑脸。他高高兴兴地讲着,忽而一声喊:‘刘安全队长来了没有?台下刘安全一激棱,站起来:‘康总,我在这儿呢!老康叫:‘来来,请上来!刘安全快步上台后。康世恩冲他肩膀猛拍一下,叫道:‘老刘,你干得好啊!又转脸向大家:‘同志们,这位仁兄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安全,他犯了错误,挨了批评,但是他没躺倒,没怨言,不止一次地向受过他气的工人们赔礼道歉。工人们身上有多少土,他身上就有多少泥;工人每顿吃3两,他没比人家多一钱!他理规章,定岗位,排除了不少隐患,这才叫实实在在的大安全啊。刘队长,你是好样的,我们的干部都是好样的!当初,我在台上批你,损你,发脾气,叫你出丑难堪。说明我作风也不好,老刘,现在我也向你道歉!他转脸深深一鞠躬,全场欢呼,掌声雷动,刘安全的热泪顿如泉涌……”
回顾大庆会战史实,它不仅让于彦夫,还有后来听到这些故事的张天民深受感染:为他们在电影《创业》创作中的形象构成和重场戏奠了基,而且对于我来说,每当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与气壮山河的画面重现在脑海里,也总是景仰不忘,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