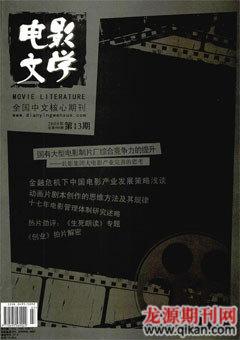论基督教文化与北村的小说创作
李雪峰
[摘要]在当代文坛,北村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基督教信念和创作追求的作家,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使北村的小说确立了“神圣超越价值”话语的地位和“苦难\救赎”的“神性书写”模式。北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人的生存困境和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开拓了多元价值文化背景下的神性一维。
[关键词]北村小说;基督教文化;神性写作;救赎
北村在当代文坛的影响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创作浪潮,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注重“语言迷宫”构建的游戏带给北村越来越多的困惑,对人类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迷惘使北村深陷痛苦之中,个人情感的变故及多种原因的纠合使北村于1992年公开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成了一个基督徒。“1992年3月10日晚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了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耶稣基督。三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见证说他是宇宙间惟一真活的神。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在这轻描淡写的叙述里面,实际上蕴涵了一个作家信仰的实质性转向。就是这个极为私人化的事件对北村及当代文坛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此北村开始了对人类生存的本质和终极意义的追问,他的写作成就了一个教徒的心声的流露,有“神圣的启示”和人的“终极关怀”,北村的朝圣之旅就此开始,虔诚地用手中的笔为主唱赞歌,相继发表了《施洗的河》《张生的婚姻》《伤逝》《消失的人类》《孔成的生活》《孙权的故事》《玛卓的爱情》《周渔的火车》《望着你》《玻璃》《愤怒》《东张的心情》等作品,它们是北村以“宗教主义”的目光审视这个堕落的世界的话语表达。
北村以小说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还一边用理性的眼光去追问文学与神性的关联。他的小说大都围绕受难、死亡、忏悔、救赎、复活的主题,意义是如此简单,以至于批评者认为在北村不断重复的苦难/救赎的叙事中,除了高扬的信仰姿态外,其内核已接近于虚无。但是信仰的基点在于“信”字,信其有、信其真并完全相信。“就是相信有一个神圣至美的绝对形象,它就是至爱本身,相信上帝无非是相信其他绝对力量。”“人类所有的苦难都是信心危机带来的苦难。没有信心的人只有使自己挺住,因为对于他来说,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没有信念的“挺住”是西西弗斯的“抗争”,是绝望的反抗,它来自抵抗,也止于抵抗,所有的行动都是僵硬而相同的。有了“信仰”,“挺住”就成了对“信念”的坚守,它通向的是无尽的力量和无穷的意义,行动就有了意义。“作家能够继续写作并不是由于他的智慧,乃在于他的能力和信心。”在“美与丑”之间,北村更倾向“真”,是神性的真理,“美如果没有神圣作依托,它是非常脆弱的,毫无超越现实的能力,它只是一种猜想。”“人活着是有意义的,没有神人活着就没有意义。”就如“基督认为如果没有他来到世间把神的奥秘告诉人们,人们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人类完满人生的问题。”“远离了上帝之爱,人便失去了神性的光辉;偏离神的方向,没有了神的尺度,人就会滑向罪恶和堕落,这就是人的罪性。”于是,人有无“信念”就成为北村小说创作的基本价值判断。有信则得永生,无信则必灭亡。在他小说里的人物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蒙神的拯救而得救,要么远离了上帝之爱而绝望死亡。
小说《施洗的河》以霍童和张板为空间背景,北村将人性恶在这里做了淋漓尽致的披露,恶本身施于人的肉体戕害,人类或许可以通过医疗、法律手段来处理和解决。可残忍的是,人们意识深处对人性恶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恐惧,这都不是任何外在的处理可以抚慰的。北村敏感地捕捉到了人群中这种危险,失去了道德规范没有意义的人生促使人疯狂、犯罪,而罪孽的深重最终又使毫无保障的灵魂不堪重负,成为变本加厉的惩罚。在主人公刘浪的生命即将耗竭在这种充斥恶的行为的时候,一个奇迹出现了。神的引导让他蒙恩,在张板和霍童之间的杜村领受了传道人告知的神的声音,“人无法自救,因为那个必死的律在你心中作王,行善不能叫人脱离罪,道德不能脱离罪,念经不能叫人脱离罪,拜佛不能叫人脱离罪。人有一个罪,叫人死;人有一个缺陷,不认识神。”于是,他开始向主发出祷告:“主啊!我相信你……从此以后。他成了一只温顺的“羔羊”,手里抱着《圣经》,时时“让阳光临到身上”,感悟到“阳光是一种里面深藏的眼睛,只有在这双眼睛注视的时候,万物才得以清晰地呈现变得可靠和真实。”
可以说,是基督的爱拯救了刘浪,使他从罪恶、仇恨、恐惧和孤独中脱离出来,进入光明和自由之中。刘浪无疑是幸运的,他不仅得到灵魂的皈依,同时也拯救了在世的肉体生命,这种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拯救才更具有宗教的现世意义,心中有了“光”的刘浪在看一切事物时都是和谐和温暖。连一根稻草也是美的,故乡霍童也成了“一切都是和谐”的世界。
如果说《施洗的河》展示的了人从沉沦到信仰,从罪恶到救赎的转变过程,那么《伤逝》《玛卓的爱情》和《发烧》《鸟》《张生的婚姻》《公民凯恩》等小说则更多地关注人没有信仰的精神黑洞和走向死亡的必然结局。
《玛卓的爱情》里的玛卓和刘仁相爱,他们相互写情书,送生日礼物和金钱,用物质形式来传达他们的爱情,信誓旦旦,又矫揉造作,“我爱玛卓”也成了刘仁的口头禅。结婚以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自己并不懂得该如何去爱,玛卓理想中的生活是荷尔德林的“诗意的栖居”,但现实却是无趣和琐碎的。最后结局只有走向死亡,他们不知道生活的问题出在哪儿,精神又陷入崩溃的边缘,死是一种必然,也是最好选择。靠人们自己无法得救,“一切都是徒劳”,只有依靠“神”才能得救。康生(《鸟》)曾经虔诚地生活在艺术的幻觉里寻找人生的意义,无奈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也只能“在地狱的边缘等死”,即使死了,他也认为自己是一把有罪的灰。人缺失了神的爱,也就缺失了神赐予人的爱人爱己的尺度和能力,而人又不堪无爱的孤独与黑暗,滑向罪恶似是必然。但人同样也不堪罪恶的沉重,因而在罪恶中沉沦最终毁灭似乎更是必然。这是北村此类小说表达的主题,即对世俗生活和审美人生的否定,对有神生活的肯定,北村说:“人的生存一旦失去引导,失去牧者。也就失去了希望。”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不是上帝想要的那个世界,人类的罪、邪恶和死亡本身就表征着世界对上帝想要的那种被造秩序的偏离幅度。”所以,那些因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有罪的人,失去了神性的人,结局只能是丧失坚守的勇气和信心,灵魂彻底失去依托,失重的人生只好堕落、毁灭。
其实那些滑向或坠入罪孽中的人在深渊里也曾经本能地发出呼救的声音,但又表现为他们因为不知道应该向谁、向哪里发出呼救。所以这类人物所呈现出的也只是道德上的愧疚感和和深深的自责,然而这愧疚感和自责在欲望化的时代和金钱的诱惑面前是如此软弱无力。《最后的艺术家》中,杜林在开始堕落时对自己的丑行有过深刻的厌恶,
然而在欲望的诱惑下。完全抛弃了内心残留的那点家庭责任感和起码的道德感,而急速地不可遏制地滑向罪恶的深渊。为了一张邮票而杀死同伴并将尸体肢解成碎块的少年(《张生的婚姻》)案发被捕后也还是没有丝毫悔过之心。直到明白自己可能会被枪决才本能地感到害怕,“我不想死……救救我。”少年罪犯发出了求救的呼声,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谁能救你。”这种深渊中的呼求在鲁迅笔下的阿Q临刑前就有了,只是阿Q在想喊“救救我”但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就被砍了头。那时的阿Q也确实不知道向谁求救,因此,救命的呼声得不到回应理所当然。而时至今天,又有那么多人在罪恶和苦难的深渊中发出呼救与恳求,也朝向了求救者以为能够具有拯救力量的具体对象,但得到的回答却同样是不知道谁能救你。这就和阿O当初未发出声的呼求的效果是一样的。至此,我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中救赎功能的缺失再一次被凸显出来。
我不知道谁能救你,其实就是谁也救不了你。因而诗人康生(《鸟》)即使已经悔罪,但在不能够得到赦免和拯救的情况下,只能在灵魂绝望和精神崩溃的挣扎中自杀。如果说康生(《鸟》)“罪”有应得,那么与罪恶、赦免都无关涉的孔丘(《消失的人类》)却也在物质生活非常优越,事业成功,家庭生活美满的情境之下,居然以不留痕迹彻底消失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死亡。比起那些与罪性相关的深渊中的呼求,孔丘没有呼救,当然也谈不上赦免。北村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似乎春风得意的人去死呢?恐怕与作者的基督教信仰有关,基督教要解救的是人的精神。人的灵魂。当人没有得到神的眷顾时,人是无法独立面对灵魂的虚无和精神匮乏的。无论人是否有罪,都无法承受生的虚无和存在本身的无意义等形而上的痛苦,即所谓人的“伟大的苦难”和恐惧——寻求拯救却注定无望。很显然,北村眼里的“罪”已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罪过,这就是孔丘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拥有能够让他很好地活在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基础,却惟独没有一个让他活下去的理由。
从北村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他对神性的体认与想象,信仰与皈依不过是显示了北村表达基督教文化的艺术方式。正是基督教文化所拥有的罪恶与救赎,爱与宽恕,苦难与超越等内涵为北村小说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与世俗的价值诉求,“从精神上扯起了一面反抗着的大旗”。基督教信仰给了北村力量,于是,他把这个救赎的秘密——“爱”宣示给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