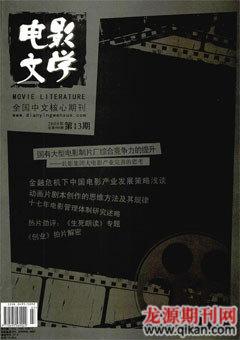艺术人生的还原 心灵史诗的呈现
陈旭光
[摘要]《梅兰芳》代表了陈凯歌电影追求的新风貌,成为陈凯歌电影从前期电影浓厚沉郁的超越性哲理追求到回归现实、人生的“世俗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影片具有浓郁的文化感同时又极为重视讲故事,展示了一代京剧大师的艺术人生和个体化的心灵史,也饱含了导演陈凯歌自己坚忍执著、欲说还休的人文诉求和艺术情怀。
[关键词]艺术人生;心灵史诗;陈凯歌;文化感;艺术精神
《霸王别姬》的成功尚未成为“忘却的记忆”,我们无疑会对《梅兰芳》抱有强烈的期待。
《梅兰芳》正是在我们强烈的期待中,以优雅的风格、传奇。富于文化感的情节,充满人生感的戏剧张力——款款进入我们的期待视野。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电影的艺术轨迹和文化版图上,陈凯歌无疑常常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具有一种较为浓厚的精英知识分子气质,堪称“少年凯歌”,勃勃英姿。这与“五四”以来的一种“少年中国”的精神和“五四”新文化气象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承传性的。他一直自认为是“文化工作者”而非单纯意义上的电影导演,他说,“与其说我是一个电影导演,我宁愿说自己是—个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叙说(用弘扬、宣扬这类词对我来讲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谈对中国文化现状的忧虑,是徒唤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面积的呼应。但用电影表达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却是我的一种自觉选择。”他还宣称,“当民族振兴的时代开始来到的时候,我们希望一切从头开始,希望从受伤的地方生长出足以振奋整个民族精神的思想来。”从上述自述,我们不难发现陈凯歌所一向秉有并在他的风格性化的,颇具“作者电影”味道的影片中感知那种“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式的历史使命感、时代精神、启蒙理想乃至焦灼、沉郁的艺术意蕴。
在一定程度上,陈凯歌在他早期代表性电影作品《黄土地》《孩子王》《大阅兵》等影片中,都寓言式地传达了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界反思民族痼弊,批判国民性、追求“现代性”、向蔚蓝色文明大踏步迈进的高远理想。虽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与其少年英气不甚协调的悲凉沉郁和苍凉迷茫,但总的气象是积极向上的。此后在时代文化的剧烈转型中,陈凯歌的探索似乎因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似乎一直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他陷入一种矛盾和冲突之中,创作追求开始分化。
《边走边唱》在主题意向上有所偏移,更为凸显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艺术理想,自我意识、人生追求等哲理主题,民族历史感有所淡化。
15年前斩获“金棕榈最佳电影”的《霸王别姬》是各方面都结合得比较好的成功之作。主题宏大,试图把京剧舞台与历史舞台合一。巧妙地借用了“戏中戏”结构。影片非常重视戏剧化的视觉形式的建构,在视觉美感上颇具凄艳华美的意象美。《霸王别姬》的时间跨度很大,它以中国50年的历史为背景,试图表现人陛的两个重要主题:迷恋与背叛。影片借用“戏中戏”结构,把京剧舞台与历史舞台合一。对一种文化的历史变迁表达了深情款款的关注,有明显的包容万象、概括历史的雄心。
程蝶衣的形象似乎与陈凯歌《边走边唱》中的探索一以贯之。陈凯歌自己说过,“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程蝶衣这个人物是创造者的一个支柱。作为一个演旦角的演员,他的生活跟舞台表演没有办法区分。”
总之,《霸王别姬》是一曲传统文化的挽歌。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内省,也有迷恋与赏玩,对待传统的态度比较复杂。
在陈凯歌电影创作的历史上,《霸王别姬》具有一定的转型性意义,它一反过去对理念表达和华美造型的迷恋,而是比较注重讲故事和叙事性,通过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情节,把一个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此后的《风月》在题材上颇有猎奇、猎艳、奇观化之嫌,其原意虽在于挖掘人性的深度,在情节剧中探索人的本真和生命状态。但似乎略显病态。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陈凯歌的《风月》就是一次向精神废墟的寻踪。在昨日的废墟里挖掘,在废墟的迷宫里恋栈,从而也使他的理想主义在废墟的阴影里失落的电影之旅。”
《荆柯刺秦王》让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虽然气势很宏大,人物丰富复杂,心理世界的探人也颇为深刻,视觉效果极好,通过加字幕呈现的结构方式也很有特色,电影语言更是纯熟老到。电影无疑是试图借助历史演义讲述关于权力异化的寓言。一以贯之的是对秦王之人格分裂和异化的哲理思考,权力对秦王的异化是通过秦王与其父、与其母、与其友、与其情人等的多重复杂关系展开的。但这种方式太满,个人主观化、刻意化痕迹太重,此外影片结构性很强,似乎是对历史进行重新观照和结构,但有些负荷过重显得不和谐。
陈凯歌的《和你在一起》虽是陈凯歌难能可贵的回归平民和世俗之作,但世俗却未能免于庸俗。把一个本来颇有现代性意味的关于个人价值自我实现与亲情伦理冲突的复杂主题,简化为未免简单化的伦理价值评判,而且有一种伦理至上的意味。更不乏煽情。两个对立的教授的设置尤其脸谱化和类型化,冲突的依据不足,缺少应有的张力。影片的影像堪称流光溢彩,哪怕是大杂院的平民生活,都拍得很漂亮华丽,也很不现实。这既反映了陈凯歌之类成功人士与中国现实的“隔”,也折射了他一以贯之的那种精神贵族的格调。
总之,比起张艺谋的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引领时代潮流,陈凯歌的电影探索,如《风月》《荆柯刺秦王》《和你在一起》《无极》等,往往是主观意图太强烈,想要表达的主题太复杂,总给人留下不和谐感以及诸多遗憾。在我看来,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是文化语境的巨变。陈凯歌在时代文化转型的巨变中显得有些迷茫,这影响到电影文本层面(如叙述结构、悲喜剧风格、价值取向等)上的不和谐。往往是既反映了文化转型的一些趋向(如视觉奇观化、投合西方的“后殖民”倾向、封闭的淡化时代背景的大宅院、叙事性的增强、世俗化策略等等),同时又顽固地保留了第五代的一些理想(如历史感的追求、寓言化的表意策略)。总之,其电影表意的复杂错乱是文化转型年代所有复杂性的表现。
进入新世纪。经历了《无极》的低潮后,陈凯歌似乎憋足了一口气,选择回归“文化电影”,又一次表现和解读他体会甚深,或可称驾轻就熟的中国文化精粹——京剧。取材于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故事,拍摄带有“传记色彩”但又合理虚构的《梅兰芳》,它代表了陈凯歌艺术电影的新世代新风貌,成为陈凯歌电影从常常有点“浓得化不开”的超越性哲理追求到回归现实、人生的“世俗化”转型的重要里程碑。
《梅兰芳》聚焦于梅兰芳的心灵世界,三段式结构虽未道尽大师一生,但这部具有浓郁“文化感”同时又极为重视讲故事的“情节剧”,展示了一代京剧大师的艺术人生和心灵史,也饱含了导演陈凯歌自己坚忍执著、欲说还休的人文诉求和艺术情怀。
全片以梅兰芳的人生轨迹为时间线,不同于《霸王别姬》将近半个世纪的感情纠葛和世事沉浮,导演这进行了删减,只为我们展现了其一生中“死别”“生离”“聚散”三个重要片段。既大
刀阔斧,又细致入微,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泼墨写意的笔法,点彩构砌,浓缩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
作为具有“传记”性质的电影,传主本身对导演具有约束性,不允许导演超越事实本原,进行天马行空的情节虚构和悲情演绎,作为一代文化名人的梅兰芳毫无疑问更应该是“雷池”多多的。导演首要做的就是“还原”原本,但是导演并不拘泥于“还原”与“再现”,而是进行“诗意”的处理和合理的虚构,使全片在写实的基础上具有“写意化”的浓郁抒隋色彩和戏剧冲突性较强的情节剧特征。就片中的感情戏来说,那段梅孟之间由钟情到幻灭的爱情,在导演那里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戏剧冲突。相反,充满写意性、扑朔迷离的爱情借用“京剧”来暗喻曲折表达。既含蓄蕴藉又充满诤隋画意。经过电影的这种“诗化”处理,这段感情显得纯净美好并且励志;显得既是遗憾一世。更是千古必然,几乎成了—个晶莹剔透的传说,—个劳燕分飞的慨叹。一个流传千古的爱情寓言。与此相似的是梅兰芳与邱如白的关系,也是恰到好处。张力十足,耐人寻味而扑朔迷离。虽然导演并未刻意渲染,但如有观众(特别是对同性恋话题可能特别敏感的西方观众)往那边猜测,我以为这反倒是影片吸引观众的某种“情节剧法“的成功之处。
影片的第一篇章主要关注梅兰芳的京剧艺术革新问题,但往后第二、第三篇章,导演并没有把笔墨的重点继续放在梅兰芳艺术的追求上,而是放在他怎么做人上,细腻真实地浓缩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即使是关注艺术革新,导演似乎也是更为关注怎样做人。如“斗戏”段落。“爷爷”十三燕实际上成为一代老京剧艺人的文化形象。“祖孙擂台”这场戏的结局使梅兰芳开启了一个属于他的新时代。从这场戏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梅兰芳艺术人生成功的起点归功于革新,也源于京剧自身所内蕴的生命力。正如影片中少年梅兰芳所说“真正的好戏是人打破规矩”。十三燕期望梅兰芳提拔戏子地位的遗言,和他在最后一次擂台前的那句“输不丢人,怕才丢人!”最终成为梅兰芳艺术人生的导航。陈凯歌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流畅雅致的镜语表达、有相当概括力度的台词等。具象了京剧艺术的文化精神与人生精髓。在我看来,通过十三燕虽败犹荣。退出历史舞台的仪式化表现。陈凯歌对传统文化献上了一曲深情款款的挽歌,更留下了文化精神的照耀后世。而这种文化精神灌注于此后梅兰芳的整个人生。这又毋宁说是陈凯歌对传统文化的最高礼赞。
细细品味这浓缩的“艺术人生”,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以有限的篇幅,传达了无限的人生内涵和文化感,这似乎和导演本人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某种“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了导演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念,诚如陈凯歌自述,“我所有的影片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从大的方面说这主题就是人性,然后每部片子还有不同的附题,但都有联系,这联系的纽带是我自己的人生观,也可以这么说,我所拍的影片都是反映某一时期之内。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拍每部片子时,我的生命本身都受到了考验,拍片过程也自幌生命得以灌溉和培育的过程。”无疑,陈凯歌是一个自我意识极为强烈的导演,在许多影片中都寄寓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意图,刻下了自己强烈的个人化风格化印痕。也许可以说,就像陈凯歌曾表示的,在《霸王别姬》中,自己就是那个程蝶衣,在《梅兰芳》中,陈凯歌就是梅兰芳。就此而言,《梅兰芳》堪称陈凯歌的又一部精神自传。
陈凯歌本人也曾表示《梅兰芳》“让他有机会将梅兰芳先生的人格魅力纳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的确,梅兰芳的生命状态和艺术情怀与陈凯歌不无“神似”。导演似乎是把自己文人情怀和艺术人生寄托、浓缩在电影中了。在影片中,我们不难找到导演的影子。例如,梅与邱对“艺术有无国界”、艺术是否纯粹的矛盾也正传达了陈凯歌自身的矛盾,两种选择正是导演心中的两种力量冲突纠结的表现。而邱如白代表的是一个陈凯歌的另一个自我——“本我”。从邱如白带有的明显悲剧意味的追求和无法得到别人理解的悲惨结局,到梅兰芳有容乃大、历尽劫波而修成正果(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梅兰芳从台阶往高处走的仰拍镜头所流露的),暗喻了梅兰芳自己从纯艺术理想追求到人间烟火的世俗化追求的心路历程。
“纸枷锁”也许是导演对自己艺术使命的一种自我隐喻。在我看来,纸枷锁有点像英国电影《红菱艳》中的红舞鞋,是一种挣脱不了的宿命,也是一种类乎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大无畏自觉追求。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梅兰芳慢慢地隐忍于宿命而坚韧,他的选择与坚毅正是导演给自己的心理暗示,就像导演自己所说“我从梅兰芳这里学到的,就是不怕输”。的确,梅兰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京剧艺术,就像穿上红舞鞋那样身不由己,也许是为了一种别无选择的文化使命(或文化宿命),他放弃了爱情和自由,虽然收获了巨大的成就,却也收获了无尽的孤独!
显然,导演并不着力于星现历史的史诗感,而是全力聚焦于个人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的丰富性和微妙性。影片是通过一个人的个体心灵世界的开掘而折射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点在人而非史(或者说是以人带史)。这与《霸王别姬》的史诗性取向是不同的。在《梅兰芳》中,历史只是一种写意化的背景(北京、上海还是香港的地域交代甚至还有点模糊不清),更重要的是,人物内心节奏的变化同京剧程式化的节奏起伏浑然交融,细腻中不乏浑然大气。如果说《霸王别姬》富含了历史史诗的韵味和气魄,令人荡气回肠的话,那么《梅兰芳》则呈现了一代京剧大家的孤独、丰富而痛苦的个体心灵史诗,真挚、细腻而传神。
从两部影片的主要人物形象看,《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艺术“异化”了,成为一种不无偏执的“为艺术而艺术”,戏内戏外不分的艺术精神的象征:而在《梅兰芳》中,梅兰芳则由原来人们心目中的精神载体、文化符号,而成为银幕上血肉饱满的“梅兰芳”,甚至是一个“凡人”,一个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的真实具体的艺人,这是一种“去魅化”的回归,一种心灵的“回归”。影片对梅兰芳不是“神化”而是“人化”,借此,陈凯歌仿佛也隐喻了自己的回归。从《边走边唱》中为一种理想和宿命而活的瞎子、《霸王别姬》中的“痴人”程蝶衣到今天的梅兰芳,我们足以感知时代的巨变以及陈凯歌心灵的流变轨迹。
导演陈凯歌曾表示,这部影片“写人不写事”,希望“把梅先生的精神世界表达出来。”他通过对梅兰芳的心灵史诗性的呈现,表现的不是梅兰芳的所谓“形似”,而是内在的“神似”,他是一个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就像导演自己所说:“这部电影能够部分接近梅兰芳首先是平凡人的内心世界,然后再看他怎么成为—个伟大的艺术家,成为一个优秀文化的代表。”梅兰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精神的缩影,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导演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一个这样的“梅兰芳”就这样诞生了,他不是一个空洞的偶像或符号。也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他是一个人,一个经过导演的投射,从导演心中产生的,也活在观众心中的“梅兰芳”!
这样的平衡点也意味着陈凯歌找到了高雅文化和大众趣味之间的契合点——一种文化中的个体人的命运、传奇和心灵痛苦!在人物众多而鲜活的塑造和井然有序的关系呈现以及表现剧情跌宕起伏的同时,他在这部高雅的、有文化的“情节剧”中灌注了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当然这与影片哲理性台词、程式化表演性京剧元素的有机介入、优雅的写意性视听语言,复杂而顺畅的镜头内部调度等都是分不开的。影片通过造型感强烈的视听语言,在三个段落中通过不同的节奏和基调,传达出人性、人情和人本的真实。“斗戏”部分的紧张激烈和“弃情”部分的凄凉感人在节奏上形成鲜明对比,使影片具有一种张弛有度的节奏感。
影片《梅兰芳》让我们欣喜,让我们在2008年的冬天感到温暖:陈凯歌浓缩、映射了梅兰芳的艺术人生与心灵史诗。带着他新的艺术追求与多年电影艺术和文化的反思,回到了我们中间!“与我们在一起”!
陈凯歌还是那个陈凯歌!不过,比以前更平易通脱而充实洞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