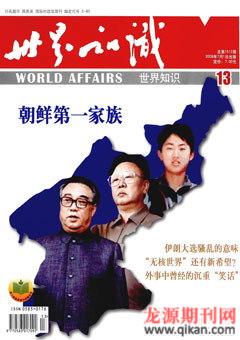“惟‘壮心不已’字可以当之”
“每一句话都要实实在在”
今年已89岁高龄的汪熙先生,是资深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国研究专家。目前,老人正在致力于《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的写作。
这位德高望重的复旦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登工商管理学院。曾任上海工商学院院长和名誉院长、美国通用再保险公司/科隆再保险公司副总裁等。与此同时,兼治古今中西,上下求索,孜孜不倦,成就斐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求索集》,选收了汪先生到那时为止的代表性文章。
中国近代史是汪先生长期耕耘的专业领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1993年)、《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1980年)、《论晚清的官督商办》(1979年)、《论郑观应》(1982年)、《一个国际托拉斯在中国的历史记录——英美烟公司在华活动分析》(1985年)等长篇专论,无论是选题、立意、观点还是材料,均在业内有口皆碑。汪先生反复叮咛学生的是,做学问“一定要肯做冷板凳。你要真正潜心地研究下去,如果心里想的太多了、太杂了,是不行的。写文章,也不要空话连篇,每一句话都要实实在在,要有根据”。老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专论都是立足于丰富、扎实、详细的中外文档案资料和相关研究专著。如《论晚清的官督商办》有注释181条、近万字,《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有216条注释、一万多字,其学风之严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出于对珍贵的近代文献的保护性整理和抢救的公益之心,汪先生还与他的两位好友,即已故的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和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教授合作,前后用了30年时间,锲而不舍,组织沪上专家从浩如烟海的旧文档中精心整理,编纂、出版了近千万字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原始文献资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
“轩然大波,全国学术界都骚动了”
与绝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局限于近代中国的偏狭视阈不同,汪先生一直立足于国际学术前沿的最新成果,并身体力行,为推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史和东印度公司史等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初,汪先生即率先在《世界历史》发表了引起学界内外广泛关注和重大影响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该文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出发,提出重新研究、更好地总结中美关系历史的创见。在汪先生看来,“中美关系历经曲折,有历史的创痛,也有美好的回忆”;“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是中美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中美两国虽有近两百年的交往,但相互了解还很不够……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历史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在增进中美友谊的现实生活中是多么重要。在这一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此,汪先生围绕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门户开放政策与中国领土完整、传教事业、人民交往等问题,主张用对立统一规律来重新研究中美关系史,既要研究中美矛盾的两个方面,考察与中美关系相关的其他矛盾以及诸矛盾的转化,还要仔细地分析中美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性质及其影响。该文纲举目张,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与罗荣渠先生随后在《历史研究》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遥相呼应,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国学界思想解放的代表作。
事隔20多年后,2005年,汪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曾专门回忆过《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写作和发表的来龙去脉及其刻骨铭心的独特感受:“文革”尽管已经结束了,但还有很多人不能理解。当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为这篇文章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文革结束后形势有很大的转变,觉得应该讲真话了。再不讲真话,糊里糊涂搞下去,中国历史就要走到末路上来了。我有一个老师叫陈翰笙,我寄给他看,他说好。发表是发表了,但是情况不对。我估计到打击一定是很大的,但是当时也不管了,反正已经到了喉咙口的东西非讲不可……我这算是第一炮。因为我考虑到中美关系史过去的研究方法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越走越死了,这对国家也是不利的。你片面地了解东西,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对国家掌握政策也是不利的。所以我想来想去,就写了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过去的话,我肯定是右派。没得办法想了。批评我的人很多。戴了我很多帽子,什么资产阶级买办利益的学者、美国的……轩然大波,全国学术界都骚动了……复旦大学很注意这个问题,把它仅仅限定为学术上的争论……这是学术问题,应当讨论而不是上纲上线,这很不错。从这个时候,情况也开始变化,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的意见。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好过一点,不然我就一下子不行了”。可谓甘苦与共,冷暖自知。这就是历史学家的遭遇。而且,这也同样是不可遗忘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之后,汪先生义无反顾,继续其新的探索之路,发表《门户开放政策的一次考验——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东亚的影响(1934-1937)》等长篇论文,并从1985年起主编出版大型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汪先生主张:“研究中美关系史,不仅要研究中国一方,也要研究美国一方,还要研究它的对华政策是怎样形成的——它的经济结构、政治集团、舆论动向和人物素质等在形成对华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丛书包括了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韩德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唐耐心著《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入江昭等主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 1949)》等译著以及《中国人的美国观——个历史的考察》(杨玉圣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张济顺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吴心伯著)等专著(共23种),其中晚近出版的即是汪先生等主编的囊括中、英、日文的《150年来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1823-1990)》这一大型工具书。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嘱咐说:“今后,希望每隔二十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或历史系都能相继有这样一本在时间上相衔接的‘目录问世。年复百年,成为复旦后来者永远保留的一个项目。”
“应该做的事太多,好戏还在后头呢!”
1999年不幸中风后,汪先生右半身偏瘫。但这并未难倒先生,右手不能写了,就靠左手用电脑上写作。他以顽强的毅力,至今一直坚持读书、写作。做学问是先生的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新著《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先生生病后写出来的。不久前去世的陈乐民先生在读了《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后动情地说:“我读后首先感触的,是汪老以耄耋之年,在身体又欠佳的情况下,完成这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所表现出的治学毅力。这部著述实为我国西洋近代史研究一大创获。就我所见,我们还没有这样对英国自1600年起二百余年的‘东印度公司资料如此翔实厚重的专门著作。”汪先生反复告诫学生说:“正确的观点只能从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离开事实的观点十有八九是错误的,而且离开了事实也不可能产生正确的理论。”故此,陈先生高度评价道:“汪熙老治史,特别是在西洋近代史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勤耕不息的榜样。他经验阅历之丰、藏书读书之多、上下求索之勤、提掖后进之诚,灼灼可见。近几年我每次到上海拜会他,看他坐着轮椅打电脑、梳理资料、兴致盎然地讲述他正计划还将做什么,毫无倦意,我想,惟‘壮心不已字可以当之。”这也正好契合了今年4月我在沪上见到老人时的印象。
“自从中国有了改革开放,我的生命就始于七十了,应该做的事太多,好戏还在后头呢!”这是汪先生1998年9月在其《求索集》“前言”中的夫子自道。“路是漫长的,我将在这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征途上永远前进、求索。”壮心不已的老人一再表示:“以后我还有东西要出来,叫《美国海军与中美关系》……我材料已经搜集了,我这几年到美国大概去了九次……我搜集了大批有关美国海军在中国活动的情况,这批材料收拾好了……我就要用剩下来的时间把美国海军和中美关系当中的问题搞出来。”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先生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