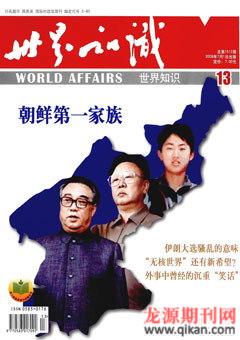舍本逐末,皆因利在末而不在本
张运成
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皮克最近放出话来:中国未来将在世界衍生品市场上成为重要角色。如果从风险角度来解读,或许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将处于下一次危机的“浪尖”上。
自由经济推崇的是以最少的监管来维持金融市场秩序,出了问题就让市场自行分配风险,消解风险。当金融衍生产品在全球发展到一个极为复杂的阶段时,风险大量累积,市场根本承担不起,最终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加以释放。既然“最少的监管”绑不住金融衍生品这头“怪兽”,不碰不摸又不现实,那么一味严加监管又是否能够奏效?危机以来国际上加强金融监管之呼声不绝于耳,但莫衷一是,未见良策。
并非金融“工具”本身的错误
究其原因,在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已经“本末倒置”,是方向和道路出现了问题,而不是“工具”本身的错误,因此也无法单靠监管就能扭转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人祸”,而金融机构之衍生品“上身”就是灾祸之源。金融业无限放大自身营利预期并不择手段加以实现,从保守的观点视之即必然需要“舍”传统按揭业务及赚取息差之本,“逐”投资和经营金融衍生工具之末。之所以要舍本逐末,皆因利在末而不在本。金融圈子一包括众多衍生品的投资者、提供者、经营者及参与者对此心知肚明,各种对冲基金、退休基金如此,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如此,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也是如此,争先恐后,前赴后继。
经历金融危机一劫,投资者自然会有一段时间对风险较高的结构性产品存有戒心,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正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在投资及财富管理业务方面将要面对重重困难。“back to basic”——更多地重新倚靠传统业务来维持经营,可能再次成为银行业的主流,各家银行业务发展由金融衍生工具回归至传统按揭业务,借此降低投资风险之余,也希望得到稳定回报。近期主要国家的多家银行纷纷推出各式按揭优惠,以图抢占按揭市场。据称,摩根士丹利已经率先转向华尔街传统经营模式。
银行要重回传统业务,就要简单化或去复杂化,但金融机构真正能做到简化相关金融衍生工具、提高透明度,又谈何容易,最大的困难还在于本、末牵动的利益链条和不平衡并未被危机打断,而且留给各国监管机构拿出有效解决之道的时间已经为时不多。当前危机之下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困难逃其咎而暂时“潜伏”,加之财富萎缩,衍生品生产过剩而需求急降,造成汇控、花旗等的投资银行部门自去年以来连续裁员,但金融衍生工具避险兼有撬动巨额利润的本质并无改变,功能也未消失。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这个“潜伏期”应不会太长。当前,尽管各国对衍生工具的表现“愤怒不已”,但规模近700万亿美元的场外交易(OTC)合约中的大部分仍然维持原状,它们是在苦撑待变,盘算着、等待着新的“狂欢”的到来。
一利兴,一弊随。金融衍生工具的误用与滥用,显然不能成为不用与弃用的借口。在利率、汇率大幅波动的时候,这些衍生工具可以用来规避风险;但同时也是威力巨大的高杠杆率押注工具。对中国经济而言,不碰不摸承担的风险要远远大于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除了参与其中没有更好选择。今年初联合国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称,非洲企业大多未沾手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对全球金融危机具有相对免疫力。但非洲的情况是尚未融入全球金融体系,这种“免疫力”显然对中国并没有吸引力。过去,中国一些国有企业因为不能抵御巨额投机利润的诱惑,以及不懂衍生产品背后的巨大风险,在衍生工具投资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栽跟斗。当前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能够做到趋利避害,那些投资损手的企业必须要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增强对衍生工具的认识,获得真正的“免疫力”;而那些声称“绝对没有投资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的企业在沾沾自喜和庆幸之余,恐怕早晚也要走上这条道,实在是没什么好骄傲的。
法律或条例,反而助长了衍生品交易的“胃口”
国际金融市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主要可分为外部监管、自律监管及内部风险控制三种模式。但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避险与投机往往一线之隔,有效监管不仅十分棘手,事实上也做不到。金融衍生品交易3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角色表明,国际金融体系的监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和将来,恐怕都难以赶得上市场本身发展及产品创新的需要。例如,各国监管机构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充分掌握此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主要国家和地区先后对涉及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过立法,然而法律或条例本身反而助长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胃口”。
1999年,美国国会在金融行业强力公关游说下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合并,从而摧毁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保护民众储蓄和企业资金免受泡沫风险的“防火墙”,为游离于联邦政府严格监管之外的范围更广、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的出现提供了温床。2000年,美国国会进而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其中包括被视为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掉期”(CDS)。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容许投行把杠杆从L5倍放大到40倍,自此,投行可以用有限的资金,把业务做得更大。但在业务扩大的过程中,投行发觉,如果采用传统的经营手法或按照政府容许的杠杆操作,收益有限,只有把金融衍生工具产品的影子银行业务做大,才可以大赚特赚。
2003年香港修改证券及期货条例,容许银行向客户出售投资相关产品,实际上就是金融衍生产品。此例一开,不论大小银行,均争相开设个人银行及理财业务,以增加非利息收入。由于不少中小型银行本身缺乏开发投资产品的能力,于是便充当其他银行所发行产品的分销商,利用银行本身的客户群来增加收入,并且将推销对象放到了根本看不懂合约、看不到风险的高龄客户群。香港案例的最大教训是,一般投资者主要是小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以致最终形成类似“雷曼债券事件”一样的政经难题。
2007年11月1日,号称“欧盟历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金融法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正式生效。根据这部法规,欧盟范围内证券交易所将不再是投资者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惟一途径,银行和投资公司也可以搭建自己的交易平台,与证券交易所同场竞技,其本质就是推动大家一起来分享金融衍生品这场“盛宴”。
在一片对金融衍生品要加强监管的呼声中,需要保持清醒,要认识到可能带来的弊端:一是金融危机无疑令监管者和金融机构都备受压力,但切勿盲目监管,监管是否有效的标准还在于参与者是否遵守游戏规则。香港监管部门就认为,目前上市公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所遵从的风险披露准则已经足够,无需作出修改,但前提是上市公司遵守规则。二是强迫所有OTC衍生工具转为进行场内交易,或许可起到减少市场投机的作用,但会难以满足包括企业和保险公司在内的很多用户风险对冲的需求。监管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制定适当的监管法规,既能发挥价格透明度等场内交易的优势,又能保护产品创新和个性化。三是一直以来,国际投行的竞争模式就是寡头垄断,少数的竞争者控制了整个市场,具有极大的议价能力,形成其超级的赚钱能力。这提醒监管部门在出台政策时要十分审慎,因为长远来说,监管愈多,经营门槛就愈高,竞争对手也就愈少。
历史不会重复,但其剧本可能一演再演。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皮克最近放出话来,中国未来将在世界衍生品市场上成为重要角色。如果从风险角度来解读,或许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将处于下一次危机的“浪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