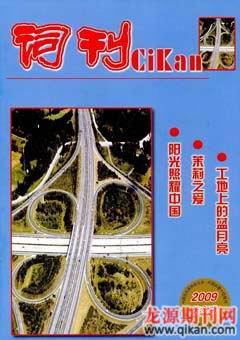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一 盈
他身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才华”,另一个是“相貌”。有“粉丝”这样评价他:“横溢的才华吓跑了脸上的帅气。”还有人描述他的长相:“有惊无险,像街头路人甲。”最损的莫过于吴宗宪“歹毒”的大嘴:“看看他的词,再看看他的脸,这时你才明白,原来上帝多么公平!”
此刻,被人捉弄的他像小学生般坐在我面前,姿势端正稳当,带着一种刻意而为的老成庄重。但随着谈话的深入,他渐渐兴奋起来,身体语言频频增加,眼神变得单纯而快乐,令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遥远的台北,雨后的花园里,他拿着铲子,心满意足地蹲在一片自己搭建的微型“桃源”前,傻呵呵直笑。
事实上,在我眼中,所有关于他的调侃都有些言过其实,就像人物漫画,夸大人物外形特点从而达到会心一笑的目的。他并不丑,是典型的闽南男子:矮,黑,憨厚,敦实,普通话含糊、拖音,“酱紫”与“这样子”分不清。不同的是,他学会了打扮——花衬衫领子从蓝牛仔外衣中翻出来,扣子大方地解至胸前第三颗,脑袋上扣顶花哨的牛仔棒球帽,后面翘着细细的马尾,明星“范儿”十足。
他便是方文山,周杰伦的“御用”词人。从几年前的《娘子》、《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等一直到去年感人脏腑的《菊花台》,他几乎包办了周杰伦所有脍炙人口的精品,成为今日歌坛中无法振动的“指标性人物”。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话放在今天或许过时,但方文山却对它有切身感悟:“如果说‘励志是一件商品的话,还有什么人比我更有资格、更适合代言呢?”听听,又是一个麻雀变凤凰的故事。
《读者》(原创版):你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范本写过一本励志书《演好自己的偶像剧》。之所以有如此感悟,是否因为自己的成长故事充满励志色彩?
方文山:成长对我来说并非一帆风顺。我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小乡镇的蓝领家庭,故乡是桃园龟山。因为家境不好,我很小便开始勤工俭学了。每到寒暑假时我一般都会外出打工,比如送报纸、当餐厅服务员、做业务员、当高尔夫球童……当时也会觉得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蛮感激。因为有过那些困顿、不如意和苦难,今天的自己才会懂得惜福。
《读者》(原创版):你在歌词创作方面的成功,大家更愿意归功于“天才”甚至“鬼才”两字。果真是这样吗?
方文山:不算是。其实我很晚熟,不像很多天才儿童那样从小展露锋芒,只是从小喜欢乱写而已。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一直没有明确目标,直到二十多岁退伍才认定电影和写作是自己的理想,开始大量写字。
《读者》(原创版):既然电影和写作是你的理想,那为何却写了歌词?刚开始写时是种什么状态?
方文山:当年我本想进电影圈发展,但是行业不景气,只好退而求其次写歌词。我想反正都是创作,总有一天,自己会慢慢靠近电影圈的。当时我的工作是安装防盗系统,类似水电工。工作时我会随身带一个笔记本、一支笔,边工作边想歌词。有时突然想到一句好歌词,赶紧停下工作,掏出笔记本,把歌词记到本子上。就这样,一年下来写了一百多首,四处投递出去,最终只有宪哥(吴宗宪)回了我的电话。
《读者》(原创版):当时是什么感觉?有没有想过如果吴宗宪不回你的电话,将会怎么办?
方文山:当然很吃惊、很意外,不敢相信电话那头真的是吴宗宪。(笑)不过即便接不到宪哥的电话,我也想方设法进入这个圈子,比如去唱片公司或电影公司当行政助理。
《读者》(原创版):看来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方文山:是的,只是我更是一个懂得步骤的理想主义者。
《读者》(原创版):与吴宗宪签约,是否令生活发生很大变化?
方文山:没有。签约不代表有收入,只能证明自己是公司的人,作品会优先采用。当时签了很多人,大家都需要拼歌。譬如说一首旋律定下来,好多人写歌词,互相比,谁的被采用才会有报酬。如果没有被采用,是连底薪都没有的。所以竞争也是蛮残酷的。
《读者》(原创版):什么时候你的歌词才被首次采用?
方文山:进公司一年后。在这一年时间里,我没有任何创作上的收入。当年签约那么多人,最终也只有我和杰伦熬了下来,其余的最终都另谋出路了。
机会显然眷顾方文山。当吴宗宪幸运地光顾之后,周杰伦又呼啸而来。9年前,这个和方文山同时被吴宗宪选中的青葱少年还只是一块璞玉,未经雕琢,粗糙黯淡,但方文山却隐约感受到那青涩背后逼人的光。
《读者》(原创版):周杰伦给你的最初印象是怎样的?
方文山:我们同时被宪哥签下词曲经纪约。起初对杰伦的感觉是:嘿,这个年轻人有些与众不同,做事酷酷的,可他凭什么那么酷?慢慢接触久了,我发现他的确不错,他的音乐的确比别人更有创意。一年后他签了歌手约,显然是个可造之才。
《读者》(原创版):你和周杰伦算是一对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但是任何黄金搭档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番艰苦打磨。能不能谈谈你们这对搭档是如何磨合的?
方文山:我和杰伦并非一开始就搭档,只是我们慢慢发现,彼此合作最默契、最能擦出火花。于是渐渐固定下来。刚开始合作也有摩擦,比如针对一首歌,我会认为多写几个字或换另一种写法能令它更饱满。为了维护作品的完整,我宁愿不拿版税也希望他重唱。但他却认为重唱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就不愿意重唱。印象最深的是《娘子》那首前面的一个RAT,他很即兴地把我的歌词当RAT唱,我觉得意思不完整,想重写,但他却认为自己唱得已经很OK、100分了,怎么也不愿意重唱。渐渐地我也学乖了,以后他再唱歌,我就坐在录音室里随时修改,不会等录完音后再犯难。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说过,周杰伦是天才型作曲者,你却是用功型作词者。你们的天才和用功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方文山:杰伦的创作浑然天成、挥洒自如,好像神来之笔或天外飞仙。每当他有灵感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一两个小时就能创作出作品。可我的创作很有概念。比如写一首歌,第一段写好后,我三天不再碰它,到了第四天,我接着再去写第二段,下一星期,又去写副歌。在写歌的过程中,我会比较谨慎,会去收集资料,随时补充打磨。
目前,“粉丝”们为方文山与周杰伦的地位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法是周杰伦捧红了方文山;另一种说法是方文山成就了周杰伦。更有观点认为:这个年代,如果没有周杰伦,音乐将会很寂寞,如果没有方文山,周杰伦也会很寂寞。
《读者》(原创版):关于你和周杰伦彼此的作用,很多人都在探讨甚至争论不休。你自己认为呢?
方文山:我们是相辅相成的。曲是架构,词是衣服。可我觉得,杰伦的曲天生已经很匀称了,旋律本身已经很动人,即便没有我的词,它一样存在,不会折损到什么程度。我只是帮他的旋律加画面,提供故事,让它更有血有肉。
《读者》(原创版):周杰伦给你下了一个定义:一点儿也不天才的诗人加鬼才加呆子的笑柄老实人。是这样吗?
方文山:(笑)很贴切呀。人都有多个侧面,我在某些方面很迟钝。比如电脑、英文很差,生活能力基本是白痴,很笨的。呆子就呆子吧,无伤大雅。至于笑柄老实人,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爱恶作剧,爱搞笑吧。(笑)
《读者》(原创版):你如何评价周杰伦?
方文山:自恋、天才、搞笑。生活中,杰伦和我爱互相捉弄。比如他生日时,我可能安排一些朋友演警察吓唬他;而我过生日时,他会安排朋友演狗仔队跟踪。(笑)
《读者》(原创版):有没有想过如果搭档不是周杰伦,而是别的歌手,你的歌词还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吗?
方文山:我想不会。好的作品需要好的曝光平台,正如一个好演员需要一个好导演。反之,即便他的演技很好,但总演二三流的影片,大家也不会欣赏。杰伦的曲风便是强有力的曝光媒介,这种强强联手的效果便是“1+1=3”。
《读者》(原创版):从吴宗宪到周杰伦,你拥有两次令人艳羡的机会。由此看来,你也算是相当幸运的人了。
方文山:是的。但我觉得机会和实力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实力,当机会来临时,你无法长久把握。机会是叩门砖,实力是枝繁叶茂的保证。
《读者》(原创版):9年来,你们这对黄金搭档创作过许多优秀的作品。你自己最满意哪一首?
方文山:《菊花台》。这首歌有点儿像量身定做。杰伦先给我看电影脚本、花絮,于是我便明白歌词要表达的元素:菊花、季节、分享等。因为主轴很清楚,所以我写得也顺利。
从《双截棍》、《东风破》、《七里香》,直到今天的《菊花台》,方文山用天马行空的文字与瑰丽的想象一次又一次冲击我们的感官。关于自己“鬼才”的秘诀,他老老实实解释:演好自己的偶像剧。
《读者》(原创版):置身于竞争激烈的音乐剧,你觉得自己的歌词能在浩若烟海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方文山:风格。创作歌词时,我会故意强调段落与段落间不见得有关系,但阅读时依旧有主题。比如《爱在西元前》,我的第一句歌词是:“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刻在黑色的玄武岩,距今已经三千七百多年。”这句话只是叙述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但第二句是“你却在橱窗前,凝视碑文的字眼,我却在旁静静欣赏你那张我深爱的脸”。如此一来就把人称代词“你”、“我”、“他”联系起来,把情绪连贯起来,整体形成了感觉。
《读者》(原创版):你的歌词有浓重的东方民族韵味,也有怀旧气质。这是否是你个性的反映?
方文山:中国电影和古典诗对我影响很大。我个人也喜欢怀旧复古,喜欢旧东西,车牌门牌、残砖片瓦以及一切和历史相关的东西。因为历史已经灰飞烟灭,但它们却带着历史的印记,很有感觉。
《读者》(原创版):“特色”这两个字令很多作者又爱又恨。在这个文艺泛滥的年代,寻找自己的特色或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方文山:我想大家焦虑的不应该是风格的确定,而是作品要源于自己的内心与原创,没有模仿或抄袭别人。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急躁,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要幻想凭一首歌就确立风格。我们不也努力了很久才慢慢被大家接受吗?只有当作品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大家才会关注你、评论你,才有可能让你成为风格鲜明的作者。
《读者》(原创版):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最大的悲哀是不想当自己。
方文山:几年来,我在圈内看到许多年轻人不想扮演自己,永远羡慕别人。比如王小明本应该是快乐的男生,应该和朋友爬山、健身,但他却不想当王小明,而是成天幻想当周杰伦、刘德华。我觉得,即便演艺圈出现一个章子怡,可你更应该看到学表演的成千上万人。与其羡慕别人,耽误自己的人生,不如多看看那些失败的案例。
《读者》(原创版):你的词里有浓重的思乡情结,比如娘子、琵琶、牡丹江等。这些年,你也经常往返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关于大陆,你的感受是什么?
方文山:距离是一种美。没有大陆之前,我会有很多憧憬与想象。比如北京,我会高想有很多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胡同等。但来到这边,我才发现大陆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古旧沧桑。北京把很多与历史相关的东西都拆除了,现代化比台北还厉害呢。刚开始我会有些失落,但久了也渐渐明白传统与发展的两难。
记者手记:
方文山太红了,以至于这个采访不得不分两次进行。前半部在北京,后半部分电话追到上海,就差没通过海底电缆,随着他的行踪到台北了。
数年前,这位当红词人还是位头顶安全帽、拎着电钻奔波于尘堆瓦砾中的蓝领水电工,可如今,他已经坐在豪华会客厅里,在频频闪烁的镜头中,举止得体地应付一拨又一拨记者的进攻。
在“一切皆有可能”的今天,人人都有理由憧憬由麻雀变成凤凰。只是,变成凤凰的方文山却一再提醒:先甘心当一只麻雀,潜心演好自己的偶像剧。否则,既错过麻雀的欢愉,又无法企及凤凰的荣耀,那岂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转自2007年7月《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