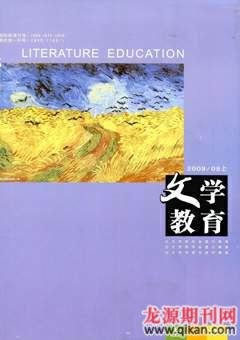悲哀的“向日葵”
一
“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①这是凡高之死——面向太阳朝自己开了一枪。
凡高,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热烈的画家,有《向日葵》为证——黄色的背景,黄色的花瓶,黄色的花,深黄,浅黄,柠檬黄,橘黄,土黄,阳光的金黄,永远向着太阳的向日葵,这是热烈而狂躁的凡高的代表。凡高也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为悲苦的画家,可以《悲哀》为证——瘦骨嶙峋的手搁在膝头上,面孔埋在细瘦的手臂中,稀薄的头发纷乱地披在背上,干瘪的双乳直垂向无肉的小腿,平坦的双足不着实地落在地上,这是一幅以西恩(跟他生活一年多的一位妓女)为模特的素描画,难道不也是凡高的一幅自画像吗——悲哀而孤独。而《麦田与收割者》应该是凡高二者兼具的最好写照——一轮金光闪闪的太阳照在天空,周围的云彩全变成了阳光般的金子一样的颜色,而且似乎被烧着了一样,群山是浓重的一抹,像着了火的火焰山,燃得最旺的还是山脚下的广阔无垠的麦田,那分明是一堆熊熊而燃的大火啊,不,这也不是大火,而是凡高的生命激情在燃烧,是凡高的生命价值最大的释放;但是,那个可怜的孤独的收割者却又是凡高在现实社会中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二
凡高,现实生活中的“倒霉鬼”:十六岁开始工作,失恋失业,做传教士因为“过于热情”又被解雇,而后当画家,却又进入了疯人院,穷得只能靠弟弟来养活,自割耳朵还失去了朋友的友情,他一生中仅仅卖出一幅画,价值不足一百美元,最后在37岁的时候,在自己挚爱的黄色麦田,开枪自杀,时间是1890年7月27日,两天后,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但是,他生命凋谢的同时,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省略号,他的另一种生命开始重生。
1891年,凡高的遗作得以在独立沙龙展出;1893年,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件开始发表;1901年,凡高画展在巴黎举行,给后来的野兽派画家以强烈的影响;1905年,阿姆斯特丹国家美术馆举办凡高画展……1934年,《渴望生活·凡高传》出版,到了今天,此书已销售几千万册,凡高的事迹打动了全世界的人……1962年,在凡高侄子的努力下,荷兰政府修建了阿姆斯特丹国立凡高美术馆,永久珍藏凡高的作品和书信,这也是现在收藏凡高作品最多的艺术馆……1987年3月《向日葵》被日商保险公司以3990万美元购得,他的另一幅名作《鸢尾花》更卖得5390万美元,几年后《伽塞医生》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被日本纸业大王斋藤英买走了,这是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
我相信,生前的悲苦不是凡高需要的,但也不是他想改变的;而死后的喧嚣却一定不是凡高所追求的,因为凡高就是凡高。
三
很多人喜欢引用下面这段话来说明逆境出人才:“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报任安书》),从此出发来评凡高,那就是因为生活的穷困潦倒而使凡高走上了艺术道路。这实在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要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凡高家族是欧洲图画商界最大的家族,与他同名的一个叔叔又没有后代,他实际上有可能控制欧洲大陆的艺术,他的弟弟提奥不也正是荷兰有名的艺术商吗?他自己一开始工作就在叔叔的古皮尔艺术公司任职,从海牙到伦敦。但是他拒绝了这样的生活,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将他唯一的一生花费在把非常蹩脚的图画卖给非常愚蠢的人”②这是非常不正当的行为。他宁愿穷困也不愿背叛——背叛自己的灵魂。
另一方面,有人说,凡高的伟大是以他付出世俗性的享乐为代价换来的,这也是一种很表象的评论。凡高何尝不想高价卖出他的画?何尝不想吃好穿好?何尝不想享受惊心动魄的爱情和温情脉脉的亲情?谁不需要生存啊,他接受有五个孩子并怀着孕的妓女西恩,也是一个证明。但我们必须承认,世俗生活的恶劣使他走出了庸俗。厄休拉,这个房东家的女儿,凡高的初恋,她对他的轻蔑,促使他摆脱了庸俗的生活,如果,她答应了他的求婚,凡高将在伦敦的古皮尔艺术公司终老也说不定;表姐凯,她的“不,永远不!永远不!”永远辛酸地铭写在他的心上,否则他也许就是一个有些固执但不乏爱情的普通丈夫。
所以,我们说,凡高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凡高,不在于他以顽强的意志在逆境中破茧成蝶,也不在于他牺牲世俗生活而醉心于艺术世界,应该是因为他献身于他的艺术时,并没有指望这种献身去换得名利,也没有因为生存的窘困而放弃他的绘画,他敢于挣脱生存世界把价值世界从生存世界中分裂出来,使它们独立而存。
四
在生存世界,凡高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他完全可以投靠叔叔而享受荣华富贵,但他没有,因为那将以牺牲他的价值世界为代价,在“快活”与“心安”不得兼得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在价值世界,凡高只做心灵依托所召唤他做的事,因为那里是安放他灵魂的地方,这就是执着。
我们不回避,也不能回避欲望世界对价值世界的浸染,比如在初识西恩时,凡高因为付不起西恩的一英磅模特费他只能停止绘画;他自杀前,因为一向提供他生活费的弟弟有了小孩,体弱,失业,本性善良的凡高决定撤退,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凡高因为生存世界的逼迫而死,他作为一个自然的人的生存能力实在是极其低下,他寄生虫般的生活也让他对自己深恶痛绝,最后的自杀或许也是他摆脱寄生虫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强调的是,凡高对使自己“心安”的价值世界一向是从不为外物而影响的,艺术是凡高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带着强烈的“凡高”印记。正是因为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现“食土豆者”们,才使得自己的画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即使这样,他还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他说:“我能够在那些不幸的年月活过来,是因为我必须画画,是因为我必须表达我心中燃烧的东西。”③自杀后,在凡高身上发现的一封信中,凡高说:“说到我的事业,我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为它,我的理智已近乎崩溃。”他还说:“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肉体和灵魂,为了它,我甘冒失去生命和理智的危险。”他的艺术不是“为人生而艺术”,那只有群体观;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那只有个人闲适感;而凡高的艺术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现,不存在谁为谁的问题。正因为他的“向日葵”、他的“麦田”、他的“星空”镌刻着凡高的个体人格、个体精神,所以才产生了震撼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种执着通过他的行为来说明可能更通俗易懂一些。
凡高在被厄休拉拒绝后,回到了荷兰,但他拒绝了荷兰较为舒适的工作,再次跑到英国,在一个叫拉姆斯美特的小城谋得一个只供食宿没有薪水的职位,仅仅因为厄休拉还没有婚嫁。在几乎每个周末,这个没有一分钱的穷光蛋,只为了看一眼他心爱的姑娘,他从周五晚上开始步行,去丈量火车程也要四个半小时的伦敦路,他不吃不喝不睡,一心一意地只是步行、步行,等周日早上看一眼出门去教堂的厄休拉,他再往回步行、步行,周一早晨回到拉姆斯盖特的凡高该是怎样的狼狈又满足啊,这是怎样一个分裂的世界啊。这样的日子一直到他亲眼目睹厄休拉结婚,“他步履艰难地冒着大雨走回艾尔沃思,收拾行装,永远离开了英国。”④
五
凡高是一个执着狂,但他却是一个永远向着太阳的执着狂,他的这种向上的人格力量也成了激励后人的最强有力的催进剂。一个人忍受穷困不难,难的是同时守住一份精神执着;一个守住一份精神执着也不难,难的是坚守一份永远向上的执着。而凡高做到了。
在博里纳日矿区,他跟矿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给自己留下一件衬衫、一双袜子和一套内衣,其余的衣被全都送给了孩子、老人和孕妇,就在由于“过于热情”而被教会解雇以后他还把提奥寄给他的生活费全部送给了矿工们。他到处借钱帮西恩度过生育难关,帮西恩养育她的六个孩子。他帮助他们,是因为在他心中,是他们帮助他热爱世界上的被人瞧不起的人,是他们让他懂得了爱人、爱生活。
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啊,他把这种挚爱用他的画笔铺叙在他的画布上,这也是他不同于他人的地方,凡高所关注的不是再现对象,而是利用形和色来表达他对观察对象所获得的个感受和内在激情。传达给别人的也就是这种亢奋昂扬的激情——单纯热烈的颜色,翻动涌动的线条,狂放不羁的风格,脱却了自然物象的束缚,肆意畅快地渲泄着他对生命本质的认识和追求。他的“向阳葵”不是自然的真实写照,而是他生命与精神的自我流露,是他以火一般的热情为生活高唱的赞歌;他的“日月”也不是自然的星月写真,而是他那孩子般单纯的心灵在绚烂星空下的一种被媚惑,是痛苦和幸福的一种折射;他的“阳光”、他的“麦田”全是他疯狂挚爱的精神外化。即使是黯淡,即使是灰色,在边缘,在背后,我们还是读到他对生命的无比关爱和对生活的无限留恋。凡高的作品是一个充满着善良、对美和创作想象自由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创造,他短暂的一生都用于追逐和寻找他理想中的色彩。
六
凡高,为了令他“心安”的价值世界背离了能让他“快乐”的生存世界,他又不囿于窘迫的生存世界而放弃他的价值世界,他把两者分裂又让两者分立于他的生命之中。他没有为了世俗的伟大而放弃人格的伟大,他没有拜倒在“伟大”之下,他跟艺术是合为一体的,人格力量是非凡的。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征服了后人,让凡高身后“价值”突飞猛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升值同时也存在着凡高生前所不能接受的庸俗——他窘迫的生存环境、他分裂的精神状态、他不长的艺术生涯、他有限的作品数量、他对生命的自我戕害都成了他“升值”的某种理由——凡高的热爱者们是多么希望当时的社会能多给他一些关怀和理解,至少,一位天才的画家不会生活得这般艰难,走得这么的匆忙和悲壮。
现在的世人眼里崇高的凡高,那时的凡高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只为自己的生命价值活着,而不是为了身后的价值世界而奋斗着。现在的凡高,也是一个俗化的凡高,他活在别人的敬仰中、爱慕中、哄抬中,我相信这不是凡高所想要的。他只想要一个放他灵魂的世界,一个让他自己“心安”的世界,凡高,这个不俗的名字;凡高,这个不朽的名字。这是一株生存状态“悲哀”,但价值状态永远昂扬的“向日葵”。
这就是凡高——生活在低处,灵魂在高处。
注释:
①(美)欧文·斯通,刘明毅译.渴望生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521.
②(美)欧文·斯通,刘明毅译.渴望生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22.
③(美)欧文·斯通,刘明毅译.渴望生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517.
④(美)欧文·斯通,刘明毅译.渴望生活[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30.
参考文献:
[1]吴炫.否定本体论[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欧文·斯通著,刘明毅译.渴望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郭惠芬,江苏无锡高等师范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