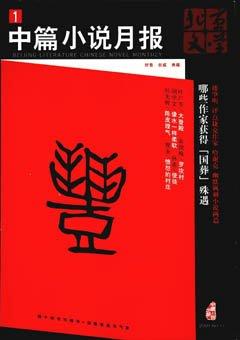像水一样柔软
一
直到离开村庄,罗盘依然想着数日前的那个黄昏。
当街站的人都听到了宋如花的尖叫。罗盘自然也听到了,但他只是回头瞥了瞥。宋如花总是一惊一乍,四十多岁的人了,没一点儿定性。罗盘不,心慌脚不乱。呛死了,呛死了。宋如花一路走一路揉眼睛,风把她的声音荡过来,如同飞扬的空壳谷子。宋如花就这样把众人的目光拽定。人未站稳,话已离开舌根,烟不往外冒,往家里扑,呛死了。罗盘料定她没什么事,不就是烟囱倒扑烟么?马上有人说,炕堵了,掏吧。宋如花犯愁道,这顿饭咋办?像问罗盘,又像问众人。罗盘没说话,别人遇到难事都是找他拿主意,自家的事还要人教?罗盘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他从不在琐事上和人废话,表情往往更有力度。果然,没人再搭茬儿了。
宋如花跟在罗盘身后,征询地问,要不,掏掏?罗盘不答,走了几步,突然回头,什么饭?宋如花说,莜面饺子,馅儿都剁好了,就差和面……你瞅我的眼熏成啥了?罗盘并不看她的眼,他说,炸几个辣椒搁进去。
罗盘找根竹竿,在竹竿一端绑上旧布条。随后爬上房,把绑布条的一端插进烟囱,反复抽动几次,烟灰扑出来,啄着他的头发眉毛。罗盘对院里的宋如花说,你再试试。几分钟后,宋如花跑出来,行了,不冒了。
罗盘没有急着从房顶下来,他在房顶没什么目的,就是想坐一会儿。罗盘家房子地势高,目光拉出去,整个村庄尽收眼底。房屋不整齐,前一户后一户,像一群没垄行的蒜头。烟囱七高八低,有的冒烟,有的没冒。没烟的多数是到城里去了,门窗也都用泥巴糊了。风一阵比一阵软,拂在脸上,像一只毛茸茸的手。一只燕子从罗盘眼底掠过,罗盘的目光追着它,可很快它就没了影儿。燕子把一个新的季节捎来了。罗盘想,明儿得把化肥拉回来。
罗盘闻到莜面饺子的香味。罗盘被香味勾回来,不经意地往远处瞟瞟,目光突然冻住。罗盘看见了侯夏。准确点儿,是看见了侯夏院子里的侯夏。侯夏家和罗盘家隔两户人家,屋顶上的罗盘把侯夏家的院子里看得清清楚楚。侯夏在自家院子里并不奇怪,问题是罗盘看见王丫进了侯夏的院子。罗盘听不见两人说什么,只看见侯夏在王丫后腰拍了拍。这个亲昵的动作硌疼了罗盘。侯夏和王丫进屋,罗盘仍然是那个僵硬的姿势。宋如花喊他,罗盘才醒过神儿。
饺子是锅巴的,干的一面平平整整,另一面鼓胀胀的,像丰满的鱼肚子。宋如花茶饭好,尤其擅长做锅巴饺子,因为罗盘爱吃。罗盘没像往常那样一口大半个,吃得很慢,而且不声不响。宋如花哟了一声,怎么变成小丫头了?罗盘看看宋如花,眼神却是空洞的。宋如花问,犯什么呆?罗盘说没有啊,谁犯呆了?宋如花说那我考考你,问罗盘饺子像啥。罗盘说,能像啥?像饺子呗。宋如花问,除了饺子,还像啥?罗盘偏头看看,说,像枕头。宋如花追问,还有呢?罗盘说了几样,宋如花用别样的眼神斜着他,有一样儿最像,你没说。罗盘问,哪样?宋如花骂,呆瓜!罗盘突然明白她指的是什么。罗盘说,没正经。宋如花说,两口子,哪来那么多正经?宋如花嘴不饶人,脸却红了。
罗盘没把房顶上看到的跟宋如花说,宋如花藏不住话。而且,罗盘对自己也有些怀疑,他是不是看错了?王丫怎么会和侯夏混在一起?侯夏游手好闲,还好赌,女人和他过不下去,离了。侯夏快四十的人了,王丫不过十八九岁,还没对象,她怎么能看上侯夏?侯夏有什么好?想想,又不是没可能。侯夏虽不务正业,却有一副好嗓子,鼓匠班揽了活儿常喊他去。王丫野性大,行事不管不顾。按说侯夏王丫与罗盘没什么关系,两人厮混也碍不着罗盘,但罗盘心里堵了烂棉絮似的,又闷又胀。不看见就罢了,看见了,就不能再把眼睛闭上。
第二天,罗盘雇吴四的三轮车去镇上拉化肥。化肥是去年冬天订好的,罗盘年年买,和老板已混得很熟。孰料店里没货,老板说昨儿个有人把存货全买走了。老板说你稍等等,一会儿咱的车就回来了。罗盘不好说啥,可一等就等到了下午。罗盘毛躁了,他嘱咐老板给他留着,改日再拉。老板给司机打电话,说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罗盘说什么也不等了。吴四也劝,现在回去,不白跑一趟么?罗盘说,就算是空车,我照样付你钱。吴四说,罗哥说哪里话,我不是担心你不付钱。罗盘说家里有事,吴四便发动了车。
罗盘没什么事,他惦记着侯夏王丫。到家,水没喝一口便爬上房。他的目光像一张大网将侯夏的院子罩住。没看见侯夏。侯夏的院子破败不堪,甭说牛羊了,鸡也没一只。一个猪食槽斜在当院,像个醉汉。院角窝着一堆陈年柴,已霉成黑色。霉柴边丢落着数个颜色鲜艳的方便面袋。村里,也只有侯夏这样的人常吃方便面。
罗盘躲在烟囱后面。
黄昏时分,侯夏终于出现。他从外面回来,手里提个绿书包。侯夏进屋,几分钟又出来。他来回踱着,显然在等人。又过了一会儿,王丫出现在门口。侯夏抓了她的手,似乎捏疼了,王丫用另一只手打侯夏一下。两人进屋,侯夏警惕地扫扫身后。
罗盘暗暗骂娘。狗日的侯夏,王丫还是黄花闺女呢。
吃了晚饭,罗盘去了王宝生家。罗盘很少像宋如花那样串门,除非别人主动找他。所以王宝生两口子大为意外,甚至有些慌乱。王宝生女人让王宝生买烟,罗盘说他晚上不抽烟。王宝生女人是个病秧子,怕烟,王宝生是村里唯一不抽烟的男人。王宝生女人歉意地说,你是稀客,也没啥东西招待你。罗盘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客气啥,在家呆得闷了,出来走走。王宝生附和,是呀,忙起来倒不觉得,一闲下来就慌。罗盘一边说话,一边琢磨。王宝生两口子肯定还蒙在鼓里,他不说出来,王丫就得毁在侯夏手里。可这话实在难以出口。罗盘犹豫着,直到王丫回来,话仍在舌根底压着。王丫和罗盘打声招呼,进了西屋。罗盘将话引到王丫身上,闺女大了,能指望上了。王宝生女人说,指望啥?一天到晚疯跑,嘴又馋,一点儿没跟我俩。王宝生责备,闺女是你养的,气啥?罗盘看出来,王宝生面子过不去了。王宝生虽憨,却好面子。这点和罗盘有几分相像,这也是罗盘犹豫不决的原因。王宝生女人无奈地叹气。疯跑、嘴馋就气成这样,若是知道和侯夏厮混……还是算了吧。
睡觉时,罗盘没头没脑地骂句脏话。宋如花咦了一声,你这是咋了?谁惹你了?罗盘说谁也没惹。宋如花说没惹你骂什么人?罗盘问,我骂了么?宋如花肯定地说骂了。罗盘说我骂侯夏这个狗日的。宋如花追问,侯夏惹你了?罗盘说了。宋如花呆了半晌,骂,侯夏这头猪。罗盘突然意识到什么,嘱咐宋如花,可不许乱说。宋如花说,我不说。罗盘不放心,千万不能说啊,说出去王丫就毁了。宋如花说,这话我敢乱说?只是……要不和王宝生两口子说说?罗盘讲了去王宝生家的经过,宋如花问,这可咋办?不能眼看着侯夏胡来。罗盘说,我再想想。
思量半夜,罗盘还是决定告诉王宝生。拖下去,王丫会出事。再者,宋如花已经知道,三五天还行,时间长了,她那张嘴难免露馅儿。罗盘改变了策略,单独把王宝生约出来。罗盘说,不说对不住你啊,不过你得瞒着女人,她闹点儿病,挺不住。王宝生紧张得眉毛都竖直了,啥事,啥事吗?听罗盘说完,王宝生第一句话是,不可能!侯夏什么东西,王丫哪能和他混?罗盘僵了僵说,我是说胡话的人么?我无缘无故胡说王丫干啥?王宝生的眼睛瞪得又圆又大,眼球上的血丝蝌蚪一样跳着,蝌蚪很快没了踪迹,甩下一层灰白。他恼怒地骂,这个死丫头,我揍扁她。罗盘一把拽住他,你这么闹,能瞒住你女人?她那个病,怕是撑不住。王宝生呼哧半天,我找侯夏算账。罗盘摇头,更不能去,你没证据,侯夏能承认?嚷嚷开,就更不好了。王宝生咳了一声,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王宝生仰起头,这可咋办啊。
罗盘犯难地说,是挺麻烦。
王宝生脸上扭出一片片紫青,仿佛挨了打,你得帮我拿个主意。
罗盘就等王宝生这句话。他说,你信得过我,我就帮你想个办法。第一,不能报官,除非王丫咬定是侯夏强迫,不然,治不了侯夏的罪,还弄得谣言满天飞。我看王丫不会这么说,这招不能用。第二,得现场捉拿,有了证据,侯夏王丫都反不了口。第三,对付侯夏打骂不是办法,打骂还搞得全村都知道,让他赔王丫损失费,没钱让他打条子。另外,尽量瞒着你女人。王宝生频频点头,罗盘让他回去等消息。
罗盘早早爬上屋顶,伏在烟囱旁。罗盘有点儿紧张,还有点儿担心。怕王丫不来。这担心挺不地道,可已经和王宝生说了,就得给王宝生证据。其实,让王宝生把王丫锁屋里也是个办法,可罗盘怕王宝生撬不开王丫的嘴。王丫死不承认,王宝生会怀疑、埋怨罗盘。罗盘管是管,但不能把自己扯进去。
看见侯夏王丫,罗盘麻利地溜下屋顶。宋如花想跟,罗盘狠狠瞪她一眼,你以为看戏?宋如花定在地上。
罗盘在门口喊王宝生,王宝生两口子同时出来。王宝生女人灰白着脸,目光飘飘忽忽,如飞扬的柳絮。罗盘看王宝生,王宝生说,她知道了,走吧。王宝生女人恨恨地说,看我不扒他的皮。罗盘不知她要扒谁的皮,说,不能嚷嚷,千万要冷静啊。
门从里面插着,王宝生撞两下没撞开,王宝生女人抓起石头击碎门旁的玻璃,王宝生抓住窗框一扯,窗户整个掉下来。王宝生手割破了,红了半个手掌。王宝生从窗户跳进去,罗盘叫他先把门打开,王宝生根本没听,径直跑进去。王宝生女人也要跳,可爬不进去,两条腿甩来甩去。罗盘托她一把,她总算进去了。
待罗盘进去,屋里已乱成一团。侯夏缩在墙角,王宝生女人叫骂着,又撕又抓。王宝生想拽女人起来,几次被女人甩开。王丫呆站着,傻了一样。罗盘和王宝生合力拉开王宝生女人,侯夏的脸成了地图。
二
事情暂时平息了。侯夏发誓不再招惹王丫,并当面给王宝生写了一张两万块钱的欠条,算王丫的赔偿。王丫也被王宝生关起来。王宝生一再向罗盘致谢,要不是罗盘,王丫不知被侯夏祸害成啥样呢。罗盘说你别客气,看到我就要管,王丫不懂事,我不能看她受骗。嘴上谦虚,罗盘心里颇得意。如果不是他偶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王丫搞大肚子,怎么嫁人?当然,罗盘并不指望王宝生谢他。换了张宝生李宝生,他也会这么做。
几天后,王丫突然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侯夏。
那个夜晚,王宝生敲开罗盘的门,惊慌失措地说王丫不见了。罗盘边穿衣服边问怎么回事。王宝生说这几天王丫挺规矩,他也就大意了,没再锁她,谁知她就没了影儿,他也是刚发现。罗盘劝,别急,也许她串门去了。王宝生说,这么晚了,她去谁家?罗盘和王宝生去侯夏家,门上也吊着锁。罗盘情知不妙,陪王宝生去邻村亲戚家,说没见王丫。
王丫和侯夏私奔了。侯夏把王丫拐跑了。
那天捉住侯夏,侯夏咬定和王丫是两相情愿,是爱情,王宝生女人要扯他的脸,被罗盘和王宝生拽住。罗盘损侯夏,王丫还是个孩子呢,你咋有脸说?侯夏不吭声了,对赔偿的事答应得特别痛快,那时侯夏心里怕就有了鬼念头。其实,罗盘该想到的,他大意了。
王丫失踪第二天,王宝生女人就大躺了。王宝生去镇上抓了几服药,女人死活不喝。没办法,王宝生求罗盘,让罗盘劝劝。罗盘便拉了宋如花,去王宝生家当说客。
王宝生女人拥着被子半仰半躺,怀里揣着一个枕头,见了罗盘宋如花,咧咧嘴,似乎要笑的,末了只抽出一口寒气。宋如花握住王宝生女人的手,王宝生女人的眼泪刷地下来了。宋如花劝,你想开些,王丫那么大了,不会有事。王宝生女人拧着脸说,我没这种闺女。宋如花说,也怪不得她,她让侯夏哄了。王宝生女人骂,别提那头猪。宋如花跟着骂,连猪都不如,难怪女人和他离婚。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嚼侯夏。罗盘给王宝生使眼色,王宝生把药端进来。王宝生女人还是不喝。宋如花说,喝了吧,别跟自个儿怄气。罗盘也劝,身子要紧,别落下病。王宝生女人说破罐子破摔,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爱咋咋吧。罗盘严肃地说,可不能这样,王丫咋错也是你闺女,哪有妈和闺女记仇的?王丫说回来就回来了,落下病可不是三天两天能好的。你作践自个儿王丫看不见,只是苦了宝生。王宝生女人软软的目光在王宝生身上摆了摆,罗盘忙对宋如花说,你喂她。宋如花从王宝生手里接过碗,王宝生女人顺从地张开嘴。罗盘听王宝生喉结重重响了一下,似乎裂开了。
罗盘宋如花回家不久,王宝生就来了。王宝生神色凝重,愁眉不展,让他上炕不上,给他凳子不坐,只在地上蹲着。似乎出了这档事,他就矮人一等了。罗盘劝,女人家想不开,你可得撑起点儿。王宝生叹气,都怨我,该把那死丫头好好锁着,我哪能想到她会跟侯夏跑了呢?罗盘道,这是意外。王宝生道,我该想到的,我咋就大意了呢?你说侯夏能把王丫带哪儿?罗盘眼珠子错动,脑里却是一片空白,是啊,他能带哪儿?按说他没地儿去,你没再打问打问?王宝生摇头,我问过了,都说不知道。罗盘骂,侯夏这狗日的。王宝生又捡回话头,你说,侯夏能把王丫带哪儿呢?罗盘斟酌着,这也说不好。王宝生揪着自己的头发,揪一下,举在眼前看看,揪一下,举在眼前看看,仿佛要揪出一个答案。过了一会儿,王宝生再次道,你说,侯夏能把王丫带哪儿呢?罗盘说,慢慢打问吧。王宝生看着罗盘,那眼神很难判断他是否在听罗盘说话,是否听懂了罗盘的话。
第二天晚上,王宝生又来了,依然心事重重,往地上一蹲,摆出一脸愁容。罗盘看王宝生蹲着,心里别扭,又不好说啥,问道,吃过了?王宝生说,吃过了。罗盘问,你女人喝药了?王宝生说喝了。顿顿,王宝生说,这事怨我啊,我要是一直锁着王丫,她就不会跟侯夏跑了,我哪里想到呢?罗盘说,这不是你的错,也不能老锁她。王宝生叹息两声,问,你说,她和侯夏能跑到哪儿呢?罗盘想了整整一夜,现在能回答王宝生了。他俩肯定去了城里,城里混饭容易。王宝生目光灼灼,是啊,城市多了去了。罗盘问,王丫没留下啥?王宝生说没有,罗盘说你好好想想,关她那几天,她说过什么话没有?王宝生缓缓摇头。罗盘问,她没留下信什么的,哪怕一个纸片呢?王宝生说,她写字比锄地还难受。罗盘想想也是。王宝生问,你说,她会去哪个城市?罗盘说,我长千里眼就好了。
王宝生蹲到很晚,直到罗盘问你女人一个人在家行不,他才如梦方醒,站起就走。一晚上,王宝生反反复复那几句话。
送走王宝生,罗盘拍拍脑袋,这事闹的。宋如花边拉被子边打呵欠,困死了。罗盘又说,这事闹的。宋如花斜着他,你怎么成王宝生了?罗盘说,这事……顿住没往下说。宋如花说,王宝生没怪罪咱的意思。罗盘说,越这样我越不安,他怪我倒好了。宋如花说,这怨不得你,睡吧。宋如花躺下,罗盘仍坐着发呆。宋如花拽拽罗盘,罗盘哦了一声,脱衣服。脱一件,停一停,好一会儿才脱完。宋如花横过一条腿,见罗盘没什么反应,她将整个身子伏过来。宋如花似乎要用这种方式把罗盘拽回来。她的努力终于让罗盘兴奋起来。忽然间,罗盘停住。罗盘盯着宋如花的眼睛,你说,王丫和侯夏能去哪儿?宋如花没好气,你是能人,你掐算呀。罗盘说,这事闹的。
第二天,王宝生进来,宋如花躲出去了。两人说了些客套话,便默然相对。王宝生手没闲着,仍一下一下揪头发,罗盘忍不住说,别揪了,揪光也没用。王宝生伸出两手左右看看,缓缓搁在膝盖上。他问,你说,她进城了?罗盘说,绝对是。王宝生问,你说会去哪儿呢?罗盘说,难说啊,你没打算出去找找?王宝生说,她在炕上躺着,我哪儿走得开?罗盘问,她好点儿吧?王宝生说,心病,吃药效果不大。罗盘说,你多开导她,和自己闺女生什么气?王宝生黯然道,生什么气呀,她现在想王丫呢,一天到晚抹眼泪。罗盘觉得某个地方被烫了一下,想说什么,终是没想出合适的话来。
到罗盘家串门成了王宝生每晚必不可少的活计,而等待王宝生则成了罗盘的任务。王宝生没怪罗盘什么,从来没有。甭说言语了,王宝生的神态表情也没有怪罗盘的意思。王宝生只是自责、检讨。可是,罗盘越来越不安了。没有那个黄昏,一切都不会发生,至少,与罗盘无关。每个晚上是那么漫长、难熬,到后来,罗盘有点儿怕见王宝生了。
罗盘决定躲王宝生。王宝生扑几次空,该不会来了。那天晚上他和宋如花在吴四家坐到很晚。吴四刚买回一张二人转光盘,看得宋如花屁股都不想动了。罗盘瞪她,她才下炕。吴四咬罗盘耳朵,改天你自己来,我这儿有三级片。
王宝生竟然在大门口蹲着。看到那个黑影,罗盘的心就直下坠。问声谁,王宝生霍地站起来。罗盘故作惊讶,宝生啊。王宝生委屈地说,我等你一晚,以为你出门了。罗盘解释,找吴四拉化肥,顺便坐了一会儿。他让王宝生进屋。王宝生说,不早了,我回去了。孑孑地走了。宋如花说,回来早了吧?罗盘没好气,还在别人家住下?他看出来了,回来多晚王宝生也会等。
就那么一晚,罗盘没再躲。但是面对王宝生,竟然有恐慌感,而且,听到侯夏王丫的名字,就会被刺一下,仿佛侯夏王丫是马蜂屁股,他们的针会从某个遥远的地方甩过来。
一天,罗盘从街头走过,王丫二字忽然飘进耳朵。他皱皱眉,想躲开,腿却被牵着似的,顺着声音循过来。几个人在碾台旁说话,其中有宋如花。碾房废弃后,碾台便成了村民的聊天场所。罗盘走过去,几个人都不说了。但罗盘知道他们在议论啥。罗盘狠狠瞪宋如花一眼。一个人和罗盘打招呼,问今年种啥好。罗盘说去年莜麦便宜,今年肯定贵。在这方面,罗盘总是有先见。那人似乎还有什么话,罗盘已转向宋如花,让她回家。宋如花说,又不到做饭时间,回去干啥?罗盘大声说,让你回你就回,哪儿那么多废话?罗盘很少当着外人训宋如花,但此时有点儿控制不住。
宋如花跟在罗盘身后。
进门,罗盘便瞪住宋如花,谁让你把王丫的事嚷出去的?宋如花委屈地说,哪是我嚷的?王丫一跑,全村都知道了。罗盘说,别人嚷是别人的事,你别掺和。宋如花说,我不过是听别人议论。罗盘绷着脸,那也不行,听别人嚼这话头你趁早躲开。宋如花不满了,我又没做啥事,干吗……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该告诉王宝生。罗盘骂,闭住你的嘴就不行?谁还把你当哑巴卖了?宋如花扭过脸,她生气了。
晚上,王宝生进屋,见宋如花在炕上躺着,问罗盘,怎么?闹病了?罗盘说,没啥事,身子不舒服。王宝生劝,有病可要早看啊,千万别拖着,王丫妈生生是拖的。罗盘问,怎么样?好点儿了吧?王宝生愁眉苦脸地说,光吃药哪行呢?她心重,王丫不回来,药其实是白吃。罗盘问,还没消息?王宝生摇头。罗盘说,其实,能出去找找就好了。王宝生为难地说,她闹这么点儿病,我哪走得开?都怨我,不关王丫就好了。罗盘暗想,王丫想跑不关也会跑,但他没说,只能由着王宝生说。王宝生说一句,叹息一声,每声叹息都像锤子击在罗盘心上。
王宝生走后,罗盘说,我得把王丫找回来。宋如花猛地从炕上弹起来,你没疯吧?罗盘说,我好着呢。宋如花叫,凭什么?你又没欠他。罗盘说,我受不了啦,再拖,没准我真疯了。罗盘一旦做出决定,宋如花根本无法更改。她嘟囔,眼看就种地了,丢下我一个人咋办?罗盘说,雇人种嘛,你看着就行。宋如花问,你知道他俩在哪儿藏着?去哪儿找?找也不一定找见。罗盘说,找和找不见是两档子事,我总得试试。宋如花又想到一个问题,出门要路费,谁出?罗盘说,咱先垫上吧,还能找王宝生要路费?王宝生也没逼咱去。宋如花不甘心,真要去?罗盘说,我跟你瞎说啥
三
罗盘没把真实想法告诉宋如花,他所谓的寻找只是做做样子。没有一点儿线索,寻找王丫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不是三五天的事,得几十天几个月甚至几年。如宋如花所说,要花钱,路费住店费吃喝费,那是无底洞,丢进多少钱也没个响儿。儿子去年刚娶过媳妇,罗盘的钱已花去大半。还没到结婚年龄的儿子和女方已同居半年,女方没提过分的要求,否则罗盘攒的那点儿钱根本不够。要是告诉宋如花,说不定哪天她就说漏了。罗盘不是成心骗王宝生,没这个必要。甭说王宝生没怪他了,就是打官司罗盘也输不了。罗盘绝对占理,可占理不等于心安理得。王宝生每天串门对罗盘是一次折磨,罗盘宁愿王宝生揪他罗盘的头发,王宝生不,连一句重话都不说。罗盘实在受不了啦,找个借口躲几天。
罗盘说要找找王丫,王宝生并未表现出意外,但他的态度却很坚决,不行,怎么能麻烦你呢?你这儿还有一大摊子呢。罗盘说,你走不开,我替你找找吧,没准能打问见呢。王宝生无措地说,这怎么行呢?已经给你添够多麻烦了,这……真是不合适。罗盘说,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王丫还叫我大爷么,王丫不回来,你女人的病怕是腻味。王宝生低头寻思一会儿,说,我和王丫妈商量商量。罗盘说,没必要,就这么定了。王宝生满脸歉疚,哎呀着,似乎想说什么感谢话,却不知怎么表达,末了突然大骂起王丫来。罗盘制止他,王丫还小,错的是侯夏。王宝生站起来,让你受累,我实在过意不去。你放心,家里的活儿我帮嫂子干。罗盘点头,让王宝生一早把王丫的照片送来。
王宝生走后,罗盘让宋如花拿钱,宋如花数出五百,罗盘说不够。宋如花不情愿,五百还不够?罗盘说,现在的钱不禁花,多带几个吧,你想让我要饭?宋如花嘟囔,又不是村长,什么事都想管。但还是给罗盘拿了。
刚睡下,王宝生又敲门了,罗盘披衣出去。黑暗中,王宝生的眼睛闪闪发亮,好像抹了磷火。罗盘觉出王宝生脸上的热气,显然他是跑来的。王宝生说,我翻了半天,总算找齐了。王宝生抓了厚厚一沓照片。罗盘说,用不着这么多。王宝生说,放家里也没用,留你这儿吧,万一用上呢。
王宝生没有马上走开,罗盘问,还有事?
王宝生突然抓住罗盘的手,动作又快又猛,罗盘吓了一跳。
王宝生说,让你受累了。
罗盘吁口气,还说这客气话干吗?
王宝生保证,家里的事我一定帮嫂子。
罗盘说,不早了,回吧。
王宝生执拗地让罗盘先关门,罗盘关了。
罗盘没在意王宝生是否在门外站着,他不想再说什么客套话。宋如花瞅着罗盘手里的照片说,不是让他明早送来吗?半夜三更的,着什么急?罗盘说,闺女跑了,搁谁头上不急?罗盘把照片摊开,足有二三十张。有王丫的单人照,也有合影。宋如花拥着被子坐起来,和罗盘一块儿翻看。宋如花说,王宝生的脑子是不是糊涂了,拿小时候的照片干啥?罗盘说,他是怕我认不出王丫嘛。
第二天,罗盘未能走成。一大早,宋如花的弟弟宋如兵来了。罗盘一瞅他脸上的血印,知道他又和媳妇吵架了。两口子一吵架就往罗盘这儿跑,要么是宋如兵,要么是媳妇。罗盘几乎成了调解员。宋如花要看宋如兵的伤,宋如兵扭着脸不让。宋如花说,打人不打脸,没见过这么狠的女人。宋如兵媳妇是刁了点儿,可一个巴掌拍不响,宋如兵也不是善茬。宋如兵蔫头耷脑的,罗盘猜不只是吵架这么简单。果然,宋如兵说媳妇要离婚。宋如花顿时哑口。她很明白,离婚宋如兵肯定惨。罗盘自然走不成了。匆匆吃了口饭,罗盘随宋如兵回家。宋如兵家在杨柳村,离营盘村二十多里。路上,罗盘问明两人打架的原因。宋如兵一个朋友说能买假币,拿到僻远的村子花,根本认不出来。宋如兵便从家里偷了三千块钱,换回一万假币,被媳妇发现了。宋如兵埋怨女人眼光太浅。罗盘训斥,亏得她眼光浅,由你,早撞大狱门了。谁是傻子?能让你骗了?宋如兵嘴巴狠硬,我想拿到蒙古地买两头牛,听说那地儿人好哄。罗盘生气了,你和你媳妇商量吧,我不去了。宋如兵忙说软话。
宋如兵媳妇和罗盘打过招呼,便开始罗列宋如兵的不是。末了说,这种东西,我还能跟他过?离定了。罗盘说,是啊,换个女人早跟他离了,还能过到这会儿?亏得你老是迁就他,这也是他的福气呢。我路上还说,要不是你,他早撞大狱门子了。宋如兵媳妇骂,整个一头猪。她这么骂,罗盘心里就有数了。他陪着她一块儿骂。宋如兵倒是老实了,不吱声。宋如兵媳妇骂了一阵,把一万假钱丢到炕上。罗盘捻捻,若不是事先知道,还真认不出来。罗盘说,这事是他不对,不过本意是好的,想给你弄几个钱花花呗。谁也难免犯个错误,你给他个改过机会。宋如兵媳妇说,姐夫就是偏向他。罗盘笑笑,我当然有私心啦,他离婚,我就少个兄弟媳妇。宋如兵媳妇轻轻一笑,你是为这个劝我的?罗盘说,这门亲不能断呀,给我个面子吧。宋如兵媳妇说,我要不给呢?罗盘说,不给我也没办法,你没错。宋如兵媳妇说,我真是气死了。如此一说,意味着罗盘的任务完成了。平时,宋如兵媳妇也蛮听罗盘的话。罗盘说,我一会儿走了,你好好教训他。宋如兵媳妇说,我稀罕他!她问那些钱怎么办,罗盘说,当废纸烧了吧,别搁着,也别交派出所,那会惹事。宋如兵媳妇遗憾地说,真是可惜了。罗盘说,就当丢了,破财免灾。以后扣他点儿,一天给他吃一顿饭,争取把三千块钱扣回来。宋如兵媳妇神色暖了许多,姐夫教的,我就这么做。
罗盘回村已是下午。罗盘看见王宝生,想躲已经来不及,硬着头皮迎上去。罗盘心虚虚的,仿佛欺骗了王宝生。罗盘解释,本来今天要走,但小舅子家出了点儿事。王宝生忙说,不急不急,事从紧处来。罗盘生怕王宝生不信,说了劝架的过程,亏得我去了,不然两口子就散了,凭小舅子那样,下半辈子打光棍吧。王宝生点头,是呀,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不然就坏了。
王宝生目光迟缓,可罗盘总觉得他眼底长着毛刺样的东西,扯了几句话,匆匆离开。罗盘暗骂小舅子,不迟不早,偏在这当口儿吵架。
次日,罗盘离开村庄。他走得早,到镇上商店还未开门。他没有急着赶上县的车。侯夏女人在镇上卖瓜子,他想见见她。两人虽离了婚,但侯夏女人毕竟了解侯夏,罗盘想从她嘴里掏点儿有用的。等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侯夏女人推小车出来。罗盘喊她一声,侯夏女人说,哥啊,这么早就来了。罗盘说,等你半天了。侯夏女人脸红红的,今儿起晚了,有事?罗盘笑笑,我打算到县里,王宝生闺女王丫跑了,王宝生女人有病走不开,我帮他找找。侯夏女人吃惊地说,是吗?罗盘说,侯夏把她拐跑的。侯夏女人稍一怔,破口大骂,这个不要脸的,一点儿好事不干。忽然意识到什么,我早和他没关系了,你找我干吗?罗盘说,当然和你没关系,打扰你也不合适,我琢磨着,这世上只有你把侯夏看透了,我是想让你指点指点,我想不出侯夏会带王丫去哪儿。侯夏女人神色缓和了些,山旮旯他不去,肯定找红火热闹去了。罗盘说,你说得有道理……红火热闹的地儿多了去了……他在城里有亲戚吗?侯夏女人寻思了一会儿,说,大同有他个姨姐。罗盘忙问,你有她地址没?侯夏女人摇头,我没见过她,只听侯夏说起过,好像开个粮店。罗盘说,你这个线索很重要,真是谢谢你。侯夏女人又骂,这个东西,净干丢人现眼的事。罗盘嘱咐她,有什么信儿,往村里捎句话。
到县城正是中午时分,罗盘在车站喝碗羊杂汤,吃了两个烧饼。然后掏出王丫的照片,到售票处问见过没。售票的女人轻轻瞟了一眼,说没见过。罗盘怀疑她根本没看。罗盘把照片从取票的口子递进去,你再看看。结果照片掉了下去。售票员不耐烦了,没见就是没见,不是跟你说了吗?罗盘赔笑,麻烦把照片给我。售票员没好气,谁拿你照片了?你这人怎么回事?罗盘解释,不是你拿了,掉地上了。售票员捡起来丢给罗盘。周围的人都看罗盘,罗盘尽量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脸还是憋得通红。在村里,谁用这种口气和罗盘说话?罗盘想,这是何苦?凭啥替王宝生受这个气?他冒出放弃的念头,可转身一想,已经出来了,怎么也得打问打问。随便转一圈回去,那就真是哄王宝生了。这和装样子是两码事。他安慰自己,这是县城,不是营盘村,谁认得你罗盘是老几?
罗盘拿着照片到车跟前问。侯夏和王丫肯定得坐车,说不定哪辆车拉过他们。这样,罗盘至少知道两人逃跑的方向。如果王宝生出来,绝对想不出这招。王宝生种地是好手,动脑子远不行。问了几个,都说没见过。要么说,每天拉的人多了,谁能记住?
半下午,罗盘离开车站,去日日红饭馆。儿子在饭馆当厨师,儿媳当服务员。估计这个时间饭馆没生意,罗盘一来看看儿子,二来找个住处。这样,店钱就省下了。
两男两女正在饭桌上打麻将,其中有儿子。儿媳站在儿子身后。儿子看见他,只说你怎么来了,便让儿媳带他回家。儿子屁股动都没动。罗盘对儿媳说,你把他叫出来,我得让他带我去医院。儿媳惊问,你咋啦?罗盘严肃地说,没事,你叫他出来。儿子出来,儿媳跟在身后。儿子疑问,你一直好好的嘛,咋就病了?罗盘骂,少废话!儿子没再问什么,打车送罗盘去医院。罗盘说回家,儿子糊涂了,看病不去医院,回家干吗?罗盘说,让你回你就回。
到了儿子租住的地方,儿子仍不明白,爸,你咋回事?罗盘绷着脸,你还认我这个老子?我以为你只认麻将呢。儿子品出味儿了,却没一点儿内疚,反而抱怨罗盘,你生哪门子气,我今儿正手气好。罗盘说,看来我碍你事了,我走。儿子拦住罗盘,笑嘻嘻地说,我哪舍得你走,要不,你打我两下?罗盘瞪他一眼,你这个样子,早晚也得让老板炒了。儿子说,打麻将的就有老板,炒了我,谁陪他玩?罗盘无语。儿子问,你上县干吗?罗盘说,没事,看看你。儿子鬼精鬼精的,不大像啊,你准有什么事,不是看病就好,我得走了,晚上让小红请假回来做饭。罗盘说,不用了,你把钥匙留下就行。他不愿给儿子添什么麻烦。
天色还早,罗盘再次去车站打问。直到所有的车走光,还是一无所获。罗盘又拿照片让车站附近摆摊儿的人辨认,万一王丫到过车站,万一王丫买过货呢。摇头。摇头。摇头。摇头。有一个问,是你闺女?罗盘说不是。那人满有把握地说,那就是儿媳妇了,这年头娶个媳妇不容易啊,我儿子也这命,八万块钱娶个媳妇,结婚不到半年跟人跑了。
罗盘回去已经很晚,儿子儿媳还没回来。罗盘吃了两个烧饼,无事可干,就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来回换台。眼珠子忽然黏屏幕上不动了,一个想法冒出来。儿子儿媳进门,罗盘说了来县的目的。儿子瞪大眼,王宝生闺女跑了关你什么事?罗盘说王宝生走不开,我能眼睁睁看着吗?儿子没好话,啥事都揽,村长也没你管得宽。罗盘提高声音,乡里乡亲的,谁没个难事?儿子的脸马上就变了,我不过说说,也挺好,拿他的钱四处逛逛。如果不是儿媳在身边,罗盘非给儿子一个嘴巴不可。儿子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儿子看罗盘不高兴,赔着小心说,这跟海底捞针一样,除非你给提供线索的人钱。罗盘咬咬牙,要是说出王丫的去向,给钱。儿子问,找谁联系呢?你又没手机。罗盘说,打你手机吧。儿子差点儿把脖子摇断,那可不行,接电话不少钱呢,除非王宝生出话费。罗盘重重咽口唾沫,话费你垫着,到时我来跟你算。儿子说,这还差不多,劳务费就免了,算给王宝生作贡献吧。
电视寻人广告挺简单,不到一小时就办完了。只是有点儿贵,三百块钱,才播六天。花钱像打水漂一样,几个泡泡就没了。之后,罗盘又去了车站。罗盘本打算在县里住一阵就回去。找见找不见,罗盘尽力了,也对得起王宝生了。可两晚他就呆不住了。儿子儿媳夜间折腾的声音太响,睡在外屋的罗盘面红耳臊,贼一样不敢吭气。狗日的,也不懂避讳点儿。现在回村有点儿早。罗盘寻思一阵,决定去大同。
四
罗盘不在,宋如花早早睡了。宋如花喜欢枕罗盘胳膊睡觉,二十年了。一个人睡不踏实。营盘村怕是没一个女人有宋如花的习惯。一次,几个女人洗衣服,宋如花不小心说走了嘴,她常犯这种错误。当然对宋如花已算不上错误。几个女人挤眉弄眼,一个还说宋如花骚。宋如花顶她,你不骚,儿子咋出来的?
宋如花没贪床,躺躺便爬起来,家里养两头奶牛,二十只羊,罗盘一走,喂养任务自然落在她身上。
屋门一响,院外便传过问话,嫂子吗?宋如花听出是王宝生,忙拢拢头发,把扣子系好,打开院门。王宝生叫声嫂子,几乎不由分说挤进来。宋如花哎呀,你这么早……王宝生说,罗大哥不在,家里的活儿就交给我吧。宋如花说,那怎么行,我干得了。她想拦,王宝生已经忙活开了。王宝生好像对这个家很熟悉,先把羊圈清了,给羊添了草,把牛粪铲到院门外,又把牛牵到门口,拿出取奶器给牛挤奶。宋如花要帮他,罗盘干这些活儿宋如花也常打下手。王宝生不让,他说你忙你的。宋如花就由着他。挤完奶,王宝生揭开缸盖瞅瞅,提了两桶水,又扫了院子。宋如花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出来,王丫妈怎么办?王宝生头也不抬,我早侍候她吃过了。干完活儿,王宝生在院里转了一圈,屋里转了一圈,觉得暂时没啥活儿,方洗手离去。
中午,王宝生扛来一把铡刀。宋如花愕然,问干啥?王宝生解释,青玉米秆子太长,整喂都糟蹋了。宋如花说费那个劲儿干吗,罗盘一直这么喂。王宝生说,铡和不铡不一样。铡草得两个人,一人往刀垛上送一人铡,宋如花只得戴了套袖帮他。王宝生不让她干,抓着她胳膊说,我一个人来,你干不了。宋如花拗不过他,便站那儿看。王宝生左手抓青玉米,右手握铡刀,反复蹲站。两人不说话,只有铡刀嚓嚓的声响。不一会儿,王宝生脑门儿上就出汗了,阳光下闪闪发亮。王宝生不像村里的男人用袖子擦,而是掏出手绢。宋如花抿嘴笑了,一个大男人装块手绢。王宝生不知宋如花笑,他的眼睛吊在铡刀上。宋如花憋不住了,她已经憋了很久,嘴唇都要粘一块儿了。宋如花说,有意思。王宝生没听懂,停手问,什么有意思?宋如花说你的手绢啊。王宝生脸涨红了,没接茬儿。宋如花说,你用不着这样。王宝生动作慢下来,罗大哥替我找王丫,我就得替他干活儿。宋如花劝他歇歇,王宝生说,不累,再干也没罗大哥累。宋如花说,累倒没啥,就怕白跑一趟。王宝生说,那怪不着罗大哥,怪王丫。同时瞄宋如花一眼。宋如花觉出,王宝生大约嫌她说话不吉利,他似乎认定罗盘会把王丫带回来。宋如花问,王丫妈好点儿没?王宝生说,听说罗盘哥进城找王丫,她的病就好多了。宋如花暗想,一对实心眼儿。想到这儿,咯咯笑了。王宝生再次停下,嫂子笑啥呢?我铡的不好?宋如花说,笑我自个儿呢,我先前担心你铡了手,没想到你干活儿这么利索,不长不短好像机器弄出来的。王宝生受了鼓舞,更加卖劲。宋如花说,吃坏我家的牛,你可得赔。王宝生嘿嘿笑了。宋如花一本正经,我可不是说着玩的,全靠这两头牛挣钱呢。王宝生认真地说,牛懂得自个儿肚里装多少东西。宋如花眯眼斜斜他,我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王宝生说,我没吓着,你和罗盘哥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
每天下午,奶站的老王都来收奶。老王在当街一吹哨子,养奶牛的人家就把牛奶提过去。验奶过秤开票,每到月底,凭老王的票去奶站兑钱。宋如花不愿王宝生帮她卖奶,在家里干也就罢了,折腾到街上怪不好意思。可老王哨子还没响,王宝生就来了。宋如花板着脸不让提。两人抢来抢去,牛奶洒了。宋如花生气了,挺大个男人,你这是干啥呢?我说不用就不用。王宝生傻住了,怯怯地看着宋如花,眼里有亮闪闪的水光。宋如花心软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又不是没长手。王宝生小心翼翼地恳求,还是让我来吧,我过意不去呀。宋如花说,你家里还有一摊子呢。王宝生说,我都干完了,不信你去看。宋如花想,不是你过意不去,是我过意不去。王宝生再次央求,就让我干吧。王宝生软塌塌的目光望着宋如花,像等待宋如花施舍。宋如花叹气,好吧,不过得等会儿,老王还没来呢。
哨子一响,王宝生提起奶桶就走,走得飞快。宋如花喊,你慢点儿,等等我。王宝生没听见似的,斜着膀子猛走。宋如花不放心,跟在王宝生身后一溜小跑。到了街中心,宋如花后背全湿了,老王边验奶边说你俩跑啥,我还以为捉贼呢。宋如花反应快,那个贼就是你。老王的目光在宋如花胸上瞄瞄,我倒是想偷,没那个胆啊。宋如花笑骂,烂嘴,该撕。老王很冤枉地对王宝生说,你评评这个理,我没偷,凭啥撕我嘴?王宝生聋了一般,两眼盯着老王的每一个动作。老王甚是无趣,问,写谁的名字?王宝生抢着说,罗盘。
交完,宋如花说,空桶给我,你回吧。王宝生胳膊一甩,桶到了另一只手上。两人边走边扯,宋如花说,空桶,我拿得动。王宝生连声说,不碍事,不碍事。便有长舌的人问宋如花,罗盘呢?王宝生抢着说,替我找王丫了。虽然王丫私奔已不是秘密,但王宝生不加遮掩地挂在嘴上,宋如花还是吃了一惊。有人追问,你呢?你怎么不去?王宝生做了亏心事似的,满脸不安,老婆闹病,我走不开么。
第二天,王宝生早早就过来了。宋如花有心不开门,他一口一个嫂子叫得宋如花心慌。宋如花没想到王宝生这么拗。她软不行硬不行,只得随他。早中晚一天三趟,所有的活儿干得利利落落,强过罗盘。比如青玉米,罗盘从来不铡;比如院子,脏了罗盘才扫,王宝生每天一扫。过了两三天,宋如花就习惯了。王宝生干活儿,她在一旁说话,或者边嗑瓜子边远远瞧着。有时,她丢下王宝生去串门子。不用惦记给罗盘做饭,她想几点回就几点回。原先不行,饭做迟了,罗盘的脸就裹了黑麻布似的。
一天晚上,宋如花正洗脚,王宝生扑进来,叫着,看见了,看见了。宋如花吓了一跳,问他看见什么了。王宝生挥着胳膊说,电视播了,寻王丫呢。目光灿烂地扑闪着,像一群飞舞的彩蝶。宋如花也很兴奋,忙打开电视。寻见本县节目,两人眼睛紧盯着屏幕,电视里是售酒广告,之后是药品,治中风偏瘫的,不孕不育的,再后是驾校招生,饭店开业。王宝生脖子渐渐拉长,几乎要钻进去……砰的一声,王宝生狠地缩回头。电视机稳稳的,电视里的楼爆炸了。播上电视剧了。王宝生失望地说,怎么不播了,我明明看见了。彩蝶折翅断头,纷纷掉到地上。宋如花安慰,今儿不播,明儿肯定播。王宝生点头,还是罗盘哥有招,换了我,借个脑袋也想不出来。
王宝生没走,蹲在那儿自言自语,也不知王丫看到看不到。宋如花却在琢磨播一次花多少钱。宋如花盼罗盘找回王丫,但花钱她心疼。又一想,她只给罗盘拿了一千,撑死也就这个数。于是笑问,这下你放心了吧?王宝生声音很高,原先也放心,罗盘哥是能人。宋如花撇嘴,能什么能?能还没当个村长?王宝生说,他不愿意干哩,他干还能轮到别人?王宝生边和宋如花争论,边盯着宋如花的脚。宋如花感觉到了,想他别是要给我洗脚吧,这么一想,便把脚抽出来。
王宝生端起洗脚水就往外走。
宋如花叫,别,别……
王宝生已经出去了。
王宝生返回,宋如花的脸依然发烫。责备道,你看你这人,你看你这人。王宝生憨憨地笑笑,我回去了。
次日晚上,王宝生早早来到宋如花家。两人盯着电视,像等待一个隆重的节目。宋如花给王宝生沏杯水,想想,又加了勺糖。王宝生出进惯了,不再拘谨,喝完自己倒了一杯。他对宋如花说,你也喝呀。宋如花说自己不喝,王宝生说,倒一杯吧。宋如花没动。
初冬时节,罗盘回了趟家。天冷了,身上得加衣服。还有,得凑钱。王宝生拿出七十块钱,罗盘知道他肯定榨不出来了。七十块钱罗盘咋拿?他说自己有,这个留着给女人买药。王宝生死活不肯,说这一段女人根本不用吃药,王丫有信儿她就好多了。王宝生还说罗盘贴的钱他早晚会还上,让罗盘放心。罗盘说找人要紧,你甭惦记这个。王宝生强调,那可不行!罗盘和宋如花相视一眼,苦笑。
出来二十天后,罗盘往回打电话。宋如花告诉罗盘,王宝生准备借高利贷,二分利贷不上就贷三分的。罗盘脑袋砰的一响,险些摔了电话。他让宋如花拦住王宝生,他近日赶回去。宋如花说我哪能拦住?罗盘说,必须拦住!
罗盘是半夜回去的。宋如花说好歹把王宝生拦住了,不过恐怕是暂时的,王宝生这个人哪听别人的?她忧心忡忡地问罗盘,这可咋办呀?罗盘把想好的计划说了:带她一起离开,不见王宝生的面。宋如花问,让我和你一块儿找?家里怎么办?罗盘说,咱也去城里找个营生干,我看出去的混得都不错。至于找王丫,以后再说,当前的事是赶快离开。宋如花不同意,说不能因为王宝生就不在村里呆了,又没欠他的债。罗盘说就这么下去,会毁了王宝生,那就真欠他了。宋如花说在村里住了二十年,舍不得走。罗盘说以后想回来还可以回来,我估摸着王丫一年半载就回来了。宋如花问,要是王丫再也不回来呢?咱就甭回村?罗盘横他一眼,嫌她嘴臭。宋如花气鼓鼓地说,要走,牲畜都得处理,再回来咋办?罗盘说有钱飞机都能买,还怕买不上牲畜?宋如花还是不乐意,罗盘有些恼火,说再这么下去,王宝生毁了不说,他和她也甭想再到一块儿。宋如花窝在罗盘怀里呜呜哭。罗盘松了口气,摸着她的头说,城里光景比村里好,几天你就习惯了。其实,他心里更难过。
第二天,罗盘对王宝生说了。罗盘说,找王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俩就在城里住了,这样能省不少路费,让你女人安心养病,有信儿我就告诉你。王宝生脸涨得紫红,结结巴巴地说,这……咋行?罗盘拍拍他,放心,我会好好找。王宝生提出替罗盘饲养那些牲畜。罗盘说现在贼多,卖了好,叫王宝生别操心了。
接下来的一周,罗盘卖掉了奶牛、羊、猪、柴草。鸡给了王宝生,粮食在王宝生那儿存了一些,余下的全卖了。锅碗瓢盆铁锨锄头畚箕叉子都存在房里,罗盘带的只是衣服和两套行李。
最后的工序是封门窗。门窗先用砖垒好,再从外面抹泥。宋如花给罗盘打下手,两人默默干活儿,谁也不说话。封好,罗盘爬上房,盖了烟囱。然后,他望望村子。数月前,罗盘就是在房顶发现了王丫侯夏的秘密。冬天的村庄枯黄枯黄的,罗盘感觉自己的心也枯了。
罗盘的目光一点点摆过去,猛就看见了王宝生。王宝生正往这边跑,他的样子慌慌张张,由于跑得急,两条胳膊像溺水一样没有章法地挥舞着。罗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呆了呆,腿忽然就软了下去。
原载《芒种》2008年第12期
原刊责编王霆
本刊责编章颖
作者简介
男,1967年9月生。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天外的歌声》《私人档案》等三部,中篇小说集《极地胭脂》《麦子的盖头》《婚姻穴位》等四部。小说被多家报刊转载,入选多种选本。曾获《小说选刊》“贞丰杯”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全国读者喜爱的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百花奖、《十月》“福星惠誉杯”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省第9—10届文艺振兴奖。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2006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创作谈:皮尖草
胡学文
这是一篇犹豫的小说,写前犹豫,下手也犹豫。上路了,方向不明,模模糊糊地走。目的明确甚好,但有时模糊也有好处,总觉得前面有新奇,有意外。未必是惊喜,却有那一汪期待。这个人存在了很久,乡村类似者大有人在,在别处怕是难以生存,可在乡村中,有时却是强者。我想起乡村的一种草,俗称皮尖草,生长在墙根、石块之间,看上去柔柔软软的,摸一下却能把手掌划个锋利的口子。一片土壤,一种植物,一类人,我想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篇小说涉及到道德,但我却不是想做道德上的身份认证,不想给人物贴上道德的标签,我是想弄明白皮尖草何以能在乡村的土地上疯长,想弄明白一个卑弱者何以在乡村的土壤中变得强大,变得让人畏惧。我认为与性格无关,与事件无关,二者不过是诱因,根本在于乡村阳光的成分,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及各种矿物质的成分。我想辨出那个模糊的东西,试图使其清晰地浮出来。当我走到尽头才发现,模糊者依然模糊,只有个朦胧的影子。小说是无力的,当然,换一个说法,不是小说无力,而是作者无力。